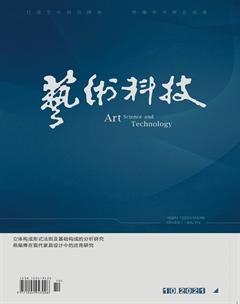唐代山水田園詩及其對現代生態文學的啟示
黃睿 楊思琪
摘要:生態文學是一種獨特又新潮的文學門類。我國的生態文學發展并不成熟,大多數文章只有一些模糊的界定。與生態相關的山水田園詩經過魏晉的提出發展后,在唐朝已有眾多詩文可考。本文希望以唐代詩歌為代表,探尋當時生態文學對現代生態文學的啟示與意義,充實生態文學內涵。
關鍵詞:唐代山水田園詩;現代生態文學;啟示
中圖分類號:I207.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10-00-02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代之一,不僅因為唐朝經濟底蘊雄厚,國力強盛,更是因為與外國文化相兼容,營造了自由開放的文化環境,成就了唐代士人的自由思想和積極心態。魏晉陶淵明開創的田園詩與謝靈運的山水詩,在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基礎上有所創新。他們多有漫游經歷,對名山大川清婉秀美或壯闊雄渾的風景皆有見與感。山林河海對他們審美性情、詩文內容的塑造功不可沒。本文或許能從其中探尋出現代生態文學問題的解決辦法。
1 生態文學
生態文學是人類自覺協調與生存環境關系的文化范式[1]。生態思想以生態系統的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而不是以人類或其他局部利益為最高標準。由此可見,生態文學就是以生態為中心,探討人類行為與自然的關系是否符合長遠發展。
生態文學的關鍵在于“生態”,但這并不是簡單的對自然環境的描寫,我們要從中汲取有關生態保護與發展的思想。尤其有一點值得注意:生態學家認為早期生態保護被稱為環境保護是不合理的,“環境”是人周圍的環境,這無意間將人變成了焦點。而生態是強調人與自然生態環境和諧平等,相互依存共生[2],因此目前生態文學研究領域仍有許多語言需要改進。如詩歌中有一種特殊的表現手法叫作“意象”,即借自然景物表現人的心理情感、行為狀態。再如杜甫《春望》“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中的“花”和“鳥”并非對“國破山河在”有怎樣的情緒,但詩人借它們來表達自己的悲觀絕望,就是利用環境表達心理情感的方法,這種以人為中心的手法在詩歌中非常普遍。生態文學以生態利益為核心的特征決定了它必須將所有將生態工具化的態度和方法排除在外[3]。這種詩歌并不能算是生態文學,我們只能以分析美學文學的方法鑒賞它,從中學習有關生態的思想。
2 唐代生態思想
在歷經工業革命時代大進步大污染之后的我們想要把生態恢復到最初的模樣是很難辦到的。但當今世界大部分人普遍認同維護生態平衡發展的重要性,生態是與人類相輔相生的。那在人為干涉較少的中國古代,文人們是如何看待人與生態的關系呢?
山水審美起于魏晉。魏晉的士人追求自我解放,他們追求的瀟灑、達觀、風流、淡泊、質樸歸為新的詩歌體裁——山水田園詩,但同時南北朝時期政治與宗教對文學的影響頗大,民眾不僅受佛教影響[4],再加上老莊思想對玄學的改造,山水被賦予了濃重的人文色彩。
但唐朝不同,因其開放自由的文化環境、初唐及盛唐期間昂揚恣意的士人態度,造就了唐代山水詩文“美在自美”的獨特風格[5]。在美學中有一個詞稱為“美不自美”,即“美”依托于觀賞者、歷史發展等外在因素而美,而這里的“美在自美”就是自然之美不依托人而存在,生態之美有其客觀性與平等性。唐代建朝以來,以儒學為基礎,佛道影響不斷加大。道教使人回歸自然,給唐代文人提供了親近自然的好理由;佛教對人的信仰上的影響頗大,如王維在《戲贈張五弟諲三首》中云:“徒然萬象多,澹爾太虛緬。一知與物平,自顧為人淺。對君忽自得,浮念不煩遣。”一句“與物平”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是“美在自美”的體現[6]。一般談及王維的詩,多講他的空靈禪靜,王維的空靈達到了物我兩空的心境,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中說“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王維恰好相反,物我平等,才可雙空。
孟浩然作為唐代田園詩人代表之一,為我們展現的是絕美的鄉間景色,孟浩然以抒情的筆調描寫淳樸自然的鄉村環境[7]。垂釣放牧與炊煙,都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人間至景。孟浩然詩中流露出的清逸應該也是當代人所追求的清逸。當代網絡中有一類人,他們因種種原因居于遠郊或鄉村,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將破舊的茅屋、荒廢的土地改造成為世外桃源、人間天堂。他們時常在視頻中展現自己對生活的熱愛,他們因充實而浪漫的生活觀念而廣受關注及好評。“詩與遠方”是這個浮躁而急速的時代下催生的理想化生活,也是很多人實現不了的夢想[8]。隨著時代的發展,近郊成為更多小資愿意選擇的居住地區——遠離被污染的市中心,返歸自然健康生活,這也正是千年前孟浩然的棲居思想,可見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內心浮躁,十分向往這種“復古”生活,以追求內心平靜。因為在這種人與自然平衡的關系下,雙方確實是互利共贏,相輔相成,自然之美確能安定人們浮躁不安的內心。
名垂千古的恣意詩仙李白的山水詩數量在唐代詩人中不可謂不多。一方面,太白是一位浪漫而自由的詩人,他熱愛山水,熱情地抒發著山河的雄渾秀麗之美。他游歷的山水幾乎覆蓋了中國一半的國土,所作的山水詩在古代幾乎也無人能及。另一方面,李白的山水詩具有詩人獨立而飄逸的個人價值,他熱愛自然、尊重自然,與自然交友,游覽名山大川,與天地融為一體。但也需要認識到,李白詩歌的特點之一就是夸張主觀思想的融入,這與我們平等地認識生態有一定偏差。
以上幾位詩人的不同詩歌風格呈現出他們的不同人生歷程,也反映出各自對待生態的反應。但無論他們各自經歷如何,均可見他們對生態自然是相似的。從他們的詩歌中可以看出唐代生態重在平等,重在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而非襯托或利用的關系。在他們的詩中有著對自然的強烈熱愛和向往之情,或許這也是他們的詩歌充滿生機的原因之一。在興趣的支持下才能長久地發展事業,正如當人們內心的信仰足夠堅定時,靈性自然會復蘇,帶你通往神性的彼岸[9],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有強烈的生態恢復或生態保護意識,那么生態可持續發展這一理念也會成功。
3 生態保護觀念與文化發展水平相一致
有的詩人描繪景物風光,有的詩人描繪自然現象。如李白《蜀道難》的“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 以巴蜀為例,能看到形式最為簡單的生態文學。詳細又夸張地描繪了巴蜀環境特征,可見當時巴蜀的生態充滿生機與野性。再如蘇颋《曉發方騫驛》的“片陰常作雨”;盧照鄰《至陳倉曉晴望京邑》的“澗流漂素沫,巖景靄朱光”;王維《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盤曲四五十里至黃牛嶺見黃花川》的“颯颯松上雨,潺潺石中流”,梳理這些信息可以得知唐代蜀道地區生態狀況極佳。文章風格的形成,與作者自身的才性和氣質有很大關系[10],文學作品無法脫離作者的主觀情感而獨立存在,尤其是在描寫山水自然時,會直接或間接地體現出作者的態度[11]。好的生態文學作品不只要求詩人對生態的美進行描寫,更要求詩人由較高的審美態度、寫作能力及文化水平,描繪出整個時代的生態審美。因此,唐代開放的文化環境與其兼容并收的博大胸懷造就了中國古代文化高峰之一,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古代的“生態文學”與時代共同繁榮。
近代社會因工業發展、人類發展而導致生態被破壞的慘案不在少數。巴西原始森林的土著居民們不知道如何保護生態,更不知道雨林對地球生態的重要作用。他們只懂得用最原始的辦法刀耕火種、砍伐森林換取經濟利益以謀求自身發展。在近代工業革命中也是如此,技術是一把雙刃劍,技術在給人類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在人類的發展進步方面有著絆腳石的身份[12]。廢舊有害氣體大量排放導致冰山融化;工業產品垃圾直接入海使動物體內充滿塑料;以及我國早期盲目開墾致使森林湖泊消失,沙土漫天……當時為了發展只考慮到眼前的利益,這也是時代的局限。
當代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13]。自然知識水平、認知思想也在不斷進步。近些年我們積極提出可持續發展、退耕還林等理念,森林復原等生態保護行動也走在世界前列,可見先進的生態觀念總是與文化發展水平一致。
4 生態文學自覺
生態文學是作家反映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發展狀況以及人類對此的行為態度與表現,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視為文學批評。生態文學寫作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觀念問題,即作家能否形成關于生態明確的立場、價值判斷等生態自覺的思維,也就是上文提過的作家審美自覺[14]。但面對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生態文學卻尤為冷漠,主要是因為感悟自然能力與生態整體觀的缺失——人仍舊以自我為中心,缺乏對自然的親近感悟,文化批判不足。“優秀的文學作品不是無根的浮萍,往近處看,其為社會現實這一廣闊肥沃的土壤上生發出的花朵;往遠處看,其遵循先哲所提出的美學理論中經過時間的淬煉而更顯其科學性的那一部分的指導。”[15]只有文化教育高度發達,使得平民階層接受文化熏陶,才能獲得一定的審美水平[16],生態保護才能落實。正如“光有生活而沒有對生活的深刻理解,那就等于沒有生活”[17]一樣,生態文學同樣適用,生態文學可以使人們反思自己的想法與行為,但可惜的是現在的生態文學并不成熟。
因此,提高文化思想水平、教育先行在當下尤為重要。我們可以從古代先賢那里學習他們對待生態的看法,力爭人人提升思想境界,發展生態文學,在根源上停止生態破壞,形成一個更加美好的生態環境。
5 結語
生態文學并不是一個高深難懂的話題,反而與我們休戚相關。正因如此,筆者閱讀了大量文獻,在他人的基礎上修正補充并提出關于“文學作用于生態”的觀點。本文的不足之處在于大篇幅地展現前人如何看待生態與出現的問題,但并未詳細說明現今不同職位的人應對此采取什么措施,比如學生應當如何、政府應利用生態文學做些什么……這些尚未解決的問題,筆者會在今后的研究中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
參考文獻:
[1] 張劉剛.生態文化傳播中的語義特征[J].戲劇之家,2019(30):235-236.
[2] 徐紫薇,薛芳芳.從“自然的人化”到“人的自然化”——生態美學視域下人的解放[J].大眾文藝,2019(05):228-229.
[3] 劉日照.論環境新聞采訪前的資料準備[J].新聞知識,2019(06):74-77.
[4] 孫靖舒.論南北朝時期的南京古寺院[J].安徽文學(下),2018(12):185-186.
[5] 閆續瑞,杜文博,馮寧.唐代山水田園詩的生態意蘊研究——以王、孟詩歌為個案[J].前沿書刊,2010(24):178.
[6] 劉兆愛.生態美學視野下的王維詩歌意象研究[D].濟南:濟南大學,2017.
[7] 孫雅婷.論汪曾祺鄉土小說中的人物形象[J].大眾文藝,2019(10):29-30.
[8] 鞠凌莉.探討電視慢綜藝的節目導向與觀眾的心理認同關系——以《向往的生活》為例[J].大眾文藝,2019(13):195-196.
[9] 苗欣雨.心有猛虎 細嗅薔薇——對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理解感悟[J].漢字文化,2019(16):123-124.
[10] 李熠婷,黃舒琳.論江蘇鐘山書院教育及其現實意義[J].大眾文藝,2019(10):214-215.
[11] 劉心依.《徐霞客游記》的創作背景與精神內涵[J].漢字文化,2020(22):32-33.
[12] 劉日照.論我國媒體社會責任缺失現象[J].今傳媒,2018(12):36-40.
[13] 張劉剛.論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的難點和路徑[J].新聞知識,2019(06):84-87.
[14] 劉軍.生態文學評輯[J].創作評譚,2020(03):34.
[15] 徐紫薇,薛芳芳.論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對可然律或必然律的回應:以《百年孤獨》為例[J].神州,2018(29):1-2.
[16] 趙涵,盧欣彥.唐宋詩文與斗茶文化[J].漢字文化,2020(19):39-40.
[17] 譚媛.論陸文夫《美食家》中的矛盾人物形象[J].大眾文藝,2019(11):40-41.
作者簡介:黃睿(2000—),女,甘肅蘭州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
楊思琪(2000—),女,河南信陽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
指導老師:程嫩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