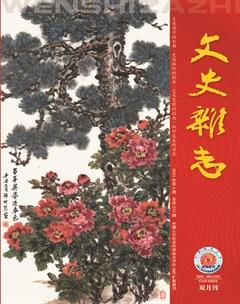近代以來中國出路的四次歷史選擇
趙映林
1949年12月,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受到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中央領導人的熱烈歡迎。斯大林高度評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勝利,他說:“中國革命的全面勝利在望,中國人民即將獲得徹底解放,共產黨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中國革命的勝利將會改變世界的天平,加重國際革命的砝碼。……我們全心全意祝賀你們的勝利,希望你們取得更大的勝利!”[1]中國共產黨取得的勝利,沖擊了二戰后形成的世界秩序(雅爾塔體系),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贏得了巨大聲譽,其影響不僅是一國的,也是世界性的。翻開中國的近代歷史,人們會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
歷史的第一次選擇: 洋務派的自強求富
鴉片戰爭(1840—1842年)加重了中國人民的苦難,喚醒了統治階級中的一部分人,出現了一些反映初步革新思想的議論和著作,如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鄭觀應的《救時揭要》、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畬的《瀛環志略》等。編著者們無不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承認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優于中國的專制制度,西方有長處,中國有不足,需要向西方學習。他們在強調學習西方目的的同時,又要求“不必仰賴于外夷”,含有獨立自主之意。不過,這些認識當時還僅限于極少數士人的一廂情愿,既沒有握有實權者的青睞,更未上升為統治集團的共識。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年),再次喪權辱國,簽訂不平等條約;之后社會上涌現出又一批具有新思想的代表人物,如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陳熾、何啟、胡禮垣等。他們抨擊專制極權統治,要求發展資本主義,主張建立“君民共主”的政體。嚴酷的現實也喚醒了統治集團中的一些有識之士。曾國藩在圍剿太平天國時,看到的是“洋船上下長江,幾如無日無之”[2]。薛福成在《庸盫筆記》中說到一件事:1861年3月,胡林翼在安慶江岸,目睹兩艘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為之“變色而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可見洋人輪船給他的刺激之深。不僅如此,曾國藩還領教了太平天國從洋人那里購買的“西洋之落地開花炮”的厲害,為之驚心動魄,囑曾國荃與李秀成交戰時一定要“小心堅守”。[3]這年8月,曾國藩在安慶首辦軍械所,將精習西方科學技術的華衡芳、徐壽、李善蘭、張斯桂等人盡悉延攬,制造西式槍炮輪船,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第二次鴉片戰爭后,統治集團中一部分身當其沖的官僚在西方優勢面前開始了尋求自強的道路,開啟了“師夷長技”的帷幕。奕、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一批官僚,開展了挽救清政權的洋務運動。
“師夷長技”的自強運動,在以練兵為要,練兵以制器為先的原則下,制造槍炮輪船。其時除最早的安慶軍械所外,比喻著名的軍工企業有:上海的江南制造總局、南京的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號稱四大軍事工業。除此之外,洋務派還相繼在西安、蘭州、濟南、成都、昆明等地和湖南、廣東、吉林、山西、浙江、臺灣等省設立機器局,制造軍火,規模雖然小于四大軍事工業,但都能為各省清軍供應軍火。在軍事工業之外,又成立海軍衙門,管理與海防有關一切事宜;還購買西方國家的鐵甲兵船,成立海軍艦隊,建筑旅順等軍港船塢,到中法戰爭前夕,建成了北洋、南洋、粵洋三支海軍。
洋務派在“求富”口號下,創辦了諸多民用工業,涉及采礦業、冶煉業、交通運輸業、紡織業等。規模較大的民用企業有: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漠河金礦、漢陽鐵廠、湖北織布局、基隆煤礦、天津電報局、蘭州機器織呢局等20余家。興辦的鐵路有唐山至胥各莊鐵路,后延長至天津,成立北洋鐵路局。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在臺灣鋪設了兩條鐵路,路線為:臺北—基隆、臺北—新竹。
民用工業的興辦,刺激了民間投資實業的熱情,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民辦企業,僅較大規模的就有50多家,資本超過了500萬元,較著名的民營企業有:廣東南海的繼昌隆繅絲廠、天津的貽來牟機器磨坊、汕頭的機器豆餅廠(機器榨油與壓制豆餅)、上海的公和永繅絲廠、上海的同文書局、上海均昌機器船廠、廣州的造紙廠、天津的自來火公司、寧波的立通久源軋花廠、上海的燮昌火柴公司、北京的機器磨坊(面粉廠)。洋務運動使買辦、外貿商人、商行的高管,以及民辦企業的投資、管理者共同形成中國的第一批資產階級。至于中國無產階級,“不但是伴隨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而來,而且是伴隨著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地經營企業而來”[4]。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不同于以前的新變化。
洋務派還舉辦了西式教育。1862年,同文館設立,以培養外語翻譯人材為主。這是中國的第一所外國語大學,初設英文館,以后次第增設俄文館、法文館、德文館、日文館、算學館;所授課程甚廣,除了外文,有算學、代數、幾何、三角、博物、化學、天文、地質、測量、礦務,以及政治、經濟、國際法等,由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任總教習,由此開創了中國近代教育事業。之后,在上海、廣州先后建立了相同性質的廣方言館。與近代教育相應的是譯書。京師同文館30年中翻譯西方書籍近200部,以外交、史地、政法一類為多,其中有中國人首次見到的第一本國際公法著作。1868年江南制造局附設的翻譯館,40年里譯書199部,其中絕大部分是自然科學、實用科學方面的著作。傳教士傅蘭雅在江南制造局供職幾十年,為以翻譯事業溝通中西作出巨大貢獻。他雖是傳教士,主旨卻不在傳教,而在翻譯西方科技著作,尤以《格致匯編》影響為巨。
為了培養“自強”需要的人材,洋務派興辦了一批專攻軍事和工藝的專門學校:設水師學堂和武備學堂于天津,辦廣東水師學堂,派軍士往德國學習水陸軍械技藝,在江南制造局辦了附設機械學校,在福州船政局辦了船政學堂,在天津、上海辦了電報學堂,還在天津辦了軍工學堂,等等。
這一階段,最值得一提的是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中國最早留學美國的容閎,1854年于耶魯大學畢業,抱著教育救國的宗旨,一心要報效祖國;但一直等到1871年,從26歲等到43歲,這才最終促成朝廷外派留學生這一“中華創始之舉,古今未有之事”。1871年9月9日,容閎的幼童出洋留學計劃在曾國藩、李鴻章等的力促與保舉之下,終于獲得批準辦理的圣旨。之后,便是“中國幼童出洋肄業局”的成立,從1872到1875年,一共四批120名幼童出洋留學,費用全部由朝廷承擔。世人所熟知的詹天佑、唐紹儀就是這一時期的幼童留學生。
洋務派“自強”新政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是為了“制夷”。“制夷”是為了鞏固清王朝的統治,為了統治者“天朝大國”的體面,很難說是真心為了中國的近代化,故李鴻章說自己是裱糊匠。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李鴻章在給光緒皇帝的奏折中明白地講:“中國文物制度,迥異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5]。“西學”因“中體”不變,“西學”嫁接到“中體”上,勢難成長,也就未能從根本上解決洋務派所追求的“自強”“求富”兩項具體目標,故而在甲午中日戰爭中一敗涂地。甲午戰爭宣告了僅在經濟、技術層面上進行器物變革,并不觸動上層建筑根基的洋務運動的失敗。
中國出路的第一次選擇的失敗,是制度的失敗。其時大清國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中體西用”的自強求富結出的果是“器”,是表面的變化進步,而“道”卻未變;兩千年的“未變之局”并沒有隨著“器”的變化而有所改變、有所進步,有的只是行政機構的增添或易名而已。中國自強求富時期,正是日本明治維新階段。彼時的東洋,毫不猶豫地拋棄了“大化革新”以來1200余年的學中國的傳統,轉向學西方,開始了制度的變革創新而迅速成為近代文明國家。中國3000年的皇皇文明,卻敗給了尚處幼沖近代文明的日本,教訓是十分的深刻。
歷史的第二次選擇:改良派的戊戌維新
甲午戰爭(1894—1895年)后,“天朝大國”夢的幻滅,催生出維新變法。一些思想敏銳的知識分子將注意力轉移到政治方面。他們當時已看出中國問題之所在,如留學法國的馬建忠指出:“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制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6]維新運動的興起正是要解決、彌補導致“自強”新政不足方面的問題。王韜在《弢園文錄外編》強調“民可順而不可逆”。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更是積極主張開議院,認為“無議院則君民之間勢多隔閡,志必乖違”;有了議院就能上下同心,“君民相洽,情誼交孚”,自無敵國敢相凌侮。簡言之,是要解決制度層面的問題。
將上述觀念付諸于實踐的當首推康有為。當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后,康有為與他的學生梁啟超等即于5月2日發起了“公車上書”,提出三條“權宜應敵之謀”:“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之后,他們組織強學會、保國會,并繼續上書推動變法……直到1898年5月29日,恭親王弈去世,長達三十余年的洋務時代結束,變法隨之驟然加速。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然而至9月21日慈禧太后等發動政變,戊戌變法僅僅103天就夭折了。百日維新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內容:經濟方面是保護農工商業,獎勵發明創造,鼓勵私人辦企業,修筑鐵路,開采礦產,改革財政,編制國家預算等;文化教育方面,設立新式學校、譯書局,開辦京師大學堂,派留學生,自由辦報,成立學會,改革科舉考試制度,廢除八股,改試策論;軍事方面,訓練新式海陸軍,裁撤綠營等;政治方面,精簡機構,裁汰冗員,長期不勞而食的“旗人”須自謀生路,廣開言路,準許、鼓勵官員和民眾論政,等等。除此之外,康有為還力主盡速開設議院。上述內容反映了康有為的急速心態:快速全面推進。康有為之弟康廣仁當時就說他 :“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措太大,當此在排者、忌者、擠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7]結果不幸說中:慈禧太后再次臨朝“訓政”,光緒帝被囚,譚嗣同六君子被殺,康、梁逃亡日本。楊天石先生總結百日維新失敗的影響說:“它激起了人們對滿洲權貴的憤恨,此后,以武力推翻清朝統治為宗旨的革命黨人即進入歷史舞臺中心,并最終導致辛亥革命的成功。”[8]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滿洲貴族利益集團的政變,促成了改良派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的聯合。
甲午中日戰爭最嚴重的一個后果不是賠款2億兩白銀、割讓臺灣,而是開啟了西方列強進一步覬覦中國的野心。進入20世紀后,國家危機愈加嚴重。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倉皇出逃。1901年1月29日,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在形勢已如危卵之下不得不發布了一份態度鮮明的上諭,實行變法,終于開啟了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
歷史的第三次選擇:清末新政與辛亥革命
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發布上諭,其變法基本精神有三點:第一,變法的目標是“富強”——繼承了此前的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的部分目標;第二,變法革新的方針是“取外國之長,去中國之短”,含有既承認當前中國政治體制需要改革的迫切性,也明確了社會改革的最終方向,與戊戌變法這部分內容一致;第三,革新的內容包括“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事、財政”,涉及的內容廣泛,與康梁要求變法的內容不悖。從上諭內容看,體現的是全面的改革思維,幾乎是戊戌變法《明定國是詔》的翻版。清統治者面對內憂外患,總算明白不變不行了,遂于4月成立了以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等人組成的“督辦政務處”作為改革的最高規劃、指導機構。新政推行幾年,取得了一定實效,如頒發了我國歷史上的第一部著作權法——《大清著作權律》。新政的成績還可從財政收入上看出:戊戌變法前,朝廷每年財政收入一直在白銀8000萬兩上下徘徊;推行新政后的1910年,財政收入高達30200萬兩,其中的商稅、實業稅是重要的一塊收入。這是有清一代歷史上的最高。[9]
然而,日俄戰爭日本大勝,俄國慘敗。這件事深深刺激了中國人的神經,不少國人認為這是立憲對專制的勝利,呼吁效法日本,實行君主立憲。在時議壓力之下,1906年9月1日,朝廷宣布預備立憲;但同時又聲稱,規制未備,民智未開,只能先從議定官制、厘定法律、廣興教育、清理財務等事情做起,作為“預備立憲的基礎”。上諭表示,要在數年后查看情況,再行妥議實行立憲期限。1907年9月,朝廷成立資政院;10月后,各省籌備設立咨議局。1908年8月27日,朝廷正式批準頒行《欽定憲法大綱》《九年預備立憲逐年推行籌備事宜清單》。此后,預備立憲進入實施階段。[10]不過,《欽定憲法大綱》卻遭到包括革命黨人在內的普遍不滿與反對,這主要是因為這部憲法的實際內容仍是竭力突出皇權、維護皇權。它雖然規定“臣民”有言論、著作、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但限于“法律范圍”之內;倘無法律規定,不得擅自。這些“自由”實際上只是一紙空頭支票。
1908年11月14日、15日,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不滿3歲的溥儀繼承皇位,由其父醇親王載灃攝政。這時的清政權已經陷入徹底的權威危機。為了保住滿洲權貴利益集團的統治,朝廷試圖通過加速變革來贏得人心。載灃的具體措施是重申預備立憲。孰料此時全國各大城市推動速開國會和成立責任內閣的請愿活動已是風起云涌。面對洶涌澎湃的輿情,朝廷被迫于1910年10月宣布于1913年召集正式國會,將原定9年的預備立憲的時間縮短了4年。1911年5月8日,清廷公布了第一屆內閣名單,共計13人,其中皇族7人、滿族2人,漢族4人,皇族超過一半。這7名皇族成員中的奕劻聲名狼藉。他最關心的就是如何弄到更多的錢,是最大的貪官。其他幾位不是昏庸無知,就是紈绔少年,讓世人大跌眼鏡,被人譏為“皇族內閣”。對此,連西方記者都看明白了,《泰晤士報》記者發回國內的報導說:“在目前,改革作為一個熱門詞匯掛在了每一個清國人的嘴上,但是在這個官僚體系中,究竟有哪一個部分作了嚴肅認真的改進?”[11]官員之所以不作“嚴肅認真的改進”,就在于各級官員無不借口“改革”“新政”而上下其手,在改革的名義下撈錢。因此,這場“預備立憲”在一批貪官污吏的操縱下,完全變味,失去民心。恰如莫理循在給《泰晤士報》的電文中所說:“清朝危在旦夕,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多數皆同情革命黨,很少有人顧惜這個使用太監、因循守舊、腐朽沒落的朝廷。”[12]對于一個病入膏肓的沒落王朝來說,最后的崩潰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而國進民退的鐵路政策成為壓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1911年5月保路運動興起,迅速擴展至川、粵、湘、鄂四省大地。隨之革命軍起。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各省紛紛響應,辛亥革命勢不可擋。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2月12日,隆裕太后頒布由張謇起草的宣統皇帝退位詔書,統治全國268年的清王朝結束了。
歷史的第四次選擇: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辛亥革命埋葬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大大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中國人民的思想解放。從此以后,任何違反民主的潮流,要在中國復辟帝制和建立獨裁統治的人或政治集團,都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對而失敗。清王朝被推翻,打亂了中國原有的社會秩序,從而為更進一步的革命發展開辟了道路。對辛亥革命,毛澤東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辛亥革命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而斗爭”的革命。[13]
由于民主共和觀念的深入人心,北洋政府官員亦或多或少受到影響,西方的各種政治思潮、社會思潮紛紛涌入,深刻影響了中國知識界。不過,民國建立后的種種亂象,則使知識分子于失望之余,繼續探求救國的出路,魯迅曾回憶說:“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新的社會起來,但不知道這種‘新的該是什么。”[14]魯迅的回憶反映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們的新覺悟,其中一部分先進分子深感以往努力的方向,過于偏重歐美的模式。這樣一批探求救國救民出路而不得其解的中國先進分子開始把尋找的目光從西方轉向東方,從歐美轉向俄國,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向愛國主義,再轉向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新青年》的出現,是知識界覺醒倡導新思想的一面旗幟。新文化運動喚醒了愈來愈多的青年知識分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準備了思想基礎。恰在此時,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首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它震動了富于政治敏感性的中國知識分子,給了中國的先進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五四”以后,社會主義思潮已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中國社會已不可阻遏地進入轉型期。兩次鴉片戰爭以來各種反抗外來侵略與本國反動勢力的失敗,或改良中國的努力,無不證明了不論是滿洲權貴利益集團,還是洋務派、維新派、立憲派,以及中國同盟會等革命派,都無法解民于倒懸,保障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更不用說去改變一個世紀來的積貧積弱,去促進中國社會的穩定和制度的重建,進而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了。白話文的推廣運用,則愈加廣泛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共產國際和蘇俄的協助下,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雖有國際因素,卻是中國歷史選擇的必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條件下,歷史選擇了拯救中國的唯一道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新民主主義革命之路。誠如陳旭麓先生所指出:“從戊戌變法仿效日俄、辛亥革命仿效法美到‘五四之后仿效蘇俄,表現了每個時期先進中國人的選擇。但三者又構成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環節,因此,這又是一次歷史的選擇。”[15]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英勇斗爭,中國歷史這才進入一個新紀元。之后的歷史發展證明了100年前的歷史選擇的無比正確——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今天,我們告別了舊的百年,開始了新的百年!
注釋:
[1]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435頁。
[2]《曾國藩家書》卷之七,中國致公出版社2011年,第273頁。
[3]《曾國藩家書》卷之八,第311頁。
[4]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7頁。
[5]轉引自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1頁。
[6]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適可齋記言》,中華書局1960年,第31頁。
[7]轉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7頁。
[8]楊天石:《帝制的終結》,岳麓書社2013年,第70頁。
[9]《中國財政史》第七卷《清代財政史》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2頁。
[10]《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
[11]英《泰晤士報》著,方激編譯《帝國的回憶——〈泰晤士報〉晚清改革觀察記》,重慶出版社2014年,第280頁。
[12]轉引自張功臣:《洋人近事——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外國人》,新華出版社2008年,第265頁。
[13]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67頁、666頁。
[14]《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8頁。
[15]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6頁。
作者:江蘇省工運研究所研究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