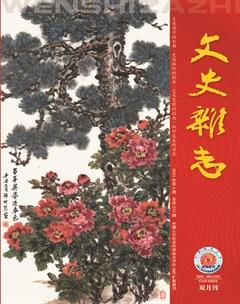五四知識分子的價值覺醒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摘? ?要:五四運動推動中國知識分子廣泛的價值覺醒,是中國近代以來飽受壓迫和剝削的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探求救國救民道路的必然結果,是中華民族思想演進的必經歷程。此后馬克思主義促成一大批先進知識分子更為深刻的價值覺醒并自覺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體力量。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必然成果,由此將中國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關鍵詞:五四;價值覺醒;馬克思主義;傳播
五四運動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掀開了中國革命、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中國道路的新篇章。辛亥革命前后,中國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面臨西方思潮的猛烈沖擊和中華傳統文化的激烈碰撞。以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倡導民主和科學為標志的新文化運動,帶來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啟蒙。五四運動應運而生,促成以個體的覺醒帶動群眾的廣泛覺醒,使學生運動擴展為全國爆發式的工人運動。此后,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優秀青年知識分子的共同信仰,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無產階級群眾運動登上歷史舞臺。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讓無產階級運動在組織上、政治上、思想上以排山倒海之勢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使五四價值擴大并影響到全國革命運動和中國未來的走向。中國這頭據說被拿破侖視為“沉睡的雄獅”真正覺醒起來。“五四運動成就和培育的一批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成為喚醒中國的主體力量”[1]。以出現一大批馬克思主義者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為標志,自鴉片戰爭以來近代中華民族的猛然覺醒,在五四運動以后得以淋漓盡致地體現。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當仁不讓地擔當起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歷史責任。
一、五四運動覺醒的內生和外在動力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長期遭受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和剝削。1919年春夏之交,在巴黎和會外交談判失敗的刺激下,由一批擁有共同信仰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推動的學生運動發展為上海等地的廣泛的工人運動并擴展到全國。這也是五四運動覺醒的內生和外來的動力,表現為徹底的毫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
一般認為,近代中國覺醒的三次表現是:“第一次是1840年開始的兩次鴉片戰爭失敗后出現的同治中興(1861—1874);第二次是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后興起的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等;第三次即是五四新文化運動。”[2]西方以侵略戰爭的方式撞開中國近代化的大門,中國不得不被動地尋求應對之策。兩次鴉片戰爭給中國領土、主權帶來了威脅,中國逐漸成為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和原料市場。遭受壓迫和剝削之苦的近代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讓中國人對西方有了新的認識,遂開始以洋務運動尋求自強之術。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促使先進的中國人再次醒悟。當時的先進之士認識到僅僅靠堅船利炮不足以達到拯救中華民族的危機,由此歐美及成功效法西方國家制度的日本便成為他們學習的對象。戊戌變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是中國人民覺醒的一系列嘗試,只是在當時飽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雙重壓迫下的資產階級的這些改良和革命并未見到巨大的成效。一次次的覺醒雖然帶動了中國部分知識分子的思想解放,為更進一步接受激進的思想啟蒙打下了一定基礎,但是中國仍然處于帝國主義和封建官僚主義的殘酷壓迫之下,中國廣大群眾中的封建的、愚昧的和腐朽的思想仍舊沒有大改變。當然也要看到,辛亥革命畢竟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以陳獨秀、李大釗等為代表的接受過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教育的先進知識分子,不再滿足于學習西方的器物、技術、制度。他們認識到中國封建思想的長期束縛,開始從傳統文化入手,力圖以激進的文化清理來解放人們的思想,以求達到與西方齊平的高度,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和民族自強。“這個動向表明,鴉片戰爭后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實踐探索,五四運動前的先進中國人站到了重新選擇救國道路的十字路口。”[3]五四前的近代中國的歷史表明,先進的中國人經歷了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醒悟,一次醒悟比一次來得更激進、更猛烈。近代愛國志士覺醒的動力在于不滿中國的現狀,要去實現民族的獨立自強,因而在外來壓迫剝削面前,展現出強大的民族自省力、自強力及抗爭力與凝聚力。這就是五四運動之所以爆發的強大的內在力量。
五四知識分子的覺醒與新文化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十月革命息息相關。內與外的結合,使五四運動由學生開始,影響到工人階級罷工斗爭,成為廣大人民群眾普遍參與的運動。這便有別于以往少數精英階層的運動,無疑拓寬了覺醒的廣度和深度。從近代以來的歷史發展進程來看,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必然結果,也是中華民族思想演進的必經歷程。
二、青年知識分子共同信仰塑造下的價值覺醒
五四運動動力的背后是覺醒的主體即受西方潮流沖擊和對中國文化予以重新審視的先進青年知識分子,包括學生。他們也是民族救亡圖存的領導主體。他們力求在民族現實困境與群體身份認同需求的雙重壓力下樹立共同信仰,也就是說“封建中國垂死掙扎的過程,是中國傳統儒家知識分子進行一系列政治抗爭的過程,也是中國新型知識分子群體尋求新身份認同的過程”[4]。
在19 世紀末20 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面臨很多選擇,西方各種思潮如進化論、自由主義、新村主義、社會主義等被譯介到中國。“十月革命使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李大釗、陳獨秀他們開始從‘西化向‘師俄的文化新范式轉換,逐漸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和傳播者。”[5]李大釗、陳獨秀在西方文化沖擊下,通過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深刻思考,進行了艱難轉型,從而完成由達爾文進化論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轉化,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群體覺醒的核心人物和領導者。他們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掌舵者,引領了更多知識分子的價值覺醒。
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鋒。當時他作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在1915年創辦《青年雜志》,舉起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向封建傳統思想開戰。新文化運動的劃時代意義在于:“在此之前,無論是立憲派還是革命派,從沒有一個人敢與中國文化開戰,就有也不敢十分堅決,新文化運動把大家的思想傳統改變了”[6]。中國近代以來知識分子轉型的代表,有戊戌維新時期的康有為、梁啟超等資產階級維新派人士,也有孫中山、黃興等有海外留學經歷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人士,還有同樣具有海外留學經歷而成長于國內新式教育環境的李大釗、陳獨秀這一代新型知識分子。他們對民主主義的表現更積極、更為徹底。他們認識到,要推動中國走上更徹底革命的道路,必先清理思想文化上的障礙,已達破舊立新之效。五四運動使部分知識分子看到了中國人民強大的團結力量和毫不妥協的決心和毅力,看到中國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和潛在力量。1919年6月陳獨秀被捕事件,與新文化運動、剛發生的外交失敗、五四學潮相聯系,喚起更多知識分子對當局予以痛斥,嚴厲抨擊北京政權。新文化界也因之為自身塑造新的社會價值理想。“現代人道主義的徹底改造方案引起廣泛關注和參與,魯迅也高調肯定人道的勝利。”[7]李大釗則提出了現代人道主義的社會全面改造理念。一大批知識分子的價值覺醒煥發出中國革命無窮的生機。
李大釗一直在尋求徹底解決世界和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作為人類歷史新紀元的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入中國。在五四運動中及以后不久,李大釗即以先進知識分子的敏銳性表達了一些新的思考。他以于1919 年、1920 年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進行了向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轉換。陳獨秀也在這一時期進行了向馬克思主義的轉換。以五四運動為標志,中國革命完成了由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的轉型,馬克思主義成為先進知識分子的共同信仰。知識分子的主體轉型,使他們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轉變為傳播主體,由此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的時代,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和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指明了新的方向。五四人文價值的覺醒,召喚出更多中國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參預革命。尤其是無產階級隊伍的壯大,使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經歷了主體意識的調整、適應和認同以后,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者,成為由思想啟蒙到社會變革的主體性力量。
三、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創新性發展
五四運動的爆發改變了新文化運動的方向,即由五四以前大力傳播“民主”和“科學”轉向熱情研究、宣傳并運用馬克思主義。“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探求救國救民道路,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注入新的活力。中國的大多數知識精英從小受到新式西學教育的影響,或有過海外求學經歷,對祖國飽有熱愛之情。十月革命使他們的目光從歐、美、日轉到向俄國學習,走社會主義革命道路,進而對馬克思主義有了新的認識。毛澤東、周恩來、李達、蔡和森、瞿秋白、惲代英等也積極呼吁和號召成立中國共產黨,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他們在五四運動后紛紛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說:“在‘五四以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8]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令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主體由純粹的知識分子轉向為集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于一體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他們通過翻譯介紹、著書立說、出版刊物、宣傳和社會教育等,把民族覺醒引導到人民大眾中,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核心主體。
五四運動把學生運動、工人運動擴大到更為廣泛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全方位的覺醒。從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成立,馬克思主義完成了思想理論介紹和在中國的實踐行動的統一,成為中國革命道路的指導思想。不同于以往諸如李提摩太、蔡爾康、梁啟超、劉師培、孫中山及其追隨者的非馬克思主義者傳播方式,毛澤東等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經過20世紀一二十年代革命大風暴的洗禮,迅速成長為腳踏實地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在斗爭實踐中不斷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提出農村包圍城市、工農武裝割據等思想,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使馬克思主義得以在中國創造性地發展。
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同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長達28年的艱苦卓絕的斗爭,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以后,又迎來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期間,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實踐化始終貫穿其中。黨的十八大以后,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正在中國土地上顯示出巨大的真理威力和強勁生命力。
注釋:
[1][4]邢云文、韓曉芳:《召喚、動員與五四知識分子主體的覺醒》,《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2]【美】費約翰:《喚醒中國: 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72頁。
[3]齊衛平:《五四運動結緣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敘事》,《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9年第2期。
[5]鄧紹根、張文婷:《馬克思主義在華早期傳播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萌芽》,《新聞與傳播評論》2018年第3期。
[6]梁漱溟講,陳政記:《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講演錄》,《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581頁。
[7]張先飛:《五四前期“新青年”派現代人道主義“公同信仰”形成考論》,《史學月刊》2017年第6期。
[8]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頁。
作者: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