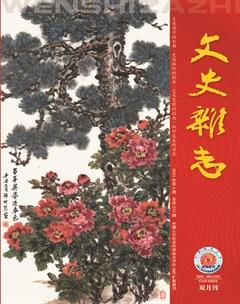論“成都”得名研究中的資料誤導
李殿元
摘? ?要:在“成都”得名的研究中,《太平寰宇記》關于“成都”二字的解釋被廣泛引用,形成訛傳、誤導。需要明確的是,《太平寰宇記》不僅對“成都”的解釋有誤,而且它也不是唯一、最早對“成都”進行解釋的古籍。比《太平寰宇記》稍早一些的《太平御覽》才最早對“成都”作出解釋,雖然它的解釋也極為牽強。
關鍵詞:成都得名研究;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訛傳誤導
上世紀80年代,學術繁榮,有關“成都”得名問題的研究一再被學者涉及。先是任乃強于《社會科學研究》1980年第2期發表《成都》;接著,李金彝、王家祐于《地名知識》1980年第4期發表《成都考》;然后,溫少峰、任乃強于《社會科學研究》1981年第1期分別發表《試為“成都”得名進一解》《贊同〈試為“成都”得名進一解〉》二文。
任乃強先生在《贊同〈試為“成都”得名進一解〉》文中,寫道:
成都這個地名,最先出現在《戰國秦策》。原文為“西控成都,沃野千里”。后世因為蜀國都城就叫成都,便分別把蘇秦所說這個“沃野千里”定為蜀國之地,而把“成都”二字定死為蜀國都城的專稱了。從公元前316年秦滅蜀,置成都縣起,迄今二千二百九十六年來,只北宋初年樂史撰的《太平寰宇記》解釋過成都二字的取義。他說:“成都縣,漢舊縣也。以周太王從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
任乃強先生所引《太平寰宇記》關于周太王“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的資料,后來被“成都”得名問題研究者認同,在所撰文中一再引用。這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任乃強先生是著名歷史學家,他引用資料應有較高可信度;二是《太平寰宇記》有200卷,即使中華書局2007年的現代印刷版本也厚達九大冊,訂價460元,不是一般學者可以常備的。因為對任乃強先生的信任,所以后來的引用者,便大多沒有去查對原文。
不過,后來的研究者卻似乎忽視了這么一個情況,即任乃強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已經是90高齡的老人了。他在寫《成都》《贊同〈試為“成都”得名進一解〉》這兩文時,就聲明過:“關于成都城的發展歷史,此僅憑記憶所及考訂一些有關地名的取義,供修史者參考。未暇翻檢書史,詳作考證。愿得拋磚引玉,征求不同意見,更作分別討論,期于折衷允當。非敢自限于此也。”[1]任老先生自己都說他的引證,“僅憑記憶……未暇翻檢書史,詳作考證”,可是后來者卻貪圖便宜,未經查證就以再引證,遂使“成都”得名研究的資料誤導更加嚴重了。
任乃強先生關于“成都這個地名,最先出現在《戰國秦策》。原文為‘西控成都,沃野千里”之言,就不準確。《戰國策》中其實并沒有“西控成都,沃野千里”這樣的字詞。在《戰國策》的《秦策一》有《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文,其中有“沃野千里”這四個字,卻無“西控成都”四字。考查古代典籍,依筆者所見,“西控成都”這幾個字是在明代如《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明太祖寶訓》《明史紀事本末》等典籍中才出現的。[2]
任乃強先生說:“從公元前316年秦滅蜀……只北宋初年樂史撰的《太平寰宇記》解釋過成都二字的取義”,這句話也不太準確。因為在歷史上“解釋過成都二字的取義”不只是《太平寰宇記》,還有《太平御覽》和《方輿勝覽》;而且,歷史上最早對“成都”二字進行解釋的也不是《太平寰宇記》而是《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是宋代著名的類書,由李昉、李穆、徐鉉等學者奉敕編纂。該書采以群書類集之,以天、地、人、事、物為序,分成55部,共引用古書1000多種,保存了宋代以前的大量文獻資料(其中十之七八已經亡佚),遂使本書顯得彌足珍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遺產。
《太平御覽》的領銜編撰者李昉(925—996),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宰相之一),學識淵博,除參與編寫《太平御覽》外,還與他人合作編寫了《舊五代史》《太平廣記》《文苑英華》等。以他為首的14位學者在宋太宗太平興國時期奉敕編撰的《太平御覽》搜羅宏富,被后人譽為輯佚工作的寶山;但是其粗疏也相當嚴重,主要體現在征引材料不夠謹嚴,引書字句往往與原文不符。
《太平寰宇記》是北宋的地理總志,全書約130余萬字,是繼唐代《元和郡縣志》以后出現的又一部歷史地理名著。就其資料的原始性和豐富性而言,在研究唐末宋初的政區沿革、經濟活動、文化風俗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太平寰宇記》的作者樂史(930—1007),是北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和文學家。他早年在南唐作過秘書郎,宋滅南唐后,入宋,任主簿、知州等地方官,并數度在史館任職。樂史仕宦近60年,從政之余,勤于著述,前后著書20余種、690余卷,另有文集《洞仙集》100卷。《太平寰宇記》是這些著述中價值最高、影響最大的一部作品。但是,它同《太平御覽》一樣,粗疏也不少。
《太平御覽》卷一百六十六《益州》說:“《史記》曰:‘周太王逾梁山,之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有成都之名。”[3]
《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二《益州》下則說:“成都縣,漢舊縣也,以周太王從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4]
《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兩書均言“成都”得名是因為周太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這就犯了牽強附會的錯誤;而《太平御覽》甚至還說其有依據,稱這是《史記》里講的。可是我們查《史記·周本紀》說到周太王時,只有“逾梁山,止于岐下”這幾個字,并無“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句;而在《史記·五帝本紀》中講到舜帝時,才有“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等語。
李昉、樂史之后兩百多年,南宋人祝穆似乎發現了李昉、樂史等人關于“周太王”的錯誤,他在《方輿勝覽》中,予以了糾正,但不知何故卻在該書“成都府路”條中仍然采用李昉、樂史的說法,認為“成都”的得名“蓋取《史記》所謂三年成都之義。”[5]所以,李昉、樂史也好,祝穆也好,他們關于“成都”得名的解釋是靠不住的。
還有的研究者甚至將《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兩書有關“成都”得名的記載混在一起說:“《太平寰宇記》:‘《史記》曰:漢舊縣也,以周太王從梁山止岐山,一年成邑,三年成都,因之名曰成都。這句話的解釋是司馬遷借用西周都城建立的歷史經過,說周太王從梁山到了岐山。而后一年建成了縣邑,三年便構筑了完整的都城。這是北宋地理學家樂史所提出的觀點,而目前也被很多人所贊同。”[6]
其實,上述引文不僅僅是將《太平御覽》與《太平寰宇記》攪在一起,而且亦將《史記》中的《五帝本紀》和《周本紀》攪在一起,偽造出一條周太王“止岐山”而“三年成都,因之名曰成都”的史料。且不說偽造史料屬于學術不端;即便真的存在這條史料,它又與戰國末的蜀地成都有何相干呢?要知道司馬遷在《五帝本紀》里的“三年成都”云云,是就城市形成過程的泛泛而談——或許可推想為周太王岐下建城之事,但與千年后的成都得名卻并無必然的邏輯聯系。(如果有,則當年岐下所建之城就該叫成都,而輪不到秦惠王二十七年仿咸陽而筑的蜀城了。)
筆者過去也曾受到舊時“成都”得名研究者的誤導,在《論秦征服古蜀與“成都”得名》《論“成都”得名研究中古蜀情結與秦文化的糾結》[7]等文中使用了上述有錯訛的引文。在此對讀者深表歉意。
話又說回來,《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是差不多同時代的著作,為什么要說《太平御覽》才是歷史上最早對“成都”二字進行解釋的著作呢?
應該知道,《太平御覽》撰始于北宋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三月,成書于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十二月。這在許多同時代的書籍中都是有記載的。
《太平寰宇記》則成書于雍熙(公元984—987年)末至端拱(公元988—989年)初,比《太平御覽》至少晚4年。其初刻本極少,流傳不廣,到明代海內宋板已無蹤影;明末清初刊本不一,已殘缺不全,無足本。中華書局出版的《太平寰宇記》在“前言”中明確說:“本書大寧監原附南宋人所作校勘記云:‘按今圖經,開寶六年置監,端拱二年以大昌縣來屬。詳此,則置監時,縣猶屬夔州,而今記作于大昌縣未來屬之前也。則書撰成于雍熙末至端拱初之間。就書中所載內容考躊,政區建置主要以太平興國(976~983年)后期,即太平興國四年滅北漢后的簿籍為主要根據,又修改補充了雍熙(984~987年)、端拱(988~989年)時期的政區建置,書載袁州分宜縣于雍熙元年置,建安軍領永貞縣于雍熙三年由揚州割屬,寧邊軍置于雍熙四年,通利軍置于端拱元年,凡此皆是。”[8]
在2018年同時獲得第十五屆“上海圖書獎”、第四屆出版政府獎的《大辭海》(2009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是這樣言及《太平御覽》和《太平寰宇記》的:
太平御覽 簡稱《御覽》。類書名。宋太宗命李昉等輯。初名《太平總類》,經太宗按日閱覽,改題今名。始于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成于八年。一千卷,分五十五門。引書浩博,多至一千六百九十種。其中漢人傳記一百余種,舊地志二百余種,現均不傳。
太平寰宇記 北宋地理總志。樂史編著。二百卷,目錄二卷。撰成于雍熙末至端拱初期間。而政區建置主要是太平興國后期,又修改補充了雍熙、端拱及淳化時期少數建置。取太平興國年號首二字為書名。作者雜取山經地志,纂成此書,始于東京,終于‘四夷。五代后晉割讓契丹的幽、薊十六州,仍列其名,以表達時人恢復燕云志愿。采摭繁富,惟取賅博。府、州排列,以當時所分十三道為準,除因襲《元和郡縣志》門類外,又增加風俗、姓氏、人物、土產、四夷等門,為后來總志體例所沿據。所載唐以前地志佚文,可補籍缺略。今本佚去八卷,《古逸叢書》刊有楊守敬從日本輯回五卷半。[9]
《大辭海》對二書完成時間的定位乃經過嚴謹的考訂,是可以相信的。
所以,在有關“成都”得名問題研究中前述被廣泛引證的那段周太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的資料,應該是《太平御覽》最早發布,而《太平寰宇記》則稍后;雖然二者對“成都”得名的解釋均極牽強。
注釋:
[1]任乃強:《成都》之注釋24,載《社會科學研究》1980年第2期。
[2]參見拙文《論蒲江“成都矛”解讀中的幾個問題——六論成都得名是在秦統一古蜀后》,載《文史雜志》2017年第3期。
[3](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一百六十六《益州》,中華書局2000年版。
[4](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二《益州》下,中華書局2007年版。
[5](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五十一《成都府路》,中華書局2003年版。
[6]成都民間歷史:《一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從何而來?》http://www.cdsouth.com/chengdu-photos/8627.html.
[7]拙文《論秦征服古蜀與“成都”得名》,載《成都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論“成都”得名研究中古蜀情結與秦文化的糾結》,載《文史雜志》2015年第2期。
[8](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之《前言》,中華書局2007年版。
[9]《大辭海》“太平御覽”條、“太平寰宇記”條,見《大辭海》之《中國古代史卷·中國史學史·史料》,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版。
附記:對于本文的思考和撰寫,要真誠地感謝《文史雜志》主編屈小強先生。我經過幾年努力,完成了“成都”得名系列研究,在論文集結出書之前,請學術功底深厚、嚴謹的小強兄為其作一次學術把關。他在逐字審核我書稿的同時發現了“成都”得名研究者對《太平御覽》的忽視和對《太平寰宇記》的錯誤引用。我們幾經討論,產生了這篇文章的主要觀點,撰于此,一是補“成都”得名系列研究之不足,二是感激小強兄對我不吝其力的無私幫助。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文史研究館退休干部,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