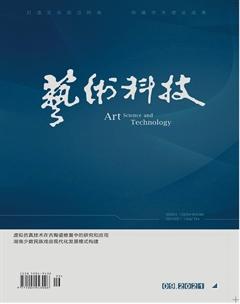“他塑”與“自塑”:好萊塢電影中華人男性形象構建的類型及啟示
摘要:20世紀的好萊塢電影先后塑造了傅滿洲、陳查理和李小龍三位經典的華人男性形象,并在“他者塑造”中憑借其全球流通性影響著西方乃至全球對華人形象的認識。在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的今天,我國迫切需要提升影視作品的對外傳播能力并自塑華人形象。在“自我塑造”的過程中,加深國際合作和主動出擊都是必不可少的路徑。
關鍵詞:好萊塢電影;華人男性形象;國際影響力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09-00-02
西方對中國人的凝視與想象由來已久,美國的好萊塢電影可以稱為西方利用電影媒介塑造華人形象的主要陣地。好萊塢電影的創作者從不同形式的作品中汲取靈感,利用新興的電影語言實現對華人形象的建構[1],以此傳達對中國社會的看法[2]。人物形象是電影中極其重要的元素[3],縱觀20世紀好萊塢電影中的華人男性形象,具有代表性和深遠影響力的當屬傅滿洲、陳查理和李小龍三位。
1 二元結構語境下華人男性形象的嬗變
1.1 對華人男性祛魅的二元結構
1.1.1 “黃禍論”的代表:傅滿洲
20世紀初,傅滿洲以類似撒旦的形象隨著小說《神秘的傅滿洲博士》的發表邁進了西方世界。作為一個被妖魔化的負面形象,銀幕中的傅滿洲極其臉譜化:高高瘦瘦、穿著清朝服飾并留著長辮子和長指甲。在容易捕捉和記憶的特征中,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刻板思維逐漸形成,同時他們認為中國和中國人就類似傅滿洲,聰明又邪惡,即使年老體衰仍有著強大攻擊力,而他們則成了惴惴不安的弱者和反抗侵略的正義者。傅滿洲的出現符合19世紀末的“黃禍論”,作為“黃禍論”的代表,他也的確憑借14部電影的陸續問世產生了經久不衰的影響。
1.1.2 “模范移民”:陳查理
在傅滿洲風靡西方一段時間后,反對的聲音顯露頭角,厄爾·比格斯曾說:“視中國人為罪惡之徒的觀點早已過時了。”[4]隨后,他便創造了一個與傅滿洲大相徑庭的華人男性——陳查理。陳查理個子不高、身材肥胖且性情溫和,更關鍵的是他是為西方服務的偵探。陳查理的出現從表面上看是對窮兇極惡的華人形象的糾正,其實他是被美國文化同化并重新塑造的模范移民。19世紀中后期的美國涌入大批移民,好萊塢試圖以他為榜樣來規范其他移民,原因是陳查理仆人式的角色完全符合美國對溫良恭順的移民的需要。
1.1.3 二元對立結構的同一指向
傅滿洲和陳查理雖然在形象上大相徑庭,但有著不可忽視的共同點:都是被好萊塢祛魅的華人男性形象,是對華人的刻板印象和種族歧視。好萊塢塑造的這兩個被閹割的華人男性形象,一則褒一則貶,以二元對立的結構操縱著華人形象,利用影像傳播的溢出效應[5],最終形成一套完整的符合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話語策略,以此來維護西方人的優越地位。
1.2 對二元對立結構形象的有限消解
20世紀70年代,李小龍以犀利的拳腳功夫、充滿力量的陽剛身材打破了之前好萊塢銀幕上被陰柔化的華人男性形象。他不同于邪惡的傅滿洲,扮演的是正面人物;也不同于溫順的陳查理,他肌肉強健、拳腳凌厲。好萊塢對華人男性的祛魅從身體特征上入手,那么李小龍便利用好萊塢表現西方男性的話語策略,即追捧陽剛的男性氣質,通過表現自己的身體,開啟了自塑華人形象的時代。
不可否認,李小龍的走紅是對傅、陳話語的強力沖擊,但這樣的解構和重建也是有限的[6]。尤其是他在影片中仍延續了陳查理話語的無性化特征,即在情感方面對女性一直持有冷漠疏離的態度。雖然李小龍仍沒有走出無性化的禁錮,但他陽剛正氣的形象和其電影的成功都為華人在好萊塢獲得主體性和話語權做了重大貢獻。
2 影響電影中華人男性形象的因素
2.1 移民角度與“黃禍論”
19世紀末受國內戰亂和國外金礦吸引,大量中國移民涌入美國,而傅滿洲這一形象于20世紀初期形成,兩者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20世紀初,唐人街已遍布美國各大城市。華人移民與美國人有著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并在唐人街形成了獨特的社群。除了外貌和生活方式上與西方存有差異[7],華人在工作上的任勞任怨更是令美國人感到焦慮。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在美華人就受到公開性的歧視和殺戮。在這樣特殊的時代大背景下,美國的媒介開始大量涌現對于中國人的負面報道。
從移民角度出發,西方根深蒂固的“黃禍論”思維也無法忽視。1895年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聲稱自己做了一個佛祖騎著惡龍入侵歐洲的噩夢,他恐懼不已,隨即用“黃禍”來描述這種感覺。于是西方人把“黃禍”與當時的中國移民聯系在一起,從而把對中國移民的歧視深化為受到威脅的恐懼與排斥。藝術滲透帶有特定時代的功利性[8],此時,傅滿洲作為“黃禍論”思維的集中體現被好萊塢搬上了銀幕。
2.2 源于政治需要的話語轉變
20世紀的30~40年代,隨著二戰的爆發,日本暫時代替中國成為新一輪“黃禍”恐懼的實體,中國的身份由威脅西方的惡人轉變為聯合對抗日本的親密盟友。在新的歷史階段,美國更著重于表現一個對白人毫無威脅的仆人式角色。20世紀70年代,中美政治、經濟關系的轉變帶來了文化上的寬松環境,華人在好萊塢有了一定的主體性和發聲空間,再加上李小龍電影中多次出現的反抗殖民者的主題與反帝主義浪潮相吻合,其走紅也帶著必然性。
傅滿洲、陳查理和李小龍三者所代表的華人形象并不是互相代替,而是交織存在。20世紀前期,傅滿洲以企圖摧毀西方的邪惡面目出現;冷戰時期傅滿洲又以“反共”的面目出現。傅滿洲的形象可以被看作中美關系的現實映射[9],在中美處于政治和諧期時他會退居幕后,其他時刻又會根據美國的需要粉墨登場。
3 當代語境下對塑造華人形象的反思
3.1 華人形象建構的困境
20世紀好萊塢電影中的華人形象大多來自他者塑造,這和當時中國國家力量薄弱、華人在外話語權的缺失不無關系。然而即使21世紀以來我國國力逐漸增強、國際地位也有了顯著提升[10],但是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話語對抗式解碼的現象仍然層出不窮。電影媒介作為一種文化輸出的手段[11]和彰顯國家精神[12]的有力工具,其中所表現的華人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的國家形象,因此認清當前華人形象建構的困境及如何利用電影媒介進行形象的自我塑造成了一個重要課題。
在如今的華人形象和國家形象建構中,國際國內紛繁復雜的環境都帶來了巨大挑戰,一方面,他者對中國形象存在偏見和誤讀,一些西方國家用“中國威脅論”打壓我國;另一方面,我國國家形象要想實現真正立體化,還存在許多傳統與現代文化符號的矛盾沖突以及自身能力建設的不足。
3.2 塑造華人形象的路徑探析
解構西方對華人的刻板印象是我們的共同認知,但如何重新建構才是重點。利用電影媒介塑造華人形象的方法可以分為兩種:一是加強國際合作,尤其是與好萊塢電影的合作;二是主動出擊,增加本土文化自信[13],加快文化輸出的腳步,祛除中國傳統社會對于男女的刻板印象[14]。
在國際傳播背景下[15],無論當今的美國電影或是中美合拍片,很大程度上都是西方占主導地位。西方盡力開發中國資源,試圖利用中國元素、中國故事抓住中國觀眾[16],在表達中國文化的內涵上卻總是融入西方價值觀。以真人版電影《花木蘭》為例,中國觀眾認為《花木蘭》是對中國元素的堆積和濫用,雖然任用了許多華人演員,但人物塑造無法讓觀眾產生認同和情感投射[17]。從現實看,西方電影不會自覺改變對華人的刻板印象,因此加深國際合作,學習好萊塢電影的同時輸出中國元素和文化是減少文化誤讀和塑造正面華人形象的必經之路。
除了尋求中外合作,想要利用電影媒介塑造出真實、正面的華人和國家形象,還必須發揮中國電影的作用[18]。近年我國主動出擊,自塑華人形象的影片并不在少數。《戰狼》系列電影塑造了孤膽英雄[19],《紅海行動》和《流浪地球》顯現的是群像式英雄[20]。然而群像式英雄往往代表集體的力量,與西方個人英雄主義[21]不符,從而產生文化折扣;《戰狼》又曾被國外觀眾質疑“太虛假”,不是中國的真實縮影[22]。藝術作品,主要是作者想讓觀眾感知什么[23],或許爆紅于國內外社交網絡的李子柒能給予我們新的啟示,由高高在上的廟堂式傳播和臉譜化形象展示[24]轉向小人物的刻畫在華人形象的塑造和提高觀眾認可度上[25]更為深入人心。
4 結語
20世紀,西方的強勢話語操縱著銀幕上的華人形象的近百年時間里,好萊塢不間斷地凝視與想象中國并建立起以美國文化為主導的全球觀。認清歷史是前提,重要的是中國的影視劇不能再在國際舞臺上失語,將國際領域華人形象的塑造權拱手讓給西方傳媒。鑒于此,我國必須通過加強國際合作以及主動出擊的自塑華人及國家形象的方法,打破好萊塢電影的思維定勢,建立起屬于新時代的正面華人形象和國家形象,讓世界聽到、看到、感受到真實的中國。
參考文獻:
[1] 黃霽風.議程設置理論下的電影話語分析[J].東南傳播,2019(01):40-43.
[2] 杜彥潔.電影作品的敘事特色分析——以侯孝賢電影為例[J].漢字文化,2019(03):36-37,48.
[3] 位云玲.法國電影《觸不可及》的人物角色分析[J].漢字文化,2020(12):124-125.
[4] 常江.從“傅滿洲”到“陳查理”:20世紀西方流行媒介上的中國與中國人[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7,24(02):76-87,127-128.
[5] 李惠敏.助力鄉村文化自信:涉農紀錄片的當代價值研究——以記住鄉愁為例[J].東南傳播,2020(06):35-37.
[6] 呂志文.構建與解構:“男性向”網絡小說改編劇分析[J].藝海,2020(07):82-83.
[7] 丁月明.危機與轉機:網絡綜藝節目敘事策略的優化——以《心動的信號》為例[J].戲劇之家,2019(16):222-223.
[8] 王全權,周碧琬.論國產動畫電影中傳統文化的美學價值及其影響——以動畫電影《大魚海棠》為例[J].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20(04):17-21.
[9] 位云玲.觀察類綜藝節目走俏的原因探究——以《我家那閨女》為例[J].藝術科技,2019(03):115,128.
[10] 位云玲.原創文化類綜藝節目持續走紅的原因探究——以《上新了!故宮》為例[J].藝術評鑒,2019(07):169-170,76.
[11] 黃晶晶.電影藝術中的傳統文化承創——《Three Idiots》[J].戲劇之家,2019(22):102,104.
[12] 杜彥潔.淺析美國電影新英雄形象——以《蝙蝠俠:黑暗騎士》為例[J].大眾文藝,2019(08):158.
[13] 李惠敏.經營體驗類綜藝節目的敘事特色分析——以《潮流合伙人》為例[J].漢字文化,2020(10):179-181.
[14] 丁月明.中國傳統文化視域下電影女性形象塑造分析——以電影《霸王別姬》為例[J].戲劇之家,2019(15):83-84.
[15] 王瑩.國際傳播背景下美國華語電視節目研究[J].戲劇之家,2019(16):89-90.
[16] 石姝敏.電影中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研究——以
電影宣傳片《啥是佩奇》為例[J].戲劇之家,2019(16):104-105.
[17] 王燦,馮廣圣.情感喚醒與鄉村認同:從《向往的生活》看慢綜藝熱[J].新聞知識,2020(07):62-65.
[18] 尤旖蕓.基于受眾角度探究國產電影的發展方向——以《我不是藥神》為例[J].戲劇之家,2018(31):57-58.
[19] 羅峻峰.新時代主旋律電影創作的問題與對策[J].藝術科技,2019(15):103-104.
[20] 陳芳芳.試論電影《流浪地球》中的生態美學思想[J].藝術評鑒,2019(11):158-159,185.
[21] 孫志宇.《血戰鋼鋸嶺》——真實的戰爭,耐人尋味的英雄主義[J].戲劇之家,2019(22):103-104.
[22] 張嫚.社會化媒體對家庭倫理劇的撕裂與彌合——以電視劇《都挺好》為例[J].藝海,2020(08):96-97.
[23] 杜彥潔.淺析張藝謀電影作品中的色彩運用[J].戲劇之家,2019(06):75-77.
[24] 朱克迎.姜文電影的人物形象美學賞析[J].戲劇之家,2019(06):85-86.
[25] 王燦.以《風味人間》為例探究飲食文化類紀錄片傳播新走向[J].戲劇之家,2019(15):79-80.
作者簡介:李宇童(1998—),女,安徽滁州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新聞與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