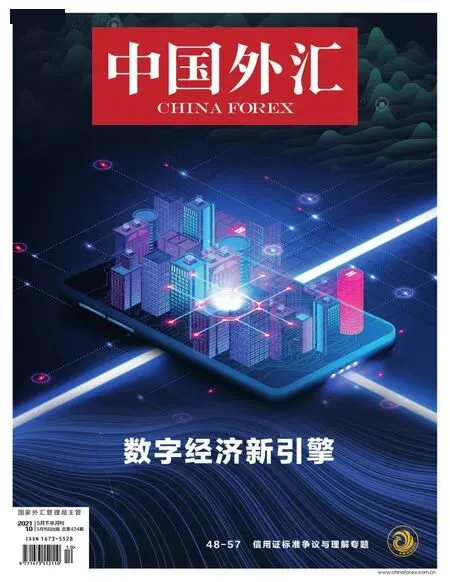數字經濟增長的本質之辨
文/程實 高欣弘 編輯/白琳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數字經濟已經滲透全球經濟運轉的每個細枝末節。宏觀經濟層面,據中國信息通訊研究院的計算,2019年全球數字經濟占GDP的平均比重達42%,其中高收入國家更積極地參與了數字經濟轉型(見附圖)。微觀企業層面,過去20年數字經濟企業一躍成為全球市值的引領者,2020年全球市值前十的企業中有八家是互聯網企業。
中國經濟正值減速增質的關鍵轉型期,告別要素依賴型的增長模式,數字經濟接棒成為增質的主動力。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占GDP的比重達到39%。在成長性日益稀缺的資本市場中,數字經濟已成為A股成長性的重要來源。唯有把握數字經濟的增長本質,方能正確理解數字經濟時代之所謀所求,從而有的放矢地安排資源傾斜,在全球數字經濟的競爭新局中掌握主動權。
數字經濟的價值創造之錨
傳統經濟在存量博弈下呈內卷化狀態。其成因在于制造業相對需求不足,而經濟總量所掩蓋的分配失衡也導致了長期潛在產出下滑、社會結構畸形和地緣政治動蕩。數字經濟則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模式變革,自動化與機械化對勞動力市場產生了替代性沖擊。從這一維度出發,我們不應將數字經濟簡單地與技術進步畫上等號,更為關鍵的是,數字經濟重新定義了價值創造的過程。

全球數字經濟格局(2019年數字經濟占GDP比重)
傳統經濟的增長之錨實質是物,簡單重復的勞動力也屬于被物化的人力資源;而數字經濟換錨為人,以數據衡量出人的創造力、影響力乃至行為習慣的潛在價值。如果說傳統經濟是以物權、債權、土地使用權為核心的存量分配體系,那么數字經濟則是以人的創造力、影響力、技術知識等作為數權核心資產的流量分配體系。因此,數字經濟所帶來的增長可以不受現實資源與物理空間的限制,幫助我們擺脫存量博弈的囚徒困境。
具體來說,數字經濟在價值創造的過程中,呈現出與傳統經濟相反的凹凸性。在初始階段,傳統經濟的要素投入產出幾乎成正比,以消耗實物資源換取經濟快速增長;但在資源瓶頸顯現后,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遂難以為繼,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與之相反,數字經濟的初始投入,較難產生即刻收益,現代信息網絡的建設、用戶數字習慣的培育以及算法算力的突破,都需要耗費大量的資金、時間與人力。區別于“即投即用”的傳統生產方式,數字經濟存在收益“真空期”,唯有基礎設施初步成型之后方能啟動價值創造。值得關注的是,一旦邁過這一階段,由于數據的邊際復制成本幾乎為0,其作為生產要素不具有排他性,數字經濟能夠打破傳統生產要素邊際收益遞減的陷阱,展現出“指數級上升”的價值驅動路徑。
數字經濟的增長本質
基于數字經濟的價值創造路徑不難發現,發展壯大數字經濟的關鍵有二,第一是基數,關乎基礎設施的完備度和先進度。例如,便捷的通信網絡和普及的智能手機是消費互聯網爆發式增長的根基。第二是指數,關乎后續增長的潛力與空間,唯有不囿于存量,不斷開發增量市場,才能釋放出行業更充裕的發展空間。過去十年,數字經濟的發展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隨著流量紅利尾部展開期的特征逐步顯露,基數和指數能夠發揮的作用開始受到局限,亟需灌注新的生命力。
穩固基數的對策是謀求強大的數字化生產力。上一輪技術紅利為消費互聯網的滲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面向更高數量級的工業互聯網,更強大的數字化生產力是不可或缺的支撐。2020年3月,政治局常委會提出了新基建的七大方向,其中5G、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即數字基礎設施是發展重點。長期以來,市場分散和產能利用率低是傳統制造業懸而未決的痛點。據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2020年全年,工業產能剩余比超過25%。而消費互聯網的加速進化推動定制化、個性化需求浪潮,“小單快返”成為行業運營趨勢,致使制造業供需匹配的鴻溝進一步加大。過去制造業的數字化程度持續處于低位,主要原因在于其復雜程度更高,不僅產業鏈條冗長,需要考慮對物料、工具、人力、資金等上下游不同資源的組織,企業之間還存在多方利益的博弈,商業信息的機密性與數量級均不在同一層次。中心化設計的互聯網技術重在連接人,而對實物資產連接不足,算力也無法承載巨大的工業信息流。如今物聯網、云計算和區塊鏈技術能夠突破這一障礙,在提供基于多方共識的完整加密信任機制之余,以分布式計算方式加強了海量信息的處理功能。伴隨新基建支撐起產業互聯網的運行框架,制造業企業上鏈形成網狀拓撲結構,實現供需的精準調度與匹配,將逐漸成為主流模式。
提升指數的對策是謀求對等的數字化生產關系。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數字經濟生產力乘數效應的發揮,有賴于生產關系的妥善處理。數據的網絡壟斷性引致了三重不對等,即中小企業與大型企業的競爭地位不對等、用戶與企業對數據的控制權不對等、數字強國與數字弱國的規則制定權不對等。脫離了公平開放的競爭環境,數字經濟的指數效應將逐步衰減。因此,除了實體經濟部門自身積極推動數字化轉型,更需要監管對于整個產業秩序重塑發揮引導作用。當前,數字監管從平臺反壟斷、隱私保護和數字稅等方面入手,表面為約束,實為鞭策,意在謀求數字經濟時代的機會均等、規則均等與權利均等,以此釋放出數字生產的巨大潛力。
數字經濟下一站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往往處于利益分配的動態平衡之中。一方面,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創造的價值并不能與實體經濟割裂。從商品構成角度看,數據價值的確擠占了人力、生產性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創造的價值,但其加總價值卻有所提升。伴隨技術進步和生產成本的大幅下降,傳統生產要素所賦予的價值自然日漸走低。因此,數據價值創造的實質是對傳統經濟利益分配的矯正。另一方面,數字經濟過熱也會實現自我平衡。當人的創造力、影響力的價值無限被抬高時,大規模勞動力將不斷流入這一領域。與之相應,商品的生產商將成為稀缺資源,引導最終利潤由數據向傳統生產要素回歸。在數字化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全面重塑之下,這一過程不再是簡單的倒退式回歸,而是將激發出產業互聯網的潛力,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或將呈現出三大全新態勢。
第一,追求從消費者到生產者的對稱性普惠。中國數字經濟的上個十年是消費互聯網的黃金時代,變革主要發生在產品市場(即居民部門向企業部門購買商品的過程基本實現數字化)。其初衷是將互聯網服務近乎無差別地傳遞至每一個人,實現某種程度的機會均等化。但若用經濟學模型稍加分析便可明白,這實質上是一種非對稱的普惠。其一,雖然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整體福利獲得長足提升,但是原有生產者卻因為生產門檻的降低而受到利益侵害。其二,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等新技術持續提升勞動生產率,加劇了不同經濟部門之間的貧富差距。其三,具備流量先發優勢的大型平臺擠壓了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發展后期或出現為了追逐利潤而損害實體經濟發展的情形。因此,數字經濟的下半場將從產品市場轉移至要素市場(即企業部門在生產商品的過程中運用數據),原有生產者有望通過打開實體商品的數字空間重獲市場機會,而企業發展路徑也將更多元化。數字化商品融合了數據與傳統商品的多重特征,也將賦予傳統商品新的數字內涵。
第二,拓展從連接人到連接資源的新六度空間。在消費互聯網時代,互聯網企業是六度空間理論的突出踐行者,激發出社交網絡的巨大價值。值得注意的是,產業互聯網時代將不再局限于人的六度空間,而傾向于釋放全部資源連接與整合的潛力。由此可以預見,產業互聯網的一大革命性變化,可能是傳統企業上下游的縱向聯系將拓展為網狀拓撲結構。其中,聯盟鏈就是新六度空間的一項成功試驗,原本并無明顯交集的企業共處于一個技術支持的互信環境下,實現數據使用整個過程的透明可監督,進行更深層次的多維業務探索。
第三,打造從流量到誠信的合作型共識。原有六度空間以連接人為主,因而流量被視為核心,平臺經濟的發展模式相對固定,即壟斷流量形成排他性的社區生態,擠出其他企業的競爭機會。而當從人的六度網絡拓展到商品、企業乃至更多資源時,流量的不可取代性將會大幅降低,代之以如何連接更多資源、創造合作共贏價值的共識。因此,產業互聯網將擺脫“燒錢”模式,拉開從競爭博弈走向合作信任的序幕,以互信互惠探尋增量業務價值。在產業互聯網中,企業之間的交易量級將遠超消費領域,因此建立一個切實可信的共識環境尤為重要。當前,數字人民幣正在探索企業級支付應用,結合區塊鏈技術全程可追溯的特性,料將成為釋放數字潛能的關鍵性基礎設施。如果說消費互聯網時代致力于通過快速傳遞消除信息不對稱,那么產業互聯網時代則是通過追根溯源確保信息的真實性。倘若每個市場參與者能在自動化技術支持的共識機制下建立起信任關系,社會整體效率將大幅提高,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的“量價齊升”時代也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