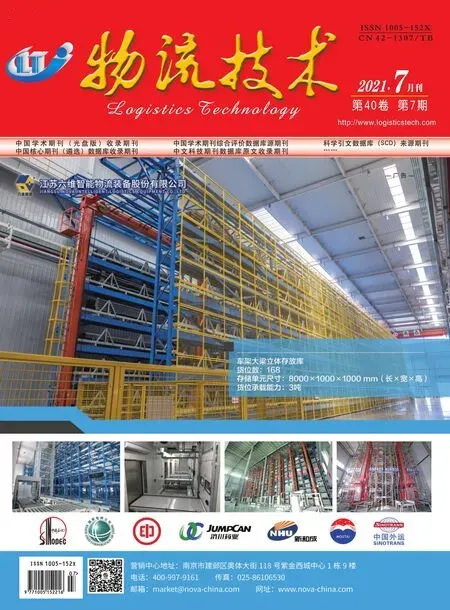考慮垃圾分類的供應鏈網絡模型
李亨英,王桂學
(太原科技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山西 太原 030024)
0 引言
生態環境部在《2019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年報》中指出,2018年我國產生一般工業固體廢物15.5億t、工業危險廢物4 643.0萬t、醫療廢物81.7萬t,大量的垃圾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為減少污染物排放,國家早在2016年就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簡稱《環保稅法》),對企業生產過程中產生垃圾的處理提出了硬性要求;2020年再次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簡稱《固廢法》)更是加大了對違法排污行為的懲處力度。因此,在《固廢法》“誰產廢、誰治理”的責任規定下,企業在確定生產運營決策的同時還需要考慮生產過程中產生固體廢棄物垃圾的處理問題,以減少固體廢棄物垃圾(以下簡稱垃圾)對環境的破壞。
在國家政策的要求下,大量企業紛紛采取相關措施降低自身排放的垃圾對環境的影響。部分企業通過廢品回收來降低垃圾對環境的破壞。存在大量研究企業廢物回收的文章,如Diabat,等[1]建立了考慮廢品各零部件質量水平、經濟價值和對環境的影響程度的廢品回收模型,并從政策監管的角度研究了不同政策監管制度對供應鏈企業經濟與環境績效的影響;Zheng,等[2]建立了由制造企業、零售企業和廢品回收企業組成的雙渠道閉環供應鏈系統,分析了產品銷售渠道和企業主導效用對產品回收效率及企業績效的影響;Ma,等[3]考慮制造商承擔回收廢品的職責,構建了由三個制造商與一個需求市場組成的三寡頭閉環供應鏈模型,分析了某一制造商回收價格波動對其他制造商利潤的影響。
部分企業通過綠色技術投入減少垃圾的產生。大量學者研究了綠色技術投入對企業的影響,如周輝,等[4]考慮政府環保法規對企業實施綠色制造的影響,構建了由單個制造商和單個零售商組成的供應鏈模型,分析了市場潛在需求、消費者環境意識等因素對產品綠色創新決策(產品綠色研發投入、綠色創新水平等)與產品定價的影響;曲優,等[5]針對消費者綠色偏好對產品需求的影響,考慮制造商通過綠色研發生產綠色環保產品,零售商通過廣告等手段宣傳產品綠色信息,構建了由單個制造商和單個零售商組成的供應鏈模型,在集中與分散決策模式下,求解了使系統最優的產品綠色水平、廣告宣傳水平和利潤;呂寶龍,等[6]在碳稅背景下,解決了制造企業增加綠色產品研發成本與降低碳排放量之間的權衡問題;Yu,等[7]建立了由綠色產品研發企業與綠色產品銷售企業組成的供應鏈模型,分析了不同的研發合作合同對雙方企業利潤的影響;Hong,等[8]構建了一個由生產商研發并生產綠色產品,零售商營銷產品的供應鏈模型,分析了綠色營銷成本分擔等問題;Yan,等[9]構建了由一個制造商與兩個零售商組成的供應鏈模型,分別求解了當只有一個零售商進行綠色投資、兩個零售商都進行綠色投資、兩個零售商都不進行綠色投資時的供應鏈均衡策略;Xu,等[10]考慮了產品的綠色度對需求的影響,構建了由制造商與零售商組成的供應鏈模型,研究集中決策與分散決策模式對產品綠色投入及產品價格的影響。
還有一些企業利用垃圾分類技術降低排放到環境中的垃圾量。目前,針對垃圾分類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居民垃圾分類方面,如,王偉,等[11]確定了在垃圾分類過程中,居民、收運企業、處理企業承擔的責任比例;徐穎,等[12]在市場化運營模式下,構建了居民、收運企業、政府組成的逆向物流系統,求解了該系統的均衡策略;王丹丹,等[13]建立了政府、居民、垃圾處理企業三方的博弈模型,分析政府的激勵監督對各方決策的影響。此外,還有部分學者從影響垃圾分類的因素[14]等其他方面展開了研究。
企業實施垃圾分類要付出一定的成本,這會影響企業的經營決策,進而影響企業所在供應鏈中其他企業的決策,因此供應鏈成員企業決策時有必要考慮生產商的垃圾分類行為。
特別的,隨著商業競爭環境的不斷改變,企業之間的關系變得越來越復雜,眾多從事供應、制造、分銷的企業相互關聯,構成了復雜的供應鏈網絡系統。構成供應鏈網絡的成員企業在相應的約束條件下受各種各樣的目標驅使選擇其最優的運作方式。因此,眾多學者利用供應鏈網絡模型來研究具有多層結構的供應鏈中成員的選擇、布局以及供應鏈的協調問題。Nagurney,等[15]將交通網絡中的相關理論應用到供應鏈網絡之中,形成了一套研究供應鏈網絡的獨特方法。此類研究主要是借助變分不等式方法在處理多博弈參與者、多層問題中的優勢,研究供應鏈網絡各層成員之間的關系。在此基礎上眾多學者分別從質量[16-17]、風險[18]、碳稅[19]等角度刻畫了供應鏈內企業的最優行為與均衡條件。
本文針對由多個生產商和多個零售商構成的供應鏈網絡系統,在考慮生產商垃圾分類行為的基礎上,利用變分不等式方法構建了考慮垃圾分類行為的供應鏈網絡模型,揭示了生產商的垃圾分類行為、政府環保政策對供應鏈成員企業運營決策的影響關系,為供應鏈企業決策以及政府環保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據。
1 考慮垃圾分類行為的供應鏈網絡模型構建
1.1 模型描述
考慮一個由m個生產商、n個零售商組成的供應鏈網絡模型,i,j分別表示第i個生產商和第j個零售商。生產商生產同質的產品,并將產品以一定的批發價格銷售給零售商,零售商再以一定的零售價格將產品銷售給終端市場的消費者。
在污染者付費原則下,政府要求生產商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對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全部垃圾進行分類,其中不可回收垃圾需要按量繳納環保稅,并對不可回收垃圾中未能分類出的可回收垃圾進行處罰。企業在垃圾分類過程中,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并且努力程度越高,不可回收垃圾中混摻的可回收垃圾的量越少,垃圾分類效果越好。政府通過征收環保稅,影響生產企業的垃圾分類行為,以減少廢物的排放,實現資源的合理利用,并減少生產活動對環境的破壞。零售商通過一定的營銷手段將生產商的垃圾分類行為傳達給消費者,引導消費者選擇環保的產品和服務。例如,自2016年起實施的《關于促進綠色消費的指導意見》中倡導的綠色消費,引導消費者崇尚勤儉節約、減少損失浪費、選擇環保產品,降低資源的消耗和污染排放。因此,考慮垃圾分類行為的供應鏈的運營過程如圖1所示。

圖1 考慮垃圾分類的供應鏈運營過程圖
生產商之間與零售商之間從事非合作競爭且均以自身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本文首先對二者進行逐層分析,描述其在供應鏈網絡中的決策行為,進而利用變分不等式描述各層博弈的均衡條件,并給出相應的經濟解釋。
1.2 生產商均衡條件
用qaij表示生產商i與零售商j之間的產品交易量,表示生產商與零售商之間的產品交易量所構成的列向量,即表示生產商i產品生產總量,表示生產商i的產品生產成本,由于原材料等因素的競爭關系,假定生產商i的生產成本與其他廠商的產量有關,即fi1是qa的函數。分別表示生產商i與零售商j交易產品的批發價格和交易成本(含運輸成本)。
生產商i在產品生產中產生的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量分別為,二者均是關于產品生產量qai的函數。按照環保政策的要求,生產商需付出一定的努力將可回收垃圾分類出來,用wi表示生產商i分類出的可回收垃圾總量,,付出的垃圾分類成本為fi2,并且fi2是關于wi的函數,用表示所有生產商分類出的可回收垃圾量構成的列向量。環保企業以pl的價格回收生產商分類出的可回收垃圾,假設pl與所有生產商分類的可回收垃圾的總量有關,即pl(w)。的環保稅款為Ti=Ti(qai,wi)=,其中u表示政府針對生產商分類后剩余的不可回收垃圾(可能摻有可回收垃圾)的環保稅率,v表示政府針對生產商未能分類的不可回收垃圾的罰款稅率。該函數存在兩個部分,表示對生產商的納稅部分,
政府要求企業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對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全部垃圾進行分類,其中不可回收垃圾按量繳納,并對不可回收垃圾中未能分類出的可回收垃圾進行處罰。假設政府向第i個生產商征收表示對生產商的罰款部分。
綜上所述,生產商i的最優化問題可以表示為:

假設所有的生產商之間從事非合作Nash博弈,并且所有生產商的產品生產成本函數、交易成本函數、垃圾分類成本函數、環保稅函數均為連續可微的凸函數,因此生產商之間相互博弈的均衡條件可以表示為下面的變分不等式,求解滿足:

1.3 零售商的均衡條件
零售商j的最優化問題可以表示為:

假設零售商的展銷成本、營銷成本均為連續可微的凸函數,所有零售商的Nash均衡條件表示為下面的變分不等式,求滿足

1.4 涵蓋垃圾分類的供應鏈模型
根據Nagurney,等[16]的研究,涵蓋垃圾分類的供應鏈的均衡狀態,是指供應鏈中產品的流量、垃圾分類數量、營銷力度等滿足變分不等式(4)和變分不等式(8)的和。得到涵蓋垃圾分類的變分不等式如下,即尋找一組解,滿足:


2 算例與分析
構建一個包含2個生產商、2個零售商的供應鏈模型,并利用Euler算法對算例進行求解。
2.1 算例函數
參照文獻[15]等相關研究,給出相關算例函數表示形式及相關系數:
生產商批發價格函數:p111=400-0.8qa11;p112=400-0.8qa12;p121=400-0.8qa21;p122=400-0.8qa22。
生產商可回收垃圾價格:pl=t-(w1+w2)。
零售商產品銷售價格函數:零售商銷售產品的價格函數如下,β為營銷敏感系數。

2.2 算例設計
本文共設計了7個算例,考慮到在現實情況下生產商之間可能存在的垃圾分類技術和生產技術的差異、政府的環保稅率變化及零售商的營銷敏感度變化(算例2至算例7)。為更好地進行分析,本文給出相關系數完全對稱的算例1作為初始算例與其他算例進行比較,各算例說明及相關系數取值見表1。

表1 算例說明及系數取值
對以上7個算例進行算法求解,并計算垃圾分類效果、利潤和產品產量等內容,各算例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均衡決策與利潤見表2。

表2 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均衡決策與利潤
根據算例結果比較,可以得到:
(1)與算例1相比,算例2中生產商的垃圾分類數量提高,但生產商1的垃圾分類效果下降、生產商2的垃圾分類效果上升。
由于生產商2的垃圾分類技術提高、垃圾分類成本系數降低,使得該生產商提高了垃圾分類數量,垃圾分類效果也由此提高。較高的垃圾分類效果既提高了生產商2的產品需求,又降低了其應繳納的環保稅額度,加之垃圾回收收入的提高,使得生產商2的利潤上升。
受生產商2產品需求的影響,生產商1的產品需求下降,其產品銷售收入下降,又因為回收市場中的可回收垃圾量的增加,使得生產商1的垃圾回收收入下降,使其利潤降低。這種變化使得生產商1不得不降低垃圾分類數量來減少垃圾分類成本,故生產商1的垃圾分類效果降低。零售商在產品定價時,受生產商2垃圾分類效果的影響,產品出售的價格較高,使其利潤增加。
(2)與算例1相比,算例3中兩個生產商的垃圾分類數量和垃圾分類效果均上升,生產商2的垃圾分類效果上升幅度大于生產商1。
由于生產商2可回收垃圾產生系數的降低,使得其可回收垃圾的產量下降。較少的可回收垃圾,既降低了該生產商應繳納的環保稅額度,又提高了該生產商的垃圾分類數量,使得其垃圾分類效果上升。生產商2較高的垃圾分類效果促進了其產品的需求,使得零售商提高了產品價格,零售商的利潤上升。產品需求的上升,使生產商2的產品流量增加,其利潤也上升。受生產商2產品需求的影響,生產商1的產品需求下降、產品流量下降,使生產商1產生的垃圾量減少,這既降低了該生產商應繳納環保稅的額度,又增加了該生產商的垃圾分類數量,提高了垃圾分類效果。
(3)與算例1相比,算例4中兩個生產商的垃圾分類數量與算例1相同,但生產商1的垃圾分類效果提高,生產商2的垃圾分類效果降低。
不可回收垃圾產量的減少只能使生產商應繳納環保稅額度降低,故不可回收垃圾產生量的變化不會影響生產商的垃圾分類決策,故兩個生產商的垃圾分類數量與算例1相同。生產商之間垃圾分類效果的變化,主要是由其產品流量的變化引起的。生產商2的產品流量增加,使得其產生的可回收垃圾量增加,在垃圾分類數量不變的情況下,生產商2的垃圾分類效果下降;生產商1的產品流量下降,使得其產生的可回收垃圾量下降,在垃圾分類數量不變的情況下,生產商1的垃圾分類效果上升。
(4)與算例1對比,在算例5與算例6中,兩個生產商的垃圾分類數量和垃圾分類效果均上升。值得注意的是,算例5中垃圾分類效果提升幅度、產品流量降低幅度都要大于算例6。
算例5與算例6都很好的驗證了環保稅的雙重效應,一方面環保稅率的提高可以提升生產商的垃圾分類數量,從而提升垃圾分類效果;另一方面過高的環保稅率會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本文表現為產品流量的下降。
(5)與算例1相比,算例7中生產商的垃圾分類數量不變,垃圾分類效果上升。
當零售商在考慮產品定價時更偏重其在生產商垃圾分類效果上的營銷效果,或者說當消費者針對零售商的營銷效果更加敏感時,并不會影響生產商對于垃圾分類數量的決策。此時,針對該產品的需求會減少,但由于產品的銷售價格較高,使得生產商與零售商的利潤提高。
3 結語
本文考慮政府環保稅政策,構建了考慮生產商垃圾分類的供應鏈網絡模型,分析了生產商垃圾分類行為對供應鏈成員企業的影響。
由分析結論可知,生產商垃圾分類效果的變化既可能由該生產商垃圾分類數量的變化產生,也可能由該生產商產品生產量的變化產生。這就要求當地政府要明確導致該地區生產商垃圾分類效果提高的具體原因,合理制定相關政策,防止對當地的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此外,政府可以引導企業進行綠色升級,通過使企業實現綠色生產,降低該企業垃圾分類成本與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垃圾量,以提高其垃圾分類效果。
本文將政府的環保稅率設定為外生變量,沒有考慮政府在制定環保稅率時存在的與供應鏈成員企業的博弈關系。在本文的基礎上,將政府的環保稅率設為決策變量,分析政府與供應鏈成員企業的博弈關系可進一步豐富有關考慮垃圾分類的供應鏈研究。此外,可將環保企業視為供應鏈成員企業,以探究在市場化模式下的供應鏈成員企業的垃圾分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