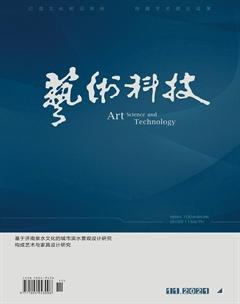基于經典文本《逃避自由》與動漫《千與千尋》論自由哲學觀
摘要:自古希臘至今數千年,“自由”始終為古今中外身處各行各業的人們普遍關注的熱門話題。近代以來,西方資產階級更是將自由、平等與博愛作為自身追求的終極目標。近代歐英歷史的要旨,實則是為爭取更為廣泛的自由而盡可能地謀求擺脫與人類相關的一切政治、經濟及精神上的枷鎖。人類對自由的熱愛與向往,從古今名言中便可略窺一二——“自由一旦扎了根,便如同植物般迅速生長”,自由那般美好,讓人甘之如飴地傾盡所有。不論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還是“不自由,毋寧死”,無一不在訴說著自由的意義與價值在某些程度上已然超出了生命存在之本身。本文基于弗洛姆經典著作《逃避自由》以及宮崎駿經典動漫《千與千尋》對自由哲學觀進行分析。
關鍵詞:自由哲學觀;責任;追求;《逃避自由》;《千與千尋》
中圖分類號:B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11-0-02
古今中外對自由的解釋各異卻又相互關聯。在我國古文中,自由的釋義為“由于自己”,即不受任何外力影響全憑自己做主。在古今名家的經典著作中,不難窺見自由的身影,那句“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更是深入人心,“自由”二字在此能與陶淵明所說的自然之意畫上等號。自由在古希臘與古羅馬時期與解放同義,主體想要真正自己做主,必須使自己從外力的限制中得以解放。追溯詞源發現,古拉丁語中的自由意為掙脫束縛、從束縛中解脫,英文中表自由之意的單詞意為不受束縛與羈絆地生活。自由在西方歷史上常關聯到的獨立、自主及擺脫強制等原初意義,在根本上意味著人類身心依附關系的解除以及主體人格上的獨立。
1 自由的定義
自由是政治哲學中的核心概念,因主體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認識存在差異,學術上對自由概念的見解也是不同的。于理論,自由可視為我們作為社會人的一種權利,從心理學層面出發,自由是主體循著本心、依著自身意愿行事,即人們能夠參照內心真實想法對自己的行為作出選擇。當然,選擇要受到與作出決定的主體本身相關的主客體因素的限制,如出生背景、成長環境、自身能力、行為習慣等。在種種條件的作用下,人類的意識可以自主地進行選擇。選擇若只依照主體內心即算自由,若受到干涉或制約,則與上述自由相悖。正如佛法曰:“你自己求的,你想要的別人不愿干涉”,由此更能明晰自由在此的釋義更貼近于一種自由意識,這是每個人都應擁有的基本權利。在自由意識下,主體必須自愿承擔所有后果。因此,若有任何行為對自由意識進行干涉,不論出于何種目的,都將被打上邪惡的印記,只因其違反了人的本性。從法律層面出發,自由簡而言之就是不違法。孟德斯鳩認為的自由,是在法律容許的范圍內行事。然則實意更為復雜,法律并非只有一種,且可劃分為善法與惡法。善法與社會學的基本要求相契合,在保護大部分人利益的同時,限制所有侵害他人的行為。惡法必定與善法相對,以自身規定作為公民行為的唯一標準,從根本上限制了人們的行為,是消極的。綜上所述,法律的自由在實行善法的地方基本等同于社會學所描述的自由;實行惡法的地方,法律不再等同于社會學的自由概念,其不僅直接限制了主體自由,更淪為間接行惡的工具。從政治層面出發,自由與否取決于人們的選舉權。《道德經》認為執政者要“以百姓心為心”,實指執政者治理國家需要完全依照百姓的意愿。一旦執政者不能履行上述職責,百姓便有權推翻政權并重新選舉,直至擇出真正的“以百姓心為心”的執政者。洛克在《政府論》中提到,“自由意味著不受他人的束縛與強暴”。現代民主制度的本質具體概括如下:尊重他人自由意識、維護他人行善自由、制止侵害他人惡行、保護他人政治自由。因而,自由與民主相互區別又密不可分。從社會層面出發,自由是以不損害他人為前提的自發性行為,對僅關乎自身的事有絕對的自主權,一旦同他人產生聯系,首先以不侵害原則為基本前提。善行是自由的行為,不會侵害他人分毫;相應地,惡行是不自由、對他人造成侵害的行為。若一個社會是健康、正常的,必定能做到賞罰分明,在鼓勵善行的同時懲罰惡行,并正確引導人們的思想,為了更好地保護公民積極行善的自由,限制人們相互侵害的行為發生。
2 自由與責任
自由是人類渴求實現人生價值,提升生活質量,進而提高生命品質的行為取向與方式,這種取向與方式以人類獲取基本生活保證為根本前提。人類無論何時都無法完全避免外在條件(自然)和內在條件的局限性,因而上述取向更多偏向于盲目,甚至是非理性的。自由從整體上看是相對性概念,由于社會各個體自由相互制約,絕對的自由必然是理想化的,它在社會中的存在一定會受到阻礙與限制。制約相互影響,終形成如道德與法律這般的約束性限制。正如蕭伯納所說:“自由意味著職責,那就是為何多數人畏懼它的緣故。”制約與限制是一種責任之所在。責任,是身處社會的個體都避不開的,帶有一定的強制性。責任伴隨人類文明社會呈于眼前,社會的產生必定伴有責任之存在。衡量個體精神素質的一個重要指標即責任感,因此不難理解“責任產生于社會關系中人與他人之間的相互承諾”,社會中每個身份角色背后必定有該身份角色需要為之承擔的責任。
自由與責任的關系在哲學中是對立統一的,責任總相伴于自由。追求自由的同時不能忘記責任的存在,自身被需要作為人類心理的最高追求早早便披露了自由與責任間的關系,其皆以實現人類自我價值為終極目標。沒有責任,自由會被濫用,從而產生無法預估的后果;正因為責任可以說是一種“被需要”,所以承擔責任就意味著一定程度的不自由。當個體被他人所需時,個體便不再以自己為中心,而是以他人為中心,這正與自由相對立,自由的核心是以自己為中心,兩者顯然相悖。然而,自由與責任又相互統一。我們說“完成各自的責任終究是為了人類社會更加和諧穩定,使人類獲得更多的自由”,這意味著責任變相成了自由的前提,脫離責任這一基礎前提的自由并非真正積極意義上的自由,僅能作為被困于限定范圍內的狹隘“自由”。以犯罪為例,世界各國雖然有各式條例法案對罪犯進行審判與制裁,但在本質上并不意味著以法律阻止人們犯罪。即使法律極其完備,人們仍然擁有犯罪自由,只是實施犯罪行為后必須承擔相應的后果。法律的“制止”并非對人類個體的行為活動進行阻攔,更多的是進行心理層面的警示與約束。以漢武帝為例,其早年酷愛金戈鐵馬,窮兵黷武,罔顧民生,致使國庫空虛;幸在晚年幡然醒悟,重新承擔起一國之君之“己任”,大漢基業得保。審視其一生,漢武帝前后行事都依自己心中所想,因其皆為自由,然此自由非彼自由,分別以兩種自由為基礎行事,結果定不相同。個體追求的自由不能建立在傷害他人、破壞社會穩定團結、損害國家利益的基礎上。
3 追求自由與逃避自由
不少人將薩特所說的“人誕生于世,注定要受自由之苦”奉為金科玉律。事實上,作為高等生物的人類或多或少存在逃避自由的傾向。弗洛姆認為,即便資本主義看似擺脫了中世紀的種種約束進而使人們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又使人們陷入孤獨與彷徨之中。弗洛姆考察現代西方人生存環境后有了新發現,那些被常人所說的擺脫了前個人主義社會桎梏的現代人實際上“并沒有獲取能使其個體自我得以實現,即他的智力、感情和感官方面的潛力得以發揮這一意義上的積極自由。自由為人帶來獨立和理性不假,但的確也讓人感到孤獨、充滿憂慮、脆弱無依”[1]。人們看似因掙脫一切精神權威的束縛獲得自由,但隨著這種自由而來的是孤單與無力,人們被空氣里彌漫著的個人無意義與無權力感所壓迫[2]。正如紀德所說,“知道怎樣得到自由還算不上什么,艱巨的是怎樣使用自由”,有時人們看似獲得了自由,但這遠不是方程式的最終結果,僅是運算過程中的一個步驟,結果的推演最終要依托于“使用自由”的方式,與“使用自由”掛鉤又逃不過“逃避自由”的問題。“追求自由”與“逃避自由”永遠是人類揮之不去的兩個夢,與其說它們是辯題雙方,不如說是孿生兄弟,它們相互依附、彼此共生,與水火不容、此消彼長的狀態完全不同。
《逃避自由》的寫作動機和弗洛姆自身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作為猶太人的弗洛姆為了躲避納粹的迫害逃亡美國。在弗洛姆看來,拼命消費正是20世紀大部分西方人生活的特點,因而人們的實際消費與自身的實際需求相互分離,人們早已在消費中被物化,完全迷失在商品世界。相應地,人們變得愈發現實,崇尚及時行樂,精明地計較著個人得失,人際關系失去了人情味與直接性,呈現出工具性和操縱精神的特點,進一步加深了個體的孤獨與無能為力感。人們在那些與人生有著根本關系的重大問題上顯得極其無知,逐漸傾向于放棄自由,屈服于一系列根深蒂固的統治,自愿拋棄自身個性,最終化身寂寂無聞的普通大眾。弗洛姆對逃避自由的途徑進行劃分,他認為逃避自由絕非好的選擇。人們逃避自由的心理原因是自由會使人覺得孤獨無依,進而產生焦慮的情緒,所以人們希望從自由的重負下脫離出來,并試圖找尋可依賴的對象。
逃避自由的前提是自由,人們只有在已獲得自由的前提下,才有資格談逃避。自由的存在伴有孤獨、焦慮、恐懼等消極情緒,甚至當人們意識到自己是不同于他人的一個“我”時,孤獨與焦慮便隨之而來。人們失去束縛后,似乎也變相地失去了方向,因而茫然無措,這看似更加貼合人類獲得自由后的直觀感覺。在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老布什出獄后,面對失而復得的自由時,只感到惶恐,而非興奮與激動,他最終選擇繩懸梁上。老布什最后的選擇,究竟是逃避了自由還是獲得了自由呢?看似逃避自由的選擇在某種意義上又何嘗不是獲得了自由呢?
4 結語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殷切地表達了對人類前途的信心,他始終相信人類可以克服自由所帶來的所有負面情緒。他認為人類可以選擇積極的自由,雖自由卻不孤獨,雖獨立卻又不與世界相脫離地活著。積極的自由建立在人類的個體差異性基礎之上,它的實現不會脫離我們生活的社會,它需要人類重新認識自己的個性,并通過與他人的合作最終實現自我主體性價值。
筆者認為弗洛姆無疑是理想的。人們在初探到自由的本質后是興奮的,對于未來是心向往之的,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選擇不會因一時興起而改變分毫,漣漪褪去后的湖面終究歸于沉寂,逃避自由似乎是簡單模式,而世間億萬人中最終能夠破除萬千阻礙選擇困難模式的不過寥寥。再看《千與千尋》,不禁感嘆宮崎駿的通透。動漫中白龍告誡千尋不要忘記自己的名字,否則只能永遠留在湯屋。這里的名字暗指自我,如果無法堅持自我,保持初心,在湯屋迷失自己,就會成為另一個小玲——丟掉自我后成為湯屋的奴隸。小玲正是那戴著相同面具做著重復工作、枯燥生活的“機器人”。無臉男的設定也極具巧思,他本身無關好壞,可在湯屋中逐漸迷失,實質暗喻了生活中的大多數庸人。他們沒有堅定的信念,在偏執地為達成某個目的的過程中不慎落入深淵,五花八門的誘惑與欲望就是被無臉男不斷吞噬的物品——從開始的食物到后來的活物,事態發展愈發不受控制。其在吞噬欲望與誘惑的同時,也被欲望與誘惑所吞噬,被世人指責與憎惡,可世人又如何能保證明日的自己不會淪為自己今日憎惡的模樣呢?萬幸,無臉男在吃下河神丸子后,吐出了被自己吞噬的一切,恢復了原樣。從這里我們可以隱約領悟到宮崎駿埋下的有關希望的伏筆。人世間唯自由與信仰不可或缺,我們應對希望抱有憧憬,做信仰堅定之人。“有些鳥注定關不住,正因為羽翼上沾滿了自由的光輝”,要努力做關不住的鳥兒,心之所向,身之所往。
參考文獻:
[1] [美]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11.
[2] 俞伯靈.弗洛姆|人類揮之不去的兩個夢——追求自由與逃避自由[J].浙江社會科學,2003(4):5.
作者簡介:黃鈺瀅(1996—),女,貴州貴陽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