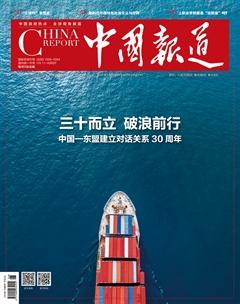鄭永年: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推動實現中國的現代性?

鄭永年
上世紀90年代,中國伴隨著鄧小平南方談話,開啟了一段新的歷史,實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個可持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可持續的社會穩定以及可持續的制度支撐與領導。從根本來說,“三個可持續”是正確處理了三個主體之間的關系,即經濟、社會和政治主體。企業是經濟的主體,人民是社會的主體,中國共產黨是政治的主體。
那么,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推動實現中國的現代性?
第一,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使命型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必須通過實現使命來執政,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中國共產黨現在那么強調“不忘初心”。
有人說,世界其他國家的政黨是隨著“民意走”。表面上是這樣說,但是實際上是不是,大家可以討論。更關鍵的是,一個隨著民意走的政黨是不是一個好政黨?一個政黨應該是代表大多數人的民意,不能被少數人的民意牽著走。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曾經說過(大意),如果大家覺得這樣做是符合這個國家的長遠利益,哪怕是一些少數的民意反對,執政黨也要去做,這個就是好政黨。如果不顧民意,那就是做人民的“大老爺”;如果光順著民意,就很容易做人民的“尾巴”,兩邊都不行。中國共產黨在這方面,把握得非常好,它的使命性就可以得到保持。當然,這個使命一定是老百姓認同的使命,而不是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個團隊認同的使命。
現在中國共產黨有很多機制來保持使命性,例如五年規劃、十年規劃,現代化新征程“三步走”,即2020年全面小康、2035年社會主義基本現代化、2050年民主富強繁榮,等等,中國有很長的規劃。今年是共產黨100周年,馬上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大家去看世界上的政黨,哪一個政黨能夠想得那么遠?在這一點上,中國共產黨是獨一無二的。

迎接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之際,位于遼寧沈陽的中共滿洲省委舊址紀念館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0年之際修繕完成。
第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開放型的政黨。
開放型的政黨就是包容型的政黨。我把西方的制度稱之為外部多元主義,你不喜歡這個政黨也可以加入其他的政黨,可以創造其他的政黨,政黨的數量可能會無限地增多。這種外部多元主義,雖然是開放的,但是會出現很多問題,很容易出現政治主體缺失。我把中國的稱之為內部多元主義,所有不同的社會經濟利益都可以納入共產黨這樣一個開放性的體系,內部通過協商來解決問題,這也正是中國解決經濟社會利益分化的途徑。
更重要的是,中國內部開放性的一個特征是“賢能政治”,即所有的社會精英都可以進入這個系統,在這個系統里面來解決問題。我認為這個跟中國文明的開放性有關系。中國的世俗文明就是包容性的,而西方的宗教文明就是排他性的。中國的黨權本身是包容性的,是一個集體,是可以民主化的,也就是我們說的“黨內民主”,開放性、包容性是黨權的主要特征。我個人認為,從學理上說“開放的一黨制”效率上要遠遠好于多黨制。
中共中央有一個提法叫“政治家集團”,這個概念我覺得很重要。中國共產黨就是現在的領導階層,相當于傳統社會儒家的精英集團。當然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具有現代性的ruling group,就是政治家集團,這個政治家集團是開放的。歷史地看,這個政治家集團是否有效取決于是否能夠容納來自“五湖四海”的人才。

2019年10月1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
第三,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高度重視參與的政黨。
我們還是要定義一下,因為現在一說政治的參與基本上就是選舉參與;實際上,上世紀60年代美國政治左派認為,不是選總統的參與最重要,而是對那些能夠影響自己生活政策的參與,即政策參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當時我們講經濟民主、講工廠民主,要先搞清楚什么樣的方式是政治參與,選舉的參與并不是最有效的方式。上世紀90年代,中國臺灣地區和新加坡人均GDP都差不多,但是現在呢?現在新加坡人均GDP達到6萬美元的水平,臺灣地區是2.6萬美元的水平。
在中國,人們對于政策的參與是非常重要的。政策上的參與和政治上的參與有很大的區別,我覺得政策參與甚至比政治參與更重要。對普通老百姓來說,判斷哪一個政治人物是好是壞很難,有很多偶然的因素都會受影響,但是這些跟政策參與沒有關系。中國的政策參與,可以說是日常的參與。中國最近幾項大的決策比西方的更復雜,比如去年通過的《民法典》耗時多少年?以前的《物權法》又是多少年呢?
前不久我到浙江考察發現,社交媒體與大數據出現以后,民眾進行政策參與的方式又有一個新的形式,這是非常有趣的。我在當地還看到有一個叫作“網格式的管理”。以前在新加坡,我對網格式管理不是很了解,西方人覺得網格式就是社會被控制,這是不對的。但是我覺得“網格化管理”這個說法也不合適,將來一定要改的。說白了,這里面其實就是一個平臺,是一個政府跟老百姓互動的平臺,是老百姓自治的平臺,可以提供精準服務。好幾年以前我看到英國《經濟學人》雜志里有一篇文章,它說正是因為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所以共產黨對民意的重視程度遠遠多于其他民主國家的執政黨。這其實是一個命題,里面的邏輯想想還是很清楚的。
第四,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學習型的政黨。
這個非常重要,因為只有學習才可以進步。我個人也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是最大的學習型政黨。大家一定要想清楚,相互學習不是說我變成你、你變成我,我們互相學習就是要變成更好的自己,這種學習才叫好學習。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盡管從鄧小平那時就開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是一直也在向美國和歐洲學習,早期上世紀80年代向東歐國家學習、向日本學習,也向新加坡這么小的國家學習。
中國共產黨一直在學,但是從來沒有照抄照搬任何一個國家的東西,總是在學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把好的經驗和best practice(最佳實踐)學過來,同時還要讓它符合中國的實際。
第五,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自我革命的政黨。
我剛才強調了中國共產黨的開放性,以開放性建設開放性的政黨。但是其內部怎么做得到呢?這幾年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四個自信”,我覺得四個自信里面最后一個“文化自信”最重要;前幾年又提出“四個全面”,我覺得最后一個“全面從嚴治黨”最重要。所以,我們現在如果真的要理解中國的現狀和未來的話,你就要把這兩個最后的“黨”和“文化”結合起來。
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已經形成了中國大的文明、大的傳統,做了一次徹底的轉型。這個轉型在結構上是一樣的,內容上是不一樣的。什么轉型呢?我把它稱之為黨內的“三權分工合作”體制。我們大家現在讀西方的書,一說西方的制度就是三權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但是大家別忘了,中國的制度也有“三權”,什么權呢?決策權、執行權和監察權。這個體制其實在漢朝就已經形成了。跟西方比較,西方的三權就是分塊的,中國的三權是政策上的時間段區分的:首先決策,決策好了之后執行,執行了以后監察。這也就是馬克斯·韋伯說的官僚的合理化(理性化)的過程。“三權分工合作”體制到晚清以后就沒有了。孫中山先生想在西方“三權”的基礎上,從中國傳統中找出“兩權”來——考試權和監察權——最終形成了“五權憲法”。他從學理上想把兩個制度結合,但今天的實踐表明,要不就是中國的“三權”,要不就是西方的“三權”。中國共產黨一直在探索。
中共十八大以后,開始在浙江、山西、北京試點監察權,中共十九大后這“三權”分類正式到位了,所以現在又成為一個內部“三權分工合作”的機制,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回歸傳統,而是一個創造性的轉型。不要低估中國內部“三權分工合作”制度,現在我們通過創造性的轉型到位了,要趕緊好好地去研究。這樣一個制度就是在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自我改革的過程中實現的。
因此,思考中國共產黨的現代性與中國國家現代性關系的問題,我們需要從政治主體以及如何處理這三個主體(黨、人民、企業)之間的關系入手。思考這一關系的問題,關鍵是要從三個傳統出發來思考:第一個是中國幾千年的“大傳統”,第二個是從近代以來的“中傳統”,第三個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小傳統”。從這三個傳統出發,反思如何來處理三個主體之間的關系,不僅可以理解黨史,還可以理解整個世界問題。
(本文由鄭永年教授于2021年4月7日在上海交通大學作的題為“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現代性”專題報告整理,首發于“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微信公眾號,在原文基礎上有編輯、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