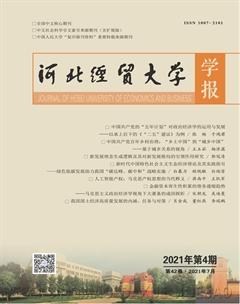中國共產黨百年鄉村治理:“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
王玉茹 楊濟菡

摘 要:
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對鄉村治理的探索已走過近百年歷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黨的鄉村治理政策方針始終與城鄉關系之境況或政策緊密相連。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農村包圍城市;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根據各階段經濟發展的重點,先后經歷了城鄉二元、城鄉失衡、城鄉統籌、城鄉融合四個時期。各個時期黨在鄉村治理目標、治理主體、治理方式上都進行了有效的探索和創新。通過對中國共產黨的鄉村治理思想和實踐進行系統梳理,從城鄉關系的角度串聯鄉村治理的變革,以更好地理解百年鄉村治理的演變邏輯。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城鄉關系
中圖分類號:F129,D23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2101(2021)04-0011-08
收稿日期:2021-04-08
作者簡介:王玉茹(1954-),女,天津人,南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楊濟菡(1991-)女,四川眉山人,南開大學博士研究生。
鄉村治理即基層治理。涉及如何對鄉村基層秩序的維護,從而實現鄉村社會有序發展[1],以維護基層社會穩定與社會發展。我國是傳統農業大國,鄉村治理歷來都極其重要。傳統中國“政權不下縣”,依靠鄉紳地主和宗族制度等非正式制度進行鄉村治理,城鄉之間沒有呈現出界限分明的鴻溝,城鄉關系遵循著自身發展規律[2],鄉村依附于城市,呈現出一種低水平的一體化。近代以降,工業化、城市化等現代化進程導致城鄉差異日漸凸顯,農村知識精英大量流失,傳統鄉紳治理模式土崩瓦解。晚清后期,國家權力開始向農村社會下沉,試圖對傳統鄉村治理模式進行替代;民國時期,地方鄉紳和知識分子也不斷探索著鄉村自救之道[3],但都成果寥寥。
具體國情和現代化建設的規律影響著城鄉關系格局的塑造,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始進行鄉村工作和制定鄉村治理基本制度和政策安排的重要出發點。本文從城鄉關系的視角出發,分為 “以農村為中心”的革命時期、城鄉二元的探索時期、城鄉失衡的調整時期、城鄉一體化的建設時期以及城鄉融合的發展時期五個階段進行考察。每個時期的城鄉關系是指黨面臨的城鄉實際問題或者國家特定發展階段所塑造的城鄉關系格局。這些問題和格局進一步影響了黨對鄉村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4]通過梳理這些制度變遷過程和具體內容,本文對中國共產黨百年鄉村治理的演變進行系統性研究,以更好地理解新時代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理解黨組織在農村基層的領導作用,理解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
一、“農村中心”革命時期的政黨下鄉
近代以降,西方入侵,中國經濟被迫卷入世界體系,逐漸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附庸。無數仁人志士進行抗爭與探索以尋求救亡圖存之路。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伊始,在之后28年的革命時期,一直致力于追求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由于理論和經驗不足,在重大決策上更多地參考共產國際的意見,行動上主要照搬俄國革命模式,在大城市領導工人運動。[5]但由于力量懸殊,先后遭到軍閥鎮壓。即便此后國共合作實現,工人運動得以恢復和發展,但國民黨反對派背信棄義,“大革命”終以失敗告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反思城市革命的經驗以及革命中面臨的歷史和現實問題后,將革命重心從城市轉向了農村。此后中國共產黨扎根農村,開始進行鄉村基層建設,探索鄉村治理的經驗。
以農村為中心,通過農村包圍城市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年代經實踐摸索出來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是將馬克思主義經典學說與中國革命實際與實踐相結合的產物。近代城鄉關系格局為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客觀基礎。西方資本入侵,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結合的封建經濟開始瓦解,但仍舊占據統治地位。[6]這種只存在于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7]的特色城鄉關系形成,使傳統的“低水平”城鄉一體格局被打破。與沿海沿江少數城市的繁榮并存的是廣大內陸農村地區的衰敗和落后,城市難以對農村地區形成控制,也難以為農村提供發展動力。農村則相對獨立地存在,貧農依舊占據多數(70%左右),他們識字率低,也無組織性,加上地主制度和封建宗族勢力盤根錯節,鄉村傳統精英邊緣異化,生活苦不堪言。這為根據地建設,紅色政權的存在提供了革命的土壤。
為了實現對農村地區的整治,中國共產黨將黨的權力徹底下沉到農村地區,打破了傳統鄉村治理的格局。首先,建立黨在農村的基層民主政權,壯大黨在鄉村的領導力量,建立了以黨組織為核心的新的組織形態。1926年《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決議案》中提及了有關鄉村自治問題的提案。1927年《對湖南工農運動態度問題》明確指出,需要堅持中共五大所制定的綱領,解決鄉村的政權問題,在黨的領導下著手建立鄉村自治政權[8],以反土豪劣紳,改變鄉村無政府之狀態。[9]黨開始通過領導廣大人民群眾管理政權,通過群眾直接選舉執行日常活動,建立代表會議等組織權利機關決定鄉村一切政治問題。[10]1933年,隨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地方蘇維埃暫行組織法(草案)》的頒布,以法律形式確定了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建設,從制度上保障廣大農民群眾的政治權利。在黨的領導下農村建立了黨支部、農協、農會等各類農民組織,深入鄉村治理結構。[11]其次,調整完善土地改革政策,改變并改善農村生產關系,最大程度地團結農民。根據地時期,黨領導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進行“平民式”的斗爭。[12]最大限度地團結農村的革命力量,并以制度形式保障了土地革命的成果,如《興國縣土地法》《鄂豫邊革命委員會土地政綱實施細則》等;此后為應對抗戰的需要,實行了“減租減息”的土改政策以鼓勵地主階級參加抗日戰爭,頒布《陜甘寧邊區政府頒發土地所有權證條例》,推動土地確權登記發證工作;抗戰勝利以后,實行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政策,最大限度地調動農村社會的積極性。[13]最后,鄉村社會建設方面,通過宣傳改良廢除鄉村迷信和宗法社會的舊習,動員農民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及加強對農村的思想政治教育。通過開辦農民學校、發展鄉村文化教育改變農民觀念,推動農民參與鄉村建設和鄉村治理。此外,還興修水利工程,解決難民問題,優待貧民等。[14]
二、“城鄉二元”探索時期的一元統合
革命時期的鄉村治理經驗為新中國成立后的鄉村治理奠定了基礎。國家戰略由革命并最終奪取勝利轉向了恢復、發展生產和進行工業化建設,戰略的變化也影響著黨對城鄉關系的認識和調整。在經濟恢復發展時期,黨在全國進一步開展土地革命運動,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隨著土改的完成,工業化建設成為了國家發展的重中之重。作為后發國家,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邏輯意味著農業和農村需要為工業化的發展提供資本積累。黨對農村和城鄉關系進行徹底地改革,短時間內建立了生產合作社,確立戶籍制度等,城鄉二元發展形成。黨以政、社、經合一的人民公社組織對鄉村進行治理。
(一)1949—1953:土地改革與政權下沉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接收的是一個落后的傳統的農業大國。①恢復經濟、穩定物價是重要任務之一,城鄉交流是重要環節。一方面可以將農產品收上來,另一方面可以使工業品銷下去,這樣同時利于農民、城市經濟和國家。對農村而言,眾多新解放區依舊是封建土地制度,土地問題便成為了這個時期鄉村治理的重點,目的是為了讓農民獲得生產資料,解放農村生產力,發揚生產積極性。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頒布以后,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開展了土地改革,將地主土地沒收,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則,分配給少地甚至無地的貧農。[15]為了積極發動農村參加土改,中國共產黨選擇解放區革命時期參與的人員組成工作隊,自上而下在鄉村進行“滲透”。[16]生產資料的獲得使廣大地區的農民群眾獲得了經濟上的解放,也讓農民成為了鄉村治理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為了加強農村地區的基層政權建設,讓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完全下沉到全國的農村地區,黨健全了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建立黨組織,建立了以推銷土特產為中心的合作社以及組織勞動互助組,等等[17],使黨和國家意志能更好地深入農村。
(二)1953—1978:城鄉分離與政社合一
經濟發展戰略影響著城鄉關系的形成,這決定著黨在農村治理體系的形成和變化。為實現使中國由落后的農業國逐步變為強大的工業國的目標[18],黨和國家確立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戰略,這需要有不斷增加的大量資金,但資金又難以通過自身積累滿足,通過農業獲取生產剩余是重要途徑之一。②這意味著農業農村的發展需要與工業化的發展相適應,對工業進行最大程度的支援。
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廣大農民群眾生產的積極性被極大地激發,農業經濟迅速恢復與發展,隨著購買力的上升,城鄉交流日益活躍。與此同時出現了兩類問題,首先是農村中的分散經營難以使國家有效地獲得工業生產原料,汲取農業剩余;其次是城鄉經濟發展差距的擴大使得農村勞動力開始流向城市,這不僅加大了城市生產生活品的供給和就業壓力,而且直接導致了農村勞動力的減少,影響農業生產。可見,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國家戰略下,城鄉之間并不能自發形成良性交流,而應該將城市放在較為重要的地位,以農補工。農村為城市工業發展提供生活資料、生產原料及外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作為重工業的商品市場(如化肥、農業機械等)。因此城鄉之間形成了二元發展模式,戶籍制度控制農村人口外流,統購統銷制度和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保證農業剩余的汲取。黨對農村的治理需要進行調整以對“以農補工”的城鄉二元體系形成支持。
在此基礎上,黨對鄉村治理進行了進一步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的治理體系。首先,通過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推行集體化經營,以合作化的組織模式解決農村生產中經濟分化問題,從而實現對鄉村社會的整治。1953年《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中明確規定,依據不同地區經濟發展和生產要求等復雜情況,農業生產合作可以由簡單的初級勞動互助、常年的互助組以及農業生產合作社三種形式逐步向更高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社會主義集體農莊)過渡。[19]在向高級合作社發展過程中,黨對農村的治理產生了變化。在黨的領導下,農民開始成為干部參與鄉村治理,相對現代化的鄉村治理逐步形成,合作社開始衍生為國家基層政權的一部分,成為黨對鄉村治理的載體。[20]此外,黨還通過對互助組和生產合作社進行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農民集體生產的積極性。到合作化運動后期,運動帶有一定強制性,治理也取得了較好的效果。③其次,隨著鄉村治理合作化運動的順利進行,以及工業化進程中資本積累的需要,黨開始對鄉村完全實行集體管控,以最大限度地限制城鄉人口流動,最小成本地獲取農業生產剩余。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頒布,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正式建立。同年,《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從規模、所有者形式、組織結構等方面確定了人民公社制度。黨在農村全面建立了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三級“政社合一”的鄉村治理體制,這些組織成為了鄉村治理的權力主體。在這種治理模式下,鄉村社會在政權建設與農業生產上充分整合,國家意志在農村地區全面滲透。不過,黨在農村的公社化治理在城鄉間形成了巨大的交流壁壘,盡管利于農業剩余的吸收,資金大量配置到城市,但是并不利于農村經濟發展,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低下,農村地區生活貧困。④但需要肯定的是,工業化建設、戶籍制度等政策所形塑的城鄉關系格局是鄉村治理公社化的重要推動力,這與當時國家發展戰略密不可分。隨著現實條件的變化,黨需要尋求更為合理的鄉村治理機制。
三、“城鄉失衡”調整時期的鄉政村治
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拉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全黨工作的重心轉向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隨著農村和城市經濟體系改革相繼進行,城鄉之間開始打破了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藩籬。在市場邏輯下,生產要素進行著有限流動。但戶籍制度的控制等計劃邏輯使得城鄉之間形成的是鄉村向城市的單向資源流動。20世紀80年代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后城市經濟發展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產生了大量需求,城鄉之間開始了以勞動力為代表的生產要素的大規模流動。這種在計劃和市場雙重邏輯下的“以鄉促城”,是一定程度上“顧城市發展之此,失鄉村發展之彼”[21]。這促使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治理體系相應地產生了調整,“鄉政村治”的正式制度逐漸建立,鄉村治理中黨、政、社、經相對開始分離,鄉村治理走向了行政化與自治相結合的發展路徑。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農村生產生活從集體化回歸單個家庭,“政社合一”治理模式的經濟基礎得以解體。農民逐漸獲得生產、生活資料的支配自由,原有鄉村組織也逐漸松弛,重構鄉村治理機制成為了現實需要。對此,黨開始探索從集體性的、國家性的到自治性的、建構性的鄉村治理模式。[22]1984年人民公社體制基本上在全國廢除,“鄉政村治”結構模式取而代之,鄉鎮是國家基層政權的一級,鄉鎮之下則實行村民自治。1988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進一步將村民自治具體化、法律化、制度化,村黨支部為核心的村委會作為村民自治的組織形式在全國確立起來,在黨的鄉村治理實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鄉政村治”,國家對鄉村的直接控制大大減少,極大便利了農村勞動力、資金和土地資源支持城市化建設。這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后市場邏輯下的要素流動。由此可見,城鄉之間的非均衡既是“鄉政村治”治理模式形成的“因”,又是城鄉進一步失衡的“果”。
鄉鎮政權成為鄉村治理的主體,與村民自治相輔相成。不過“鄉土中國”的屬性使得鄉鎮政權職能的行使不得不高度依賴鄉村自治組織,兩者之間是合作治理關系。但作為上級政府的代理人,鄉鎮與農民在鄉村事務中很容易形成緊張的關系,干部權威下降,村民的自治權利也存在著被行政權力侵蝕的可能,鄉村治理的正式制度安排出現困境。[23]村民自治名實難副,鄉鎮管理眾多掣肘。城鄉關系中,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外流又使得鄉村社會組織呈現“空心化”現象,鄉政機構抑或村治組織都面臨著精英缺乏問題,鄉村治理中的非正式制度開始回歸,成為行政權力的補充。鄉村中自發的、歷史的、內在的力量開始凸顯。
四、“城鄉統籌”建設時期的鄉村共治
進入新世紀,經濟不斷發展。2002年國內生產總值已接近1.5萬億美元,農業所占比重下降到15%左右⑤,農業提供資本積累的歷史任務基本完成。與經濟發展同時并存的是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失衡[24],這進一步制約了現代化進程,如何解決城鄉差別成為國家進行鄉村治理的突出問題。十六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統籌城鄉發展的基本方略,我國城鄉關系出現了重要轉折。十六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建立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資源配置機制。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對鄉村治理的探索以通過政府加大對農村農業的投入、改善城鄉關系、促進城鄉資源雙向流動為主線,提出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及精準扶貧戰略,探索鄉村治理模式。
(一)2003—2012:以城帶鄉與新農村建設
改革開放后“鄉政村治”的實施,尤其是村民自治只是在理論上解決了村莊內部秩序問題。村民自治機構并非鄉鎮政權的行政下級或派出機構,但鄉鎮政權在財稅等方面面臨的困難卻習慣于通過對村委會進行命令指揮式的傳統行政管理,鄉與村之間的緊張關系不僅制約著鄉鎮行政職能的發揮,也很大限度地壓縮了村民自治權的空間。鄉村治理面臨諸多挑戰,這將導致城鄉發展失衡加劇、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農業收益低下等問題,農業發展難以適應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的需要。2003年,黨的十六大將統籌城鄉發展確定為中央戰略方向,我國城鄉關系開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黨和政府開始主導構建城鄉格局,通過加大對農村和農業的投入改善城鄉關系。公共財政投入逐漸向鄉村傾斜,城鄉關系走向了城市反哺農村的道路,這對鄉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確立了“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發展要求,鄉村基層治理發生了重要轉折。[25]農業稅全面取消,財政投入向農村傾斜,鄉鎮政權在鄉村治理中的角色被弱化。鄉村基層結束了稅費征收、政府職能開始了向服務型轉變的重要階段。黨和政府對農村實現了從“汲取”到“給予”的轉變。自2005年始,國家對鄉鎮機構進行改革,旨在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基層行政體制。[26] 這既緩解了農民與基層政權機構的競爭關系,又對鄉村自治開展進一步探索。為改變以往存在的行政式治理方式,中國共產黨強調通過社會組織或者利益團體協商治理。2006年《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提出,通過加強農村地區的民主政治建設完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鄉村治理機制”。在建立村黨組織領導的村民自治組織的基礎上完善農村的民主議事制度,并首次明確提出培育新型社會化服務組織。中國共產黨通過更新治理理念,繼續在農村探索實踐新的治理機制,完善“鄉政村治”模式。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必須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 ⑥,繼續通過加大對農村的直接投入改善城鄉關系,建設新農村。新農村建設需要鄉鎮兩級的協調。隨著之前鄉鎮機構的變革和稅費改革,農民負擔有所降低,但鄉鎮在財、事、人方面的權力向縣級部門集中,使得黨和國家這期間對鄉村的治理直接越過了鄉鎮政權,這又直接帶來鄉村治理的懸空。[23]財權、事權的弱化,鄉鎮在提供鄉村公共服務上存在缺位,也缺乏動力,從財政上支持的農村公共項目建設進行困難,國家對鄉村的控制減弱。鄉村治理繼續在如何收縮鄉鎮權力和完善村民自治兩方面規范和完善,[JP+1]強調在黨組織領導下,培育和發展農村社會組織,擴大村民的自治參與,以實現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的良性互動。⑦鄉村治理模式轉向多元化治理、政府間接治理。
(二)2012—2017:城鄉一體化與美麗鄉村
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城鎮化進程加快。城鄉流動逐漸加大,農民愿意走出農村參與到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大批農民進城導致農村“空心化”現象加劇。[27]這給鄉村治理帶來了難題,如治理主體缺失、留下的村民政治參與不足等。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通過城鄉一體化解決“三農”問題。在城鄉發展關系上,在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等之外,進一步強調了城鄉一體。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是城鄉一體化之具體方略,城鄉一體化過程中給鄉村治理帶來了新的發展,而鄉村治理的創新也是實現城鄉一體化的內在要求。
黨的十八大明確指出鄉村治理目標是“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并第一次提出了“美麗中國”的概念,美麗鄉村則是美麗中國的重要部分。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首次提出了“美麗鄉村”的目標,旨在加強農村生態建設、環境保護等的同時加快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這是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進一步發展的重要舉措。[28]需要建立符合國情,充滿活力的鄉村治理機制,“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 ⑧。2015年6月《美麗鄉村建設指南》正式實施,鄉村治理強調政府引導和村民自主力量共同推動的政社互動。通過政策、社會組織動員以及資源人才輸入等激發村民參與鄉村事務管理的自主性。[29] 為探索鄉村自治活力,地方鄉村治理在自治單元的界定和選擇上進行創新,比如廣東清遠將原行政村變為服務站,村委會下移到各自然村或小組;湖北、四川等村落自治則是在村委會之下設更基層一級自治組織。[30]
2014年隨著戶籍制度的改革,統一了城鄉戶口登記制度,農業戶口與非農戶口的區分被逐步取消。⑨城鄉一體的基本公共體系(養老保險、教育經費等)也逐漸建立,扶貧開發開始作為實現全面小康的重點任務。這些都進一步推進了鄉村治理能力的改善。在美麗鄉村建設過程中,農村新社區成為新的重要載體。與基于血緣、宗族的傳統村落不同,社區是城市化與城鄉一體化發展過程中重新聚合的生活單元。這些農村社區由行政村落、自然村整合規劃而成,或是依靠產業發展集聚農民集中居住的公共空間,具有較為齊全的公共基礎設施。農村社區是農村環境與農民生活方式變革的重要途徑,也是新型的鄉村治理單元,因此需要形成新的治理模式。這類社區由政府、農民以及各類社會組織共同構成,本質上兼有政府治理和村民自治雙重屬性,但需要以團體自治為基礎[31],形成黨政主導,社會組織多元治理的合作與互動。由于農村社區構成的客觀基礎不同,黨和國家在這個時期利用了新蘇南模式、諸城模式以及中山模式等圍繞著多元組織參與和引進市場主體的方式進行探索。如新蘇南模式主要是借鑒城市社區管理模式,依靠鄉村精英發揮主導作用[32];諸城模式主要是依靠地域進行農村規劃整合,集中治理社區黨總支,建立服務中心等一系列完善的組織架構。組織架構以農民為主體,整合多方(政府、社會志愿者、企業等)的力量;中山模式則探索出 “2+8+N”社區建設模式等。[33]
五、“城鄉融合”發展時期的鄉村振興
隨著以城帶鄉、城鄉統籌以及城鄉一體化發展進程,黨和國家從“鄉政村治”到“鄉村共治”,進行了有關村民自治、村鎮共治的深入探索和實踐,農村農業的發展也取得了一些成效。鄉村治理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這也是新時期鄉村進一步治理的基礎。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出需要加快補齊農業農村發展短板,加快農業現代化。農村現代化發展需要擺脫就鄉村論鄉村的局部視角,而是將鄉村和城市結合起來,走融合發展、共享成果、互利共贏的道路。城鄉融合發展應運而生,2017年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這是面對城鄉發展實際構建新型城鄉關系的思想指導,在此基礎上部署了鄉村振興戰略。
城鄉融合發展下的鄉村振興需要鄉村治理體系的有效支撐。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法治本質上劃定了政府的權限以確保自治的正確方向,德治是通過發掘鄉村內部的情感線索,用以維護自治秩序。[34]三者相互協調和補充。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就鄉村振興做出了具體指導安排,指出治理是鄉村振興的基礎,強調通過城鄉融合實現鄉村振興。《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進一步對鄉村治理體系提出了要求,如加強農村的基層黨組織建設,強化黨組織的領導地位;堅持自治的方向,健全黨組織領導的村民自治機制建設;堅持法治理念,建設法治鄉村以及提高德治水平等,為鄉村由管理民主向有效治理的升級找到了方向。[35]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在進行鄉村治理探索時,鄉鎮與村組織參與治理一直存在行政化邏輯。城鄉融合的城鄉關系對鄉村治理的支配性邏輯有所變化,城鄉融合不僅要求城鄉人員、資金、資源等要素的雙向流動和融通,打破鄉村的封閉,更需要推動“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社會事業向農村覆蓋” ⑩,這對鄉鎮和村級組織的公共服務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共服務應當成為鄉村治理的主要思路。公共服務邏輯與行政化邏輯截然相反,后者是向上負責,而前者卻是向下服務,向下服務意味著鄉村治理應當更加深入地探索內生性的村級自治組織。在城鄉融合的背景下,鄉村治理中還更多地出現了市場化、社會化的力量。只有立足農村農業發展實際,才能對新時代的鄉村治理進行更好地探索。我國農村地區差異較大,發展狀況不一,這決定了不同城鄉發展程度的鄉村治理體系各異,內容多元、形式多樣、結構多層,但都強調“行政、自治、民主、服務”的整合[22],強調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強調基層黨組織在鄉村振興中貫徹黨的思想方略、領導基層治理以及團結動員群眾的政治和組織保證。
六、百年鄉村治理的演變邏輯
從以農為本、以土為生的“鄉土中國”走向城鄉互動、城鄉融合的“城鄉中國”[36]的本質是從傳統農業大國向現代化工業大國之轉變過程。城鄉關系中的“三農”問題是現代化建設中面臨的核心問題之一。隨著國家戰略側重點的變化,城鄉關系發生了相應的變化與調整。[37]這些變化與調整影響著農業農村發展的方向和道路,進而影響黨對鄉村治理的探索和實踐。百年以來,隨著革命目標的變化、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以及深化改革,我國城鄉關系經歷了城鄉分離、城鄉二元、城鄉失衡、城鄉統籌、城鄉融合的發展演進,中國共產黨從基本國情出發進行了有效的鄉村治理。黨通過自上而下的深度嵌入和有效整合,成為鄉村現代化建設的支柱力量,并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治理特點[38]。鄉村治理體系中主要包括了治理目標、治理主體和治理方式,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城鄉關系下形成了不同的治理邏輯,構成了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變遷的主要內容。
總體來看,鄉村治理的目標是為了實現農業農村的現代化發展,黨始終是重要的治理主體,黨中央決定鄉村治理的方向,是具體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者;政府為具體執行者,而村民群眾始終是鄉村治理的依靠力量,鄉村社會組織也越來越成為不可或缺的參與者和重要部分。鄉村治理方式是一個制度、政策不斷創新的過程。通過將治理方式制度化、法律化,并不斷結合自治和德治體現。黨的鄉村治理囊括了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等方面。具體而言,在不同發展階段,結合黨和國家的戰略布局和城鄉關系發展重點,呈現了不同的特點和表現方式(見附表)。
中國共產黨百年鄉村治理的歷史與邏輯表明,鄉村治理需要遵循客觀城鄉經濟發展規律,也需要不斷進行改革和創新,堅持在黨的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的鄉村治理道路。進入新時代,在城鄉融合的背景下,鄉村會涌入更多的人才、資源、資金和項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不斷壯大的多元的社會組織參與治理,因此,需要“打造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善治鄉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格局。”[39]“十三五”期間,我國農業現代化取得了重大進展,脫貧攻堅取得勝利。進入“十四五”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時期,鄉村振興正在全面推進。如何做好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有效銜接,需要進一步對鄉村治理進行創新。百年鄉村治理的歷史回顧表明,黨組織始終是領導作用,需要積極動員鄉村多元主體,保證農民廣泛參與以形成開放包容的多元共治格局為方向進行不斷積極探索。
注釋:
①1949年,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89.39%,農業占國民收入的68.4%。國家統計局編:《我國的國民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統計出版社1958年版,第5頁。
②1950—1952年短短三年,農業對國家財政收入從25.54億元人民幣增加至37.06億元人民幣,農業在工農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也達到了57%。董輔礽:《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上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頁。
③1957年糧食產量比1952年增長約19%;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從1952年的461億元人民幣增加到1957年的537億元人民幣。參見:彭干梓、吳金明:《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發展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18年版。
④1978 年農村貧困發生率高達 97.5%。數據來源: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9/t20180903_1620407.html, 2018年9月3日。
⑤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3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3年7月1日。
⑥《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106155/106156/6430009.html,2007年10月15日。
⑦《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切實加強農業基礎建設進一步促進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的若干意見》,http://www.gov.cn/jrzg/2008-01/30/content_875066.htm,2007年10月23日。
⑧《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http://www.moa.gov.cn/gk/zcfg/qnhnzc/201401/t20140121_3743917.htm,2014年1月20日。
⑨《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7/30/content_8944.htm,2014年7月30日。
⑩《關于加強鄉鎮政府服務能力建設的意見》,http://www.gov.cn/zhengce/2017-02/20/content_5169482.htm,2017年2月20日。
參考文獻:
[1]賀雪峰.鄉村治理研究與村莊治理研究[J].地方財政研究,2007(3):46.
[2]任吉東.歷史的城鄉與城鄉的歷史:中國傳統城鄉關系演變淺析[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3(4):106-112.
[3]周立.鄉村振興戰略與中國的百年鄉村振興實踐[J].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3):6-13.
[4]耿國階,王亞群.城鄉關系視角下鄉村治理演變的邏輯:1949~2019[J].中國農村觀察,2019(6):19-31.
[5]金民卿.十月革命的重要遺產與中國道路的成功探索[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7(8):110-122+160.
[6]復旦大學歷史系.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140.
[7]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M]//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9.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258.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全國農民協會之重要訓令——農運新規劃五項[M]//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299.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關于鄂西黨目前的政治任務及其工作決議案[M]//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405.
[11]滕明君,張昱.建黨百年來鄉村治理范式的嬗變邏輯及新時代啟示[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3):189-194.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對政局宣言[M]//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347.
[13]劉彤,楊郁.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對農村治理的初步探索[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1):37-41.
[14]高中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鄉村治理[J].人民論壇,2021(1):103-105.
[15]丁志剛,王杰.中國鄉村治理70年:歷史演進與邏輯理路[J].中國農村觀察,2019(4):18-34.
[16]徐勇. “行政下鄉”:動員、任務和命令——現代國家向鄉土社會滲透的行政機制[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5):2-9.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中共中央關于土地改革后農村和城市工作任務及干部配備問題給華東局的指示[M]//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353.
[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迎接一九五三年的偉大任務[M]//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2.
[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M]//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453-455.
[20]吳建征,武力.國家整合與體制重塑:以1949—1956年農業合作化運動為中心考察[J].湖北社會科學,2018(12):29-35.
[21]郭振宗.我國鄉村治理的背景演變、轉型趨向與有效途徑[J].理論學刊,2020(3):76-84.
[22]李華胤.我國鄉村治理的變遷與經驗探析[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5):58-66+107.
[23]劉守英,熊雪鋒.中國鄉村治理的制度與秩序演變——一個國家治理視角的回顧與評論[J].農業經濟問題,2018(9):10-23.
[24]徐勇.論現代化中后期的鄉村振興[J].社會科學研究,2019(2):36-41.
[25]武力,張強.鄉村社會治理結構的四次變革[J].國家治理,2015(14):14-25.
[26]黨國英.我國鄉鎮機構改革的回顧與展望[J].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09(3):29-31.
[27]周少來,孫瑩.鄉村的“空心化”問題及其治理——城鄉一體化視角下的制度創新[J].理論學刊,2017(2):111-117.
[28]王衛星.美麗鄉村建設:現狀與對策[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1):1-6.
[29]王惠林,洪明.政府治理與村民自治的互動機制、理論解釋及政策啟示——基于“美麗鄉村建設”的案例分析[J].學習與實踐,2018(3):105-112.
[30]徐勇.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鄉村治理創新[J].中國農村經濟,2016(10):23-26.
[31]胡建.城鄉一體化背景下農村社區治理的現代轉型[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2):54-62.
[32]曹立前,尹吉東.治理轉型:從傳統鄉村到新型農村社區[J].農村經濟,2016(11):27-33.
[33]王超.我國農村社區治理模式研究[D].合肥:安徽農業大學, 2015.
[34]徐光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N].人民法院報,2018-07-20.
[35]孫燕.推進“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建設[J].群眾,2018(1):61-62.
[36]劉守英,王一鴿.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中國轉型的鄉村變遷視角[J].管理世界,2018(10):128-146+232.
[37]張海鵬.中國城鄉關系演變70年:從分割到融合[J].中國農村經濟,2019(3):2-18.
[38]岳奎.從一元治理到黨領導下的鄉村自治——中國鄉村治理七十年[J].國家治理,2019(28):7-11.
[39]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N].人民日報,2019-01-11.
責任編輯:武玲玲
Centennial Rural Governance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Native Rural China
to Urban-rural Chin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Wang Yuru, Yang Jihan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the explor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has gone through nearly a hundred years. In the process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PCs rural governance policies have alway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ituation or policies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party used rural areas to encircle the cities; and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focu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each stage, there has experienced four periods: urban-rural dual, urban-rural imbalance,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party has made effective explorations and innovations in the objectives, subjects and methods of rural governance. By systematically combing the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f rural governance of the CPC,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was link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logic of rural governance over the past century.
Key words: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rural governance; urban-rural re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