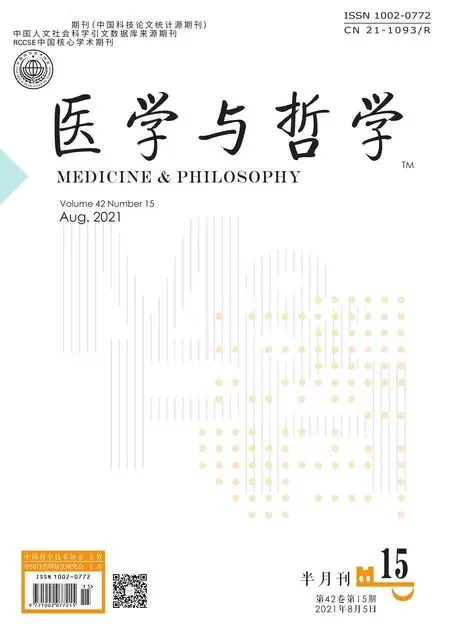手術擴大化的倫理審視與科學防范*
但漢雷 姜怡璇
人類疾病可分為以手術為主的外科疾病和以藥物等非手術為主的內科疾病。外科疾病主要涉及各種創傷、感染、腫瘤、結石、畸形以及心腦血管疾病和器官移植等。隨著醫學理論和技術發展,一些疾病分類和治療方法發生了明顯變化,如胃潰瘍過去常常需要外科手術治療,現在則主要靠內科藥物治療,肢體血管曲張、出血、栓塞等疾病過去常常采取開放手術,目前發展到以介入微創手術為主。外科手術方式、方法甚至基礎理論和技巧也發生了一系列革命性進步和變革[1-2]。在外科臨床實踐和手術技術發展進程中,存在兩種不良傾向:一是固步自封、因循守舊、不敢作為,甚至見死不救和對創新發展排斥打壓;二是在不斷攀升的醫療需求、不良行為和不當政策等因素驅使下,出現了手術擴大化等過度醫療(medical overuse),付出了不應有、不必要的代價[3-6]。
據統計分析,全世界每年實施大手術數量約為2.34億,手術并發癥發生率為3%~17%,一年內全球至少有700萬例手術在術后發生了并發癥,至少有將近100萬人在術后30天內死亡[4,6]。其中,有的屬于患方要求、簽署知情同意并經過相關審查的科研探索,出現了意外和并發癥,是否值得推廣,有待商榷,如乳腺癌基因攜帶者的預防性切除和多臟器病變廣泛切除等高精尖、復雜手術[7-8];有的因技術條件限制、試圖通過擴大手術范圍以爭取更好的治療效果,結果事與愿違,帶來慘痛的經驗和教訓,如傳統的腫瘤擴大根治、擴大超根治術和肢體腫瘤的擴大切除等[2,7-9];也有一些突破規范底線的過度手術亂象,嚴重影響了行業風氣和形象,見圖1。本文根據臨床實踐和大量文獻調研,從歷史與現實結合的角度,針對手術擴大化的表現形式、主要原因及其危害防范進行分析探討,以提高對手術擴大化的正確認識和科學防范水平。

圖1 手術合理適度與非常規和過度應用的幾種情況
1 手術擴大化的表現形式與歷史變遷
1.1 手術擴大化的技術分類和應用分類
臨床實踐中,根據技術特點,一般將“手術擴大”分為切口擴大、路徑擴大和切除范圍擴大。在傳統開放手術中,為了充分暴露和顯示病變,創造安全操作空間,提供清晰可見的手術視野,要求手術切口足夠大、路徑簡捷,反之,不僅影響手術視野和操作安全,也可能導致病變切除困難、病變殘留,甚至意外損傷、大出血,結果風險代價更大。路徑擴大主要見于比較深在病變切除,如胸腔和腹膜后腫瘤,往往一個小病變,需要很大切口和很大暴露空間。至于切除范圍擴大常見于多種腫瘤根治、擴大根治術和擴大超根治術。
臨床應用分類是從患者病情需要程度、緊迫性(輕重緩急)、手術適應證選擇、不同手術方式及其不同風險和獲益價值等角度進行分類,包括適宜、不適宜,正常、非正常,適度、過度等。Brownlee等[6]提出,當手術擴大應用導致手術風險和危害大于臨床獲益,屬于“手術過度應用”(surgical overuse),即手術范圍、適應證和技術應用的擴大化(overutilization,overmedicalization),包括高風險、低價值手術(high-risk low-value surgery)和高精尖疑難復雜手術的不恰當應用等[10]。當前,手術過度的具體判斷和分析是比較復雜和困難的,一般采取以現有診療規范或指南建議為標準。隨著內窺鏡和介入微創技術的進步,新的技術方法和理念正在改變著傳統手術模式,手術擴大化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如通過利弊分析,用于人群普查的胃腸鏡檢查,對于低風險人群的應用屬于過度;對于高風險腫瘤基因攜帶者實施預防性手術目前基本認可,但對具體手術方式還有爭議。
1.2 手術擴大化的典型歷史表現與變化
以乳腺癌手術為例,其規范和建議手術方式及其理論依據經歷了幾個重要階段性變化,見圖2。早在18世紀,只能采取原始的局部燒烙、夾切等方法,患者很痛苦且并發癥很多,治愈率很低;19世紀Halsted等根據乳腺癌淋巴轉移規律,采取全乳切除及胸大小肌和腋窩淋巴結清掃的傳統經典根治術,治愈率明顯提高,但留下了明顯的形體缺陷和并發癥;第三階段是Magottini和Urban等為了更徹底清掃鎖骨上下和內乳、縱膈淋巴結,采取擴大根治術和超根治術,治愈率未見明顯提高,相反手術創傷、并發癥和手術死亡率卻明顯增加,未能如愿以償;20世紀隨著乳腺癌研究的不斷深入,Patey、Auchincloss和Bernard Fisher等分別提出了改良根治術、保乳手術、乳房成形術等一系列新術式;在新世紀新時代,分子生物學和基因科學的進步,放化療、內分泌治療、生物靶向治療的興起以及介入微創手術的普及,乳腺癌手術進入精準(precise)和微創(minimally invasive)治療新時代,手術創傷更小、恢復效果更好、治愈率更高、無病生存時間更長[11-12]。

圖2 乳腺癌手術理論與方式的歷史變遷
與乳腺癌類似,胃癌、結直腸癌和肺癌等也經歷了根治、擴大根治再到微創手術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晚期胃癌,特別是胃壁浸潤型(鮑曼Ⅳ型)手術很難切干凈,術后復發率高;相反,全身系統治療,特別是靶向化療效果明顯[13-14]。中晚期肺癌實施擴大根治術,常常導致較高的手術相關死亡率,且手術根治率很低[15]。隨著低劑量螺旋CT對早期肺癌篩查的普及,磨玻璃結節型肺癌的檢出率大大提高,這些早期病例按新規范建議,應采取局部楔形切除術,如果還采取傳統解剖性肺葉切除和縱隔淋巴結清掃,顯然屬于手術過度[16]。
回顧幾百年的臨床經驗和最新研究顯示,擴大手術范圍或者墨守成規、按傳統方案,都不能獲得更好的臨床效果,精準、微創、合理適度(appropriate and rational/reasonable)才是手術基本原則和規范要求。在分析判斷手術是否適宜或過度,必須根據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客觀條件和認識水平、手術規范標準等情況全面、具體分析。19世紀做個乳腺癌的擴大根治屬于“合理適度”的選擇,到了20世紀、21世紀,這顯然不合適。在經驗醫學時代,各種探查性手術、切口延長、范圍擴大的“家常便飯”不能再吃了。
2 手術擴大化的現實亂象及其原因分析
當前,手術擴大化亂象正在眾多醫學領域和地區出現,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10]。一項由《柳葉刀》雜志和27位國際專家開展的研究表明,美國各州不恰當子宮切除比例在16%~70%,不恰當膝關節置換術在西班牙和美國的比例分別是26%和34%,不恰當子宮切除在中國臺灣地區是20%,在瑞士是13%;參加此項研究的美國專家分析認為,導致上述情況的主要原因是“貪婪、逐利和信息缺乏”,且不同的國家、地區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群體發生情況明顯不同[4-6,10]。結合臨床實踐和大量文獻分析表明,以臨床過度應用為特點的“手術擴大化”,其性質不同于不負責任的“手術差錯”與“手術事故”,二者不應混淆,但二者的原因具有相似性,都有客觀上的經濟技術和文化發展差異、診療條件限制、病情疑難復雜或緊急,以及臨床技術和經驗欠缺等,主觀上有技術炫耀、追逐名利、法規意識淡漠、職業道德和精神淪喪,還有技術培訓、管理和倫理審查不足等。其中,主要因素是過度強調手術作用的炫技傾向、追風逐利和法規意識淡漠等。
2.1 技術派的炫技傾向
這種現象主要指過分夸大手術作用,忽視其他方法與綜合治療[17]。具體表現為,面對多種診療選擇和指南推薦,習慣于首選手術,對中晚期腫瘤一律采取擴大切除老方法,不選擇新輔助、靶向化療等綜合措施;有的無論有無淋巴結轉移都清掃、擴大清掃,不掌握或不采取前哨淋巴結活檢、分子染色、精準邊緣分離切除等新理念、新技術,反正按老辦法一切了事;也有個別的各種新方法齊上陣,多種高精尖、微創技術都用上,如甲狀腺良性腫瘤和乳頭狀微小癌,本來可以簡單應用介入微創、“一針消融”解決問題,卻選擇開放手術、擴大切除、機器人輔助等,忽略具體病情及經濟承受能力,結果是“大炮打鳥,費力不得好”。
技術派(technicians/technocrats)的炫技亂象,在腫瘤治療中突出表現為:“所有腫瘤先動刀,輔助治療不搞噱頭;手術辛苦全白干,切不干凈還擴散;結果,該治好的治不好,費用時間打水漂”。其做派確實也辛苦,似乎也“遵循規范指南”,其實違背了“以人為本”的醫學倫理和“對癥下藥、因人施治”的職業道德要求,也是醫學人文對臨床技術監督缺失、導向不力所致[18]。
2.2 盲目跟風趕時髦
隨著手術技術突飛猛進,一些單位和個人沒有深入研究和消化吸收,引進新技術不注意個體化、人性化、本地化,出現水土不服。如開展介入手術缺乏影像技術的精準引導,開展重要臟器手術無麻醉和危重醫學的配合,基層單位不積極開展簡便有效的適宜技術,卻花時間和精力追逐干細胞等高精尖熱門技術,顯然不合時宜[19-20]。
手術領域跟風趕時髦的拿來主義典型特征是“鸚鵡學舌”“照抄照搬”,缺乏“消化吸收”,更無“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有時表現為簡單技術集成而無創新發展。在腫瘤消融技術引進國內的早期,用肝臟消融的傘狀電極消融肺腫瘤,沒有專門的鞘管引導技術,結果氣胸、出血發生率高;用粗針固定消融甲狀腺結節,而沒有采取改進的細針移動消融技術,結果消融適形效果差,完全消融率低;也有單純注重消融技術的精準、微創,忽視全身系統治療的配合,雖然局部控制滿意,全身復發轉移率卻沒改善,總體生存率和臨床獲益無明顯提高[21-23]。
2.3 逐利者的妄為
我國新醫改十年,醫療衛生行業進行了快速擴張,在緩解醫療需求緊張局面的同時,也為我國衛生事業發展帶來了新挑戰[24]。由于過分強調經濟激勵政策和監管缺失、專業技術人員職業教育不足等因素,導致過度醫療亂象發生,出現了手術項目分解重復收費、小病大手術、穩定性冠心病過度安置支架等現象[25-26]。在經濟利益驅使下,有些醫院和從業人員違背“尊重生命、尊重患者”的基本倫理,違背“尊重科學”和安全有效的基本要求,醫患溝通流于形式,醫患關系不夠融洽,甚至借高新技術推廣和轉換研究之名,實則推銷高值耗材或新特藥物而獲取高額回報,行業風氣和形象受到破壞[27-28]。不可否認,經濟激勵和創新驅動政策對醫療衛生事業的巨大作用,但過度的逐利行為和政策失控,嚴重影響著醫療行業的社會福利和公益性[29]。
2.4 不斷攀升的醫療需求
研究表明,不斷攀升的醫療需求,既是推動手術技術進步的主要動力,也是引發手術過度的主要動因。從乳腺癌手術理論和技術的歷史變遷可見,古代由于技術條件限制,人們只能談癌色變、望瘤興嘆,近現代為了保命求生存,只能忍痛割愛、根治及擴大根治,而今人們不僅要治病保命,也要保乳、保健康,還要求精神、心理和社會活動全面康復[2]。患方過高、過多的期盼,特別是對術后并發癥和復發轉移、再發病變的擔憂,自然引發保護性、防御性醫療(defensive medicine),出現“筑高壩、防低水”現象,如為了減少腫瘤術后復發轉移,仍然采取擴大根治手術,為了防止一些不利的蛛絲馬跡、防止術后患方的詬病,采取把能做的都做了的策略,必然出現過度的、不恰當的醫療行為[30]。
保護性、防御性醫療在一些情況下,確實是從患者利益出發,屬于對患者生命和健康權益的尊重和高度負責,如高復發危險的乳腺癌預防性切除健側乳房,也可能因為癌變風險高或乳房重建美學需要,從醫學倫理和法學角度,這些不應歸于過度醫療或侵權,雖然有待進一步研究評價,但不應一味質疑和責難[31]。
2.5 忽視規范,突破底線
不可否認,除了醫患雙方信息不對稱、對當時常規規范不了解或把握不準,確實也不同程度存在由于過分逐利和違規,導致手術過度亂象,如故意擴大手術適應證、小病大手術、可保守觀察卻選擇激進的手術等。個別情況觸及違法違規的底線,如美容行業個別高度不負責任、未取得執業和手術許可、超范圍執業造成患者生命和健康傷害甚至死亡等情況;嚴重、惡意的手術擴大化,不僅違反醫療行政法規甚至造成患者人身損害或發生醫療事故者,構成醫療損害侵權、非法行醫或醫療事故罪,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恰當、不適宜或超出常規或技術指南的手術行為,屬于技術管理和手術倫理問題,也是可防可控的[32]。
3 科學防控手術擴大化
根據Chassin和Galvin的定義,過度的手術擴大化屬于“過度醫療”的“過度治療”或“過度干預”,其危害不僅表現為對患者的身體、精神心理和經濟造成不必要的傷害和損失,甚至引發醫鬧、醫暴事件,也會耗費不必要的公共衛生和其他社會資源[6,10]。在臨床實踐中,傷病的治與不治,“姑息”還是“積極”,手術如何適度而不過度?問題是相當的復雜和專業,很多困境和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解決,臨床指南、規范和倫理爭論也沒有休止[33]。但從技術和倫理學角度看,無論什么主客觀原因和利弊權衡,過度的手術擴大化亂象應該避免。人文倫理審視應該深入到手術技術領域,深入到手術決策、實施、術后康復和價值評估等具體過程和環節,見表1。

表1 防范手術風險的科學人文理念與法律要求
我國著名醫學人文學家杜治政教授[4]提出,“倫理覺察可提高手術質量和水平”。美國哈佛大學外科醫生阿思爾·加萬德等通過《手術安全核查表》在全球8個城市進行測試研究表明,推行該核查表前,有8家醫院術后30天內手術死亡率為1.5%,而推行該核查表后,其死亡率降至0.8%,總體降低了47%,在幾個發展中國家則降低了52%[3-6,10]。根據臨床實踐和文獻研究,筆者認為,防范手術擴大化,應在堅持基本法規底線前提下,從歷史發展和客觀實際出發,用科學倫理導向,采取全面、綜合的手術風險與獲益分析和考量,強化原則把控,確保技術向善,見圖3。

圖3 手術倫理審視與過度醫療防控的基本原則
3.1 手術獲益與風險評估和分擔
手術可以治病救人,也有創傷和風險。選擇了手術,就要面對和承擔與手術相關的各種損傷、意外和并發癥。“高獲益常常伴隨高風險”,這是客觀存在的現實。如何踩好鋼絲、彈好鋼琴、掌控好“刀尖”技藝,是術者的必備修煉。雖然醫患雙方自然都希望千方百計降低風險和代價,但是,即使再先進的微創手術,各種副損傷和并發癥依然難免。而且,手術也不能包治百病,手術醫生除了手術成功的竊喜,面臨更多的可能是風險和擔憂,甚至醫鬧和醫暴[34]。再則手術技術的成功也并不等于傷病的治愈或獲益,嚴重的手術并發癥、過高的費用負擔可能導致前功盡棄,甚至引起政治性、經濟性問題[35]。
然而,“救死扶傷、治病救人”的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平正義原則,要求醫患雙方獲益與風險應得,這是醫療領域的“公序良俗”。歷史上蔡桓公不聽扁鵲之言,病入膏肓而不治,曹操殺了醫生,結果自己抱頭痛死;當今醫鬧、醫暴折騰醫院、醫生,催生過度的防御性、保護性醫療,導致醫患雙方都付出了不必要的更多代價。其實,醫患雙方應是共同對付傷病的利益與命運共同體,維系和諧的醫療生態,必須醫患雙方共享決策、智慧決策,共同開展手術風險和獲益的科學量化研究,共同評估和分擔風險,這不僅從體制機制上充分體現公平正義,也有助于融洽醫患關系、充分實施人性化問題疏導,構建醫患和諧文化[36]。
3.2 安全有效與法規政策導向
手術屬于高獲益、高風險的臨床技術,手術“安全有效”是基本的、起碼的技術要求,任何手術都不例外。長期以來,經過臨床實踐和經驗積累,建立了一系列手術相關法規制度,見表1,如患者知情同意與簽字、風險評估和告知、手術分級管理、重大疑難手術三級檢診查房、術前多學科會診討論等。手術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手術技術與風險管理方面,還有手術人員崗前培訓、技術準入管理以及術中、術后技術監管等規章和規范,包括重大手術意外和并發癥總結分析與報備、手術耗材和植入器材管理規定等[37]。可以說,防范手術過度與不及、降低手術風險、確保手術安全的法律制度比較健全,關鍵在貫徹落實。
近年來,新醫改政策通過醫療收入與分配直接脫鉤,加強執業監管,在高新技術手術管理上,更加注重技術的可及性、普及性和衛生經濟可承受性,特別是嚴格管控高值耗材、取消加成回扣、實行集中限量采購、大幅度降低采購價格、實行按病種醫保付費等措施,過分逐利的醫療亂象明顯得到遏制,但問題并沒有徹底解決[38-39]。應該認識到,一項醫療政策改革難以一勞永逸,改革永遠在路上。防范手術擴大化等過度醫療,還應從微觀的技術進步、宏觀的倫理導向等多方面出手[40]。
3.3 精益求精與高獲益、低風險追求
醫海無涯,學無止境。臨床醫學充滿了無數的未知數,臨床醫生很難一下子就做到一切都恰到好處;臨床診療既不過度又無不及,是一種高超的技藝,是醫生竭盡全力也比較難以達到的境界。但手術直接關系到患者的生命和健康,屬于高風險作業,一刀下去,也許手到病除,也許神經血管切斷了、臨近臟器損傷了、出血止不住了、術后感染了、傷口長不好了,一大堆可能的并發癥,甚至終生殘疾或者生命難保。
上百年來,醫學家們做出了無數努力,倡導精益求精,追求至善至美,手術風險明顯降低,監測設備的技術水平明顯提高,外科手術朝著“高獲益、低風險”方向不斷發展進步:如甲狀腺手術中喉返神經的探測和保護,肝膽手術中超聲的應用,膽道手術從巨創的剖腹探查到腹腔鏡微創手術、精準影像指導的內窺鏡自然腔道手術、經皮經肝膽道鏡手術(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oscopy,PTCS)等[41],許多手術方式和技巧乃至基本理論和操作規程都發生了革命性變化,這些難能可貴的技術進展極不容易,也的確帶來了精準微創、高獲益/低風險的曙光,防范手術過度,應該鼓勵沿著這條正確的道路不斷前行。
3.4 科學傳承與創新發展
手術的“高獲益、高風險”能夠變成“高獲益、低風險”,關鍵依賴手術技術及其科學傳承與創新發展,即不斷的技術進步和決策改進。作為醫學技藝,手術需要術者具有高度的責任和擔當精神,需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科技創新性和藝術創造性。一臺成功完美的手術,凝聚了手術團隊的無數科技智慧和辛勤汗水。吳孟超院士能夠“手到病除”絕非一日之功,開創肝膽外科史上多個第一(第一例巨大海綿狀血管瘤切除術、第一例腹腔鏡肝葉切除、第一例肝癌鑄型解剖研究等),每一個第一都經歷了風險,也凝聚了自己或別人曾經的失敗和經驗教訓,難能可貴。
手術也是實踐性、技藝性很強的科學。“師傅引入門,修行在個人”,一個成熟的外科醫生沒有8年~10年的磨練難成大器。面對日新月異,新理念、新技術不斷涌現的新時代,只有傳承和老經驗必然落伍,難以與時俱進。新出現的減肥減重術式,如果沒有生活方式和行為管控,療效有限,再次說明解決新問題,需用新技術、新方略;在用新手術治療疑難復雜疾病時,也必須協調多方面人員,團結協作,集智攻關,合理應用并促進相關學科共同發展[42]。當面對一位年輕孕婦查出癌癥、為了孩子甘愿放棄生命的偉大母親,手術絕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更是如何敬重患者,如何挽救兩條生命、護佑偉大母愛的高尚圣潔之舉,唯有膽大心細、勇于創新、德藝雙馨者方可擔當。
4 結語
總而言之,當前所謂“手術擴大化”與“精準微創、合理適度”要求相悖,是全球性醫療技術管理和臨床倫理問題,不僅造成患方不必要的身心和經濟損失,也給醫方造成不必要的衛生和其他資源浪費,甚至涉及違法違規等嚴重后果,必須端正醫療服務思想和觀念,加強管控,解決好技術教育與培訓不足、設備條件局限、團隊配合不佳、醫患溝通不當、風險防控不好等問題。對絕大多數因病情疑難復雜危重、客觀條件限制、情況緊急而難以精準微創或來不及而為之,雖情有可原,也應努力避免,積極采取系統全面、宏觀和微觀兼備的科學防范措施,如手術標準和規范的優化、技術改進、醫保政策調整、醫患和諧文化建設等多措并舉。至于創新研究和改革探索,則應有容錯理念和引導科技向善的機制,大力彰顯“革故鼎新的勇氣和堅忍不拔的定力”,為人民生命健康,直面問題、迎難而上,為“創新中國、健康中國”建設而呼號奮進。
(致謝:感謝杜治政教授對本文的審改建議,特別是提出“端正醫療服務思想和觀念”的重要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