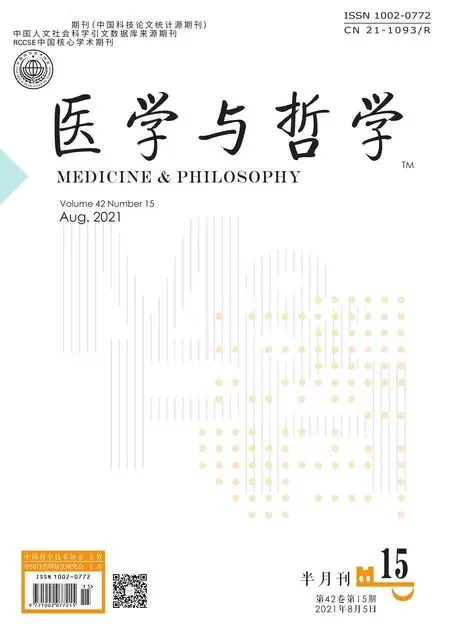新冠疫情下海外華人中醫接受度調查*——以英國牛津地區為例
彭衛華 張 苗
2020年初,全球開始暴發新冠疫情。本文對這場偶然事件的關注,更具社會學視角,即給予在既定的理性社會結構中討論“事件”原生、次生帶來的諸多特殊現象的特殊分析,并試圖在社會中還原“事件”暴露的社會文化現象。新冠疫情是一個世界公共性的突發事件。中醫,既是一種民族文化符號,又是一種醫學臨床技術。在突發的新冠疫情面前,現代醫療的應對放大了其“科學研究”滯后性的弊端,而將中醫作為一種實用的臨床技術推向了身患緊急性疾病的患者,這是在“中醫”產生的本土地域所發生的狀況。但在“中醫”文化的異鄉、地域異鄉的人群中,中醫在新冠疫情中被大家接受的樣態是怎樣的呢?這種樣態背后的文化和社會的因果鏈是什么?這些文化和社會的因果鏈又能引起哪些“事件”性的思考,是本文嘗試做出的理性努力。
1 研究緣起
以目前已知的信息來看,新冠疫情于2020年年初開始在全球范圍內流行。在疫情暴發前,本研究對于牛津地區中醫的整體狀況進行了初步實地調研的田野調查。在疫情暴發后,本研究采用線上方式在牛津地區華人中開展了對于中醫看法的問卷調查和訪談調查。
1.1 英國疫情概況
2020年3月,新冠病毒在英國國內的傳播風雨如磐。3月2日,英國首相約翰遜首次承認,英國可能會有數以千計的人感染新冠肺炎,而同日另一媒體也報導,有衛生專家認為“目前疫情尚未在英國本土自由傳播”,而在受訪的1 600名醫護人員中,只有8人認為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為應對疫情做好了準備。直到3月5日,英國當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36例,英國政府首腦科學顧問承認,新冠肺炎已經開始在英國暴發。時隔7天,即3月12日,政府官員承認英國國內可能已經有多達一萬人感染了新冠肺炎。然而此時,英國政府并沒有公布會采取關閉學校、取消大型活動等措施的計劃。但這一切在太陽升起的第二天,就完全改變了,這一天英國遭遇了單日增加新冠肺炎確診患者人數為208例,是疫情暴發以來人數最多的一天。首相約翰遜3月13日馬上宣布從下周開始取消所有體育賽事、音樂會及其他大型活動。事實上,他在前一天還堅稱不會效仿蘇格蘭地區禁止500人以上集會的做法。新冠疫情在英國瞬息萬變情況,引起了許多在英華人的恐慌。不論是對疾病憂患意識的文化傳統,還是之前對國內疫情新聞的重視和關注,都讓此時此刻在英的華人為疫情暴發后的去留感到焦慮。
1.2 牛津地區華人及中醫概況
牛津,地理上是英國英格蘭地區版塊之一。牛津享譽世界的標志即是牛津大學,所以牛津地區的華人很多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既有在牛津進行留學深造的人群,也有為追求更好的教學資源而在牛津進行中小學留學的人群,當然也存在源于其他原因來到英國的人群,如醫護工作從業人員等。
牛津地區有能獲得中醫治療服務的渠道和平臺。以是否直接獲利為標準,平臺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商業模式平臺,另一種是科普模式平臺。在商業模式平臺中,又分為兩種:商業街門店模式和社區服務模式。在牛津,提供自然療法保健服務的商業不少,中醫服務僅是其中的一種,其他的還有瑜伽館、泰式按摩館。牛津地區商業模式中最容易被發現的一家中醫服務門店設立在最繁華的商業街。該門店主要以針灸、按摩治療為主,兼營中藥。顧客群體兼具流動性和固定性。除此之外,還有設立在社區的中醫服務。通過科普模式進行傳播的中醫,以在華人社區中心開設講座、免費診療咨詢等為主要形式。宣講者一般為中醫從業者,他們一方面宣傳中醫藥保健知識,另一方面建立客戶群體。華人社區中富含中國式的“熟人社會”特色,內在蘊含中國傳統組織結構特點。故而,中醫的醫術優良與否并不是宣講人的重要素質因素。這一點,在新冠疫情暴發中被凸顯出來。
除了中醫提供服務的平臺和中醫的從業人員之外,接受中醫的患者人群樣態也有其特點。英國是高福利國家,NHS為所有具有合法身份留居英國的人員提供全員免費醫療服務。正因為如此,NHS服務覆蓋面廣,但卻囿于醫療條件,醫療服務的深度也有限。中醫在英國屬于自費項目,不進入NHS 的服務體系。在英國接受中醫提供治療服務的人群根據其文化背景,主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為文化的同鄉人,另一類則為文化的異鄉人[1]。所謂的文化同鄉人,是指具有中國文化或者中醫文化淵源的人,如華裔、具有華裔血統的,有中國文化背景的人群。而文化異鄉人則是指與中國文化或者中醫文化沒有歷史牽連的人群。無疑,第一類人群的中醫接受度是比較高的。放置在英國當下的社會文化背景來看,第二類人群的中醫接受度也并不比第一類人群低。主要原因在于英國社會文化中彌漫著對“科學化”“醫療化”的抵制。所以這些接受中醫的文化異鄉人,更多地是出于自己文化中的“理性”背景而找到中醫的。這種狀況的另一個例證來自于英國與中醫相關的書籍市場。
2 疫情暴發初期中醫在牛津的接受度問卷調查情況
2020年4月~6月,筆者在牛津華人微信群開展了問卷調查。值得說明的是,微信群在牛津地區華人中的使用頻率比較高,尤其在疫情期間,可以說微信使用滲透到牛津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2.1 問卷調查對象
疫情期間,該問卷在微信群的華人中展開,共發放調查問卷110份,回收有效問卷106份。其中男性為57人,占53.77%;女性為49人,占46.23%。其在英居住時間分布為,1年以內的占57.55%,1年~5年的占21.70%,5年~10年的占8.49%,10年以上的占12.26%。調查對象的留英原因組成則為,被迫滯留的占2.83%,移民的占5.66%,工作的占40.57%,求學的占17.92%,訪學人員26.42%,其他原因占6.60%。
2.2 選擇中醫意愿
調查對象每年看病的頻率分布情況為,一年5次以下者為86.79%,5次~10次者為11.33%,10次以上者為1.88%。而在英國就診選擇中醫的頻率為,從未看過中醫的為45.28%,偶爾(1次~2次)的為42.46%,有時(5次以內)的為6.60%,經常(5次以上)的為5.66%。而在英國是否自己使用過各種渠道獲得的中成藥的比例則為48.11%與51.89%。
2.3 對中醫的看法
調查對象對中醫的看法的分布情況如下,疫情前對中醫的印象認為有自己的優勢的占61.32%,認為不科學的占32.08%,認為有效的占6.60%。而對中醫藥對新冠療效的看法分布是,相信中醫藥有效的占59.44%,不相信中醫藥有效的占31.13%,認為說不清的占9.43%。在疫情后對中醫的印象卻與疫情前有了明顯的不同,疫情后認為中醫有自己優勢的占81.13%,認為中醫不科學的占7.55%,認為中醫有效的占11.32%。疫情后會更多地選擇中醫藥治療的分布情況為,選擇中醫的占26.42%,不選擇中醫的占35.84%,看情況而定的占37.74%。這其中,一年看病5次以下的人群,不選擇中醫的占7.60%,選擇中醫的占58.70%,而看情況決定的占33.70%;一年中就醫5次~10次的選擇中醫的比例是8.33%;不選擇中醫的比例是16.67%;看情況決定的是75.00%。
因為移民原因在英國的人群相信中醫對新冠肺炎的作用有效的占比為100.00%。因為工作原因在英國的人群中對中醫對新冠肺炎的作用的占比情況為,相信中醫有效的占34.88%,不相信中醫有效的占60.47%,認為說不清的占4.65%。因為求學原因在英國的人群,認為中醫有效的占52.63%,不相信中醫有效的占21.05%,認為說不清的占26.32%。
其中移民身份的在英華人對中醫的信任度最高,其次為訪學人員。值得注意的是,在英求學的年輕人群體對中醫的接受及信任度較低。
3 思考與討論:“禮物”——新冠疫情下的中醫
從對新冠肺炎治療的本身來講,中國傳統中醫藥的方法在國內的實踐無疑是中醫對于新冠肺炎有效的鐵證。新冠疫情中中醫藥的事實性有效,無疑讓我們國人看到了中醫藥“禮物”般的價值和意義。然而,禮物的傳遞,必須考慮其實際過程和實際在場。如果禮物的傳遞僅僅是一種一廂情愿,那么禮物本身不僅難以成為中國式的“禮”之物以傳達善意,甚至會被溢出解讀為西方莫斯[2]3式的“禮物”,而更傳遞“交換”“互惠”意味的信息。
3.1 “禮物”的受眾
在文化異鄉中更多地被標簽化為“文化性”和“民族性”的非主流之醫藥方法,其實際效用的開展卻是有著諸多不同層面的屏障。撇開全球化視野下國際關系中各國的文化隔閡不論,盡管這一層次中民族主義與全球化的背景是中醫藥進行海外傳播非常重要的網格背景,民間大眾對于“文化異鄉”的中醫藥觀念、方法、思維接受度的實際層面是值得細致探究的。
如前所述,中醫海外接受主要有兩類人群。從上述調查問卷來看,文化同鄉對于中醫藥的接受度并不是一種確然的無間隙性傳遞。由這些數據可以勾勒出在英華人人群對中醫看法的幾個維度:首先,中醫作為一種具有標識性的民族符號的非主流醫學,在“文化同鄉”人群中的傳遞并不是以其醫學理性知識而更被認可。調查顯示,中醫理論并不是他們獲得中醫理性知識的主要渠道,中醫理性知識也不是國外華人所重點關注的。其次,更多的中醫藥實際運用在“文化同鄉”中是作為一種“習俗”而被使用。此次調查展示了一個事實:“習俗”是中醫藥在華人間傳播的非常重要的標簽,而非一種非常正式的醫療活動。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勞斯(Rouse)[3]曾指出,在移民的話語中,遷徙的人群的經歷只能被想象成為兩種可能的方式:循環的和線性的。在第一種情況下,人們保持自己舊的認同,銘記自己的家鄉,并最終返回那里。在第二種狀況下,人們拋棄了曾經的家鄉和認同,在接納自己的社會中定居并最終為其所同化。由此可見,一方面中醫接受的“文化同鄉”,必然是地理上“離鄉”狀態的人群,他們一方面通過作為民俗和生活習慣的中醫延續著血統中的文化情懷,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必須接受身體實際地理“在場”的行為同步化,以此來獲得實際在場環境的歸屬和認同。在新冠疫情這樣一個特殊的事件中,地理在場的英國政府所表現出來的應急能力和實際提供的社會福利,凸顯出了地理在場的劣勢。而實際所處的社會環境,也有諸如“質疑華人戴口罩”“華人街頭被歧視”這樣的新聞和親身經歷不絕于耳。但是,他們并沒有因此而完全將日常生活中一直使用的中醫藥“習俗”放大為確然的治療選擇。調查顯示,疫情后會更多地選擇中醫藥治療的占26.42%,不會的占35.84%,看情況而定的占37.74%。不選擇中醫的和看情況而定的占73.58%。
而在接受中醫的“文化異鄉”人中的狀況,卻是另一種呈現。筆者在與一位曾經來中國學習過中國文化的當地人訪談,在訪談時他身體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咳嗽、發熱、嗓子痛等疑似新冠肺炎的癥狀。在幾次溝通中,筆者都曾經特意通過講述有效病例、中醫治療的機理等方法向他推廣中醫治療(中藥)對于新冠肺炎的有效性,但是他依然拒絕接受的中醫治療方法(服用某中成藥膠囊)。此外,還有一位已經與當地人締結了婚姻關系的華人女性與筆者聯系,她的丈夫和家人由于是英國某醫院的救護車司機,所以她意欲獲得一些中醫藥相關知識和藥物幫助她的丈夫及其家人提高免疫。在談話中,該華人女性談到她的丈夫及其親戚都“不相信”中醫方法,盡管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會幫助其進行刮痧、按摩等養生保健,但是卻不能接受服用中藥來預防新冠肺炎。在幾次溝通后,筆者建議其用水煮蒲公英的方法提高身體免疫能力,這種方法也被其本地人家屬所接受。
以上兩個個案可以看出,“中醫”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在即使是有過中國文化熏陶的“文化異鄉人”中,依然存在接受屏障。故而,中醫作為一種“特殊”的治療手段而難以被接受,主要源自根深蒂固的“文化”屏障。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政府近年來在國民教育中所推崇的核心價值觀也許應當作為一種背景知識進入我們的觀察視野。英國政府自2011年開始將本國的核心價值觀定為“民主、法治、個人自由和互相尊重信仰差異”[4]。其對核心價值觀的推崇,源自英國國內多元文化信仰帶來的社會問題[5]。具有一定的文化傳統和近代輝煌歷史的英國,正是運用核心價值觀教育來更好地讓外來種族、外來文化背景公民融入本地文化傳統。這從一個側面能夠幫助我們厘清英國本土文化主體性和領導權的現實狀況,即英國現狀包含有多元的民族、信仰的合法居民,但是英國政府也明確在教育中強化英國歷史文化傳統的主體性。在這樣的背景下,中醫藥作為一種特殊民族所沿襲的文化性、傳統性其生存空間是有限的。無論是“文化同鄉人”還是“文化異鄉人”,被當地社會建構的價值理念都對中醫藥文化的接受和傳播有離散性影響。
3.2 “禮物”受眾的“傳統”與“文化”
新冠疫情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它挑戰著已經自覺進入高度文明狀態的人類社會,也同樣對當代人類醫療技術、公共衛生健康管理是一個意外打擊。然而,這場疫情的暴發也集中放大了在應對公共災難的過程中,國家、地區間文化溝通的有限性。面對相同的公共災難,差異性地、特色性地處理災難成為國際化政治環境中標榜文化主體的一種有意或者無意的預設。不同民族、文化間的文化特性和文化分歧也得到了凸顯。中醫作為文化內部被明顯確認的特色治療如何能夠獲得“禮物”的正當性而得以傳播?在英國,中醫作為禮物被送出,朝向的是怎樣的一種受眾,其傳統和文化背景又是怎樣的?
作為一個后工業時代的資本主義國家,首先,英國當地民眾對于本地文化傳統有著根深蒂固的觀念。以牛津為例,在牛津“傳統”是一個隨處可見、頻繁出現的單詞。牛津大學的各個角落,都閃耀著歷史的光芒。無論是古代歷史中知名的宗教與強權斗爭,還是近代歷史中著名的科學與宗教斗爭,抑或是某個耳熟能詳的科學名詞或者標榜史冊的英國科學、政治等歷史人物,都能在牛津循跡到淵源。牛津大學和牛津城,將這些傳統都予以了強化和保留。 其次,在保持傳統的同時,對于現代文明和發展,保持著相當的警惕。牛津市的大部分地區都是古老的建筑,除教堂的鐘樓之外,市中心基本沒有超過5層樓的樓房。牛津市的很多馬路,也同時保持著水泥馬路和泥土馬路,因為人行道堅持不用平鋪的水泥,因而人行道中常常聽到非常刺耳的行李箱拖行的聲音。夜間的街道,也沒有燈火通明的路燈工程,路燈僅僅只是有限地照亮黑夜。市中心有集中的大規模商業區,其他地方更多見的是咖啡館、餐館或者小型超市,散在的商業區數量和規模都非常有限。
3.3 “禮”與“禮物”
中醫作為一種被醫療事實證明了可以發揮作用的醫療行為,在此次全球性的新冠疫情中,能否成為一個正當的禮物?“禮”,在中國文化中被視為儒家文化的優良傳統。“‘禮’既是社會各階層的行為規范, 也是歷代社會共同體所追求的理想社會的理論框架和價值標準, 并作為歷代社會意識形態規范著人們的生活行為、心理情操、倫理觀念和政治思想”[6]。可見,在中國文化概念中,禮物是承載著相互尊敬和相互友愛的高尚人際交往規范的實在之物。然而,值得關注的卻是“禮物”的西方思維。現代人類學理論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法國人類學家馬塞爾·莫斯曾經在他的經典著作《禮物:古代社會中的交換形式與理由》的引言中寫道:“在斯堪的納維亞文明和其他為數甚多的文明之中,交換與契約總書以禮物的形式達成,表面上這是自愿的,但實質上,送禮和回禮都是義務性的。”同時莫斯在該書著的結尾從現代社會出發對原始社會形態下的“禮物”三個層面做了總結。這三個層面是道德、經濟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和一般社會學。在道德上而言,莫斯[2]147肯定了現代社會中“物”的“情感性”,他認為饋贈與回饋一方面或多或少地包含著榮譽、面子等情感,例如,在“回報總是要更昂貴更大方”,在“遇有客人、節宴或是要給年賞時”,人們就會“揮金如土”;另一方面,莫斯還肯定了社會生活中,禮物交往對于個人和人群所帶來的“愉悅”和“歡欣”,正是因為如此社會中不同的人群才能“總體呈現制度”,人類社會的緊密聯系才在“要走出自我,要給予”這一亙古不變的原則中得以繼續。而在經濟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這個面向上,莫斯考察了“饋贈”“禮物”以及“利益”等觀念的多重含義。莫斯認為前二者之觀念“既不是純粹資源和完全白送的呈現,也不是指生產或單純意在功利的交換”,而是在社會中盛行的“雜糅的觀念”。他也認為“利益”具有多重性,并揭示出了利益觀念背后個體與集體的離散性。而莫斯也相信無論是古代社會還是他所處的現代社會,“經濟理性主義”都還不是社會生活的主流價值觀念,大眾中的“社會共同利益”具有驅動的力量。最后,在一般社會學的結論與道德的結論中,莫斯提出“社會總體事實”的原則。從西方社會學對“禮物”的社會形塑和社會功能價值的考察中,不難看出“禮物”交換的“社會”性是禮物得以成為“禮物”的重要背景。
中國文化中的“禮”也有其背后的關系形態,但這種關系形態中的“道德”成分與以莫斯為代表的西方學者所揭示的“禮物”的場域性道德不盡相同。從本次中醫在海外接受度的觀察來看,一方面中醫作為“禮物”在全球化背景下進行傳播的障礙,或許恰恰在于“文化”流動中的各種社會實際條件的不能;另一方面,人類社會的集體聯結中“共同性”也預設了中醫傳播必然性的出口。如何將具有現實價值的“中醫”作為禮物更有效地推送至世界,是當代學者的歷史任務。從文化交往理論來看,文化涵化、文化同化或者文化異化,都包含實際場域的實際問題,而不僅僅是哲學或者文化學的問題。例如,新冠疫情作為一個突出性的公共事件暴露了全球政治生態中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意識形態偏見,中醫如何體現“禮物”的價值,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獲得“禮物”的正當性。中醫要進行“異文化”向度的傳播和交流,就必然需要展開對“異文化”條件和背景的各個維度的調查和研究,尤其是作為接受方的文化條件和背景的討論。值得當下的中醫藥傳播研究者關注的是,“禮”不是一場一廂情愿的給予策略,卻是一種以尊重為前提的真誠與鄭重;禮物的質性不僅體現在“物”的價值性,還應體現在以“命運共同體”為前提的相互與交往。而從新冠疫情暴發來看,海外“文化異鄉”情景中既有有利于中醫藥得以開展的對現代醫學的態度、對自然療法的觀念等文化場域,也有對于民族主體的明確、對異文化認同的障礙等現實不利條件,更有整個現代社會中“同質性”的人的生存境遇的現實狀況。如何充分將中醫藥的價值性和在場的現實條件相結合,恐怕是當代中醫海外傳播以及中醫的當代文化自覺[7]更值得關注的問題。
4 結語
以目前的中醫藥海外傳播研究來看,業內對中醫藥海外傳播的研究中大多將“文化”與中醫藥的海外傳播相關聯。“中醫藥文化理論的傳播是中醫藥文化跨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內容”[8]是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然而值得關注的是,文化傳播和文化交流中的實際情景也是極其重要的因素之一。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是一個偶然“事件”,正是這種偶然“事件”激發了平常狀態中被隱匿的真實,偶然事件將中醫“拋入”全球化國際關系真實面貌中。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跨文化交流中不僅有文化傳播,還可能帶來文化涵化、文化同化和文化異化等問題。以英國為例,“傳統”和“文化”是當下其自身自覺進行建構和標榜的主題,如何在這樣的氛圍中,將同樣具有“傳統”屬性的中醫作為“共同”性意涵下的“禮物”呈現,是當下研究必須面對的問題意識。換言之,當下中醫藥海外傳播的研究,除了要在中醫主體性話語建構的基礎上探究中醫的禮物價值性之外,還需要從“文化異鄉”的人群的生活狀態、生存狀態、價值觀念趨向中挖掘當代中醫藥的現實價值,并延展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以中醫為代表的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