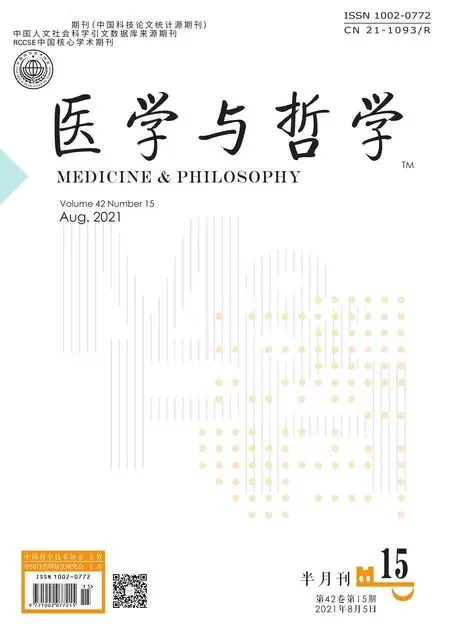道器之間:阿威羅伊醫學思想探析
白若萌
伊本·魯世德(Ibn Rushed),拉丁文名為阿威羅伊(Averroes),1126年出生于穆瓦希德王朝科爾多瓦一個書香世家,祖父和父親都是法官,他自幼熏陶漸染接受了良好教育,研習了教義、教法、哲學、天文、地理、醫學等學問,成年后擔任塞維利亞和科爾多瓦的法官,后被哲學家、醫生伊本·圖菲利(Ibn Tufail,1100年~1185年)舉薦來到京城馬拉喀什,奉國王之命重新修訂、翻譯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并兼任宮廷的總御醫。由于他堅持亞里士多德主義和“雙重真理”說,主張宗教經典與理性結論并行不悖,被國內宗教學者斥為異端流放回鄉,晚年雖又被國王召回宮廷,但不久便于1198年去世。阿威羅伊在阿拉伯世界沒有產生太大影響,但其著作譯為拉丁文后在基督教世界激起了廣泛回應,引發了西歐持續四個世紀之久的“拉丁阿威羅伊主義”運動,直到16世紀仍影響著眾多學者,如托馬斯·阿奎納、邁蒙尼德、哥白尼、布魯諾、笛卡爾,是歐洲擺脫神學桎梏、引發文藝復興運動的重要思想根源[1]。由于他堅持邏輯理性的同時也主張經驗觀察和人體解剖,而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正是唯理論和經驗論的交融,所以阿拉伯世界又稱他為“科學王子”[2]。
除了對亞里士多德著作以及對柏拉圖《理想國》的譯介外,阿威羅伊至少還寫了60多部原著,包括28部哲學著作、20部醫學著作、8部法學著作、5部神學著作和4部語法著作[3]。醫學著作大致分三類:第一類是一般性的“通論”,即寫于1162年前后的《醫學通則》[4]1。13世紀50年代該書被譯為拉丁語和希伯來語。1482年該書在威尼斯出版,成為巴黎、帕多瓦地區很多大學的教材。第二類是一系列解釋性文章,解釋蓋倫和阿維森納的著作,包括《論元素》《論氣質》《論先天稟賦》《論發熱的原因》《論癥狀與疾病的原因》《論簡易醫學》,這些評論大多屬于“研究隨筆”的風格。阿維森納(Avicenna,980年~1037年)寫過一部名為《醫學詩》的著作,阿威羅伊對此書評價甚高,最后形成了《阿維森納醫學詩評論》一書,被譯為拉丁文后于15世紀80年代在威尼斯出版[5]。第三類包括十幾篇著作,均篇幅不長,主題多樣,包括談論毒藥和解毒藥物等,如底野伽(Theriac)。本文依據《醫學通則》(阿拉伯文版本)以及有關研究成果探討阿威羅伊的醫學貢獻。在醫學哲學方面,在本體論上遵循傳統的元素、體液及平衡觀,試圖調和亞里士多德生物學和蓋倫醫學的沖突;在知識論上堅持醫學的自然哲學性質,在理論與醫療實踐關系問題上,認為理論與實踐處于平等地位,從而給予醫療以獨立性。對臨床醫學的貢獻集中在神經科學,確定了視網膜是感知光線的部位,重新解釋了腦卒中,明確描述了帕金森病的癥狀和體征。
1 理論哲學:本體論與知識論
1.1 醫學本體論:元素、體液與平衡
阿威羅伊最認可他的好友、外科醫生伊本·祖爾(Ibn Alhazen,?~1162年)以及波斯醫學家拉齊(Rhazes,864年~924年),還有伊本·瓦菲德(Ibn Wafid,998年~1074年)及其著作《藥典》、侯奈因·伊斯哈格(Hunayn Ishaq,808年~877年)、伊本·里德萬(Ibn Ridwan,968年~1061年)、扎赫拉維(Zahrawi,936年~1013年)等很多學者,這些學者大部分生活在伊比利亞地區,而較少提及阿拉伯東部的醫學家,因而總體來看阿威羅伊屬于安達盧西亞醫學傳統。《醫學通則》由導言以及六部分組成,分別是關于解剖、關于健康、關于疾病、關于疲勞的診斷和治療、關于食物和藥物、關于健康的規則[4]2。《醫學通則》幾乎每隔幾頁就要提到蓋倫,可見蓋倫是阿威羅伊的對話者。
阿威羅伊堅持自然哲學原則,認為土、水、風、火四元素組成宇宙,這些元素具有寒、濕、燥、熱四種原始性質,人體形態來源于四種元素混合的不同比例,進而形成了溫暖、寒冷、潮濕和干燥的不同氣質。四元素分別對應四體液,火元素對應黃膽汁、土元素對應黑膽汁,水元素對應黏液質,風元素對應血液質,健康在于四種體液的平衡和適當比例,如果失去平衡會導致疾病。因而,從疾病和健康的性質來看,醫生的任務就是在健康的人身上保持平衡,在生病的人身上恢復平衡。醫生與疾病的反面作斗爭,藥物使用的原則是“用冷治熱,用熱治冷,用干治濕,用濕治干”。平衡原則也表現為營養、睡眠、洗澡、鍛煉等保健方法。睡眠是“感官的平衡”,沒有睡眠,感官就會因過度運動而消亡;食物恢復身體失去的水分和溫暖,阿威羅伊推薦的食物有母雞、山羊、寒冷河流中的魚、無花果、蘋果、菠菜、牛奶等;洗澡有助于體液“流動”;運動有益于“增強內在精神,消除多余營養、廢物,直到開始出汗,呼吸增加,身體變紅,血管腫脹,到了那個階段應該坐下來”[6]162。阿威羅伊并不認為這些觀點是獨創,而是將元素、體液和平衡思想歸于希波克拉底、蓋倫和阿維森納。
1.2 醫學知識論:理論醫學和自然哲學的不同層次
《醫學通則》的第一部分,對醫學的性質做了界定:“醫學是一種從真正原則出發的技藝,以自然哲學為原則,有操作的性質。”[4]6該書序言部分的一個標題就是“醫學的自然哲學基礎”[4]7。在作者看來,既然人的身體屬于宇宙自然的一部分,那就必然符合自然規律,理論醫學與自然哲學是統一的。《醫學通則》中經常出現對蓋倫的批評,尤其當蓋倫反對亞里士多德時這些批評隨即就會出現。阿威羅伊[4]65一方面認為蓋倫是技藝高超的醫生,但因蓋倫并不完全贊同自然哲學,諸如在神經起源、是否存在“女性種子”以及感覺起源等問題上與亞里士多德不一致,于是批評蓋倫。類似的,阿威羅伊對托勒密的理論也持相同的立場,不接受托勒密與亞里士多德物理學不符的部分[7]。
可理論畢竟無法涵蓋一切具體疾病,醫學究竟要以自然哲學為依據,還是僅從經驗中汲取知識?醫療實踐與整合宇宙的哲學模型之間誰更優先?事實上,這一問題就是自古典時代被反復爭論的哲學與醫學的關系問題,是自希波克拉底,直至蓋倫、亞歷山大學派、阿拉伯學者以及歐洲經院學者都無法回避的元問題。蓋倫在《最好的醫生同時也是一位哲學家》一書中說:“哲學對于醫生來說,無論是初步學習還是之后的訓練都是必要的,真正的醫生都必須是哲學家。”這一論斷開啟了后世長達千年之久的爭辯。羅馬帝國后期的亞歷山大學派,其最大特色便是統合醫學與哲學,試圖將蓋倫與亞里士多德融合為一。該學派的學者自稱為“Iatrosophist”,即“醫哲學家”,是“既能提供治療又能掌握修辭和辯證法”的學者[8]。亞里士多德和蓋倫在很多問題上的說法明顯矛盾,典型例子是靈魂及其功能,亞里士多德認為心臟是靈魂的居所,蓋倫通過解剖注意到大腦神經損傷導致癱瘓,因此蓋倫回歸到柏拉圖的三重靈魂觀,“靈魂在心臟、大腦和肝臟之中”[9]。面對這些清醒,6世紀醫哲學家斯特法哈努斯(Stephanus)和阿格奈盧斯(Agnellus)在論及蓋倫的解剖成果和亞里士多德生物學時就避免直接面對這種矛盾,而是盡量在這二者之間尋求妥協,將二者協調統一[10]730。也難怪,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侯奈因·伊斯哈格的老師伊本·馬蘇維(Ibn Masawayh,777年~857年)說:“當蓋倫和亞里士多德就某件事達成一致時,這是真的;當他們意見不一致時,就很難確定事實真相。”[11]
10世紀之后,哲學和醫療實踐之間的矛盾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愈演愈烈,調和折中或避而不談的態度越來越難以立足,學者們致力于尋找一個總體解決方案或一個總原則來調和兩個學科之間的沖突。這一時期,對這一問題的“權威解答”主要是法拉比和阿維森納。法拉比(Farabi,870年~950年)把醫療技藝與農作物種植、烹飪并列為實用技藝,認為對癥狀、藥物、衛生和診療的研究才是醫學,其余(尤其是生理學)屬于自然哲學,法拉比對醫生在哲學上耗費巨大精力并自以為是的做法非常反對[12]。阿維森納在《醫典》中認為,“醫學只關注健康或生病的人體,而不是自然哲學,醫生不需要遵循能引導他從分歧走向真理的論證,不需要對現象的起因感興趣,也不該去尋找自然機制的原理,他只需對治療疾病的藥物感興趣”,美國醫學史學者麥克沃夫(Michael R.McVaugh)[13]將阿維森納的這種取向稱為“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醫學是處理現象的工具,而非獲得真理的手段,醫生的工作局限于恢復健康,而不去追問“事物的本質”。阿威羅伊明顯受到法拉比和阿維森納的影響,同樣帶有工具主義傾向,其貢獻在于將基礎醫學理論(及其依據的自然哲學)和醫療實踐活動明確置于一種平等的關系上。
2 醫學理論與醫療實踐:道與器的二元向度
阿威羅伊對醫學的性質做了界定,一方面堅持將自然哲學作為理論基礎,認識人體的形態是基礎醫學和自然哲學的任務;另一方面醫療有實踐操作性,“這兩個學科具有相同對象,即人的身體及其狀態,然而它們的依據和方法不同,醫學通過具體案例的經驗來達到目的……醫生不希望達到真正的知識,醫學保持著自己的地位”[6]168。在《對柏拉圖理想國的評論》一書中,通過對比醫學和政治學進一步闡明了觀點:“一般來說,(學科)分為理論和實踐,理論學科和實用學科之間存在明顯區別,它們(實用學科)取決于我們的意愿,而不是一個更高原則,目標是行動而不是理論知識,這意味著,規律越普遍,離行動越遠……(政治)就像醫學一樣,醫學一部分是理論的,一部分是實踐的。理論和實踐的區分不僅是慣例,還是醫學這門學問的本質。”阿威羅伊[14]援引《形而上學》加以佐證:“正因如此,亞里士多德將學問分為理論知識(theoria)、實踐知識(praxis)、創制知識(poiesis)……治療相對于理性醫學,實際上是兩門完全不同的學問,在這門技藝中,經驗必不可少,醫學不可能在所有的情況下都能達到真理。”例如,阿威羅伊談到疾病反復發作時,認為根據自然哲學,其原因來自天體和月球的運動,但這只是“遙遠的原因”,不需要考慮,醫生須關注具體病例和藥理,醫生類似為農夫、法官[6]170。
我們知道,亞里士多德認為形而上學是理論哲學的最高形式、第一哲學,但實踐哲學又可以支配理論哲學,因為“善”對人的生活有重大影響,把握了最高的善就可以支配其他知識,當然也包括理論知識,從這個意義上實踐哲學似乎更為根本,在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的關系上亞里士多德并未明確表示孰先孰后,因而阿威羅伊也同樣持這一觀點,認為醫學和倫理學、政治學一樣,都是為了增進人類福祉。中國先秦經典《周易·系辭上》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中國哲學的諸范疇“天、道、理”等,就其形式而言屬于形而上的存在;形而下指的是倫理行為,具有顯著的實踐性特點,當然,傳統中國文化中形而上的形式歷來都被賦予了倫理道德的具體含義,從這個意義上看,道,即醫學理論及其依據的自然哲學和形而上學根基;器,即實踐行為,帶有創制性和倫理性,“理論醫學”發現人體形態及其哲學依據,“臨床醫學”探索疾病治療,二者處于平等的地位。
阿威羅伊對醫學的態度,類似于近代“笛卡爾與培根之爭”,已接觸到了唯理論與經驗論之辨的核心。筆者認為,如果說阿維森納醫學思想沖擊了天主教壟斷下的禁錮思想、壓制理性的社會氛圍[15],那么,拉丁阿威羅伊主義“雙重真理”說,不僅對歐洲理性復蘇產生了推動作用,醫學理論和醫療實踐“平分秋色”的做法加重了哲學和實驗科學的分裂對立,而且使科學獲得了一定獨立性,因而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阿威羅伊的醫學哲學思想導致了醫學哲學的衰落”。正是由于這種二分,致使中世紀晚期醫學的哲學層面的知識逐漸被忽視,在意大利一些大學里遭冷落,15世紀后半葉帕多瓦的醫師們放棄了理論爭執,醫學理論成為低年級學生的一門基礎課,誠如深受阿威羅伊影響的巴黎大學的醫師們宣稱的那樣,“醫學開始于哲學的終點”[10]740。在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的歷史轉變過程中,阿威羅伊理性與經驗并重的思想一度沖擊了神學這一封閉陣地,在信仰氛圍濃郁的中世紀難能可貴。文藝復興時期有一幅名畫,即拉斐爾創作的裝飾梵蒂岡宮殿的《雅典學院》,該畫描繪了58位思想家跨越時空的虛擬集會,畫作左下方頭戴白巾、身著綠袍的便是阿威羅伊,該畫含義明確,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是通過阿威羅伊才被西方理解和接受的,拉斐爾對這位在西方智識發展中起了關鍵作用的穆斯林學者表達了敬意。
3 對神經科學的貢獻:視網膜、腦卒中與帕金森
《醫學通則》描述了人體的形態構造,包括骨骼、肌肉、器官、胚胎、病理生理、食品藥品、發熱、免疫等,雖然目前的文獻沒有表明阿威羅伊直接進行過人體解剖,但他支持解剖工作,強調解剖的重要性,“解剖并不違背信仰,而是加強了信仰,可以認識到人體是造物主的杰作”[16]。阿威羅伊對臨床醫學的貢獻集中在神經科學方面[17]。
3.1 視網膜與晶狀體的不同功能
美國科學史家林德伯格(Lindberg)[18]認為,雖然阿拉伯物理學家、眼科學家伊本·爾薩(Ibn Isa,940年~1010年)提出視網膜對感知光線的重要性,但阿威羅伊第一次提出視網膜而不是晶狀體才是感知光線的器官。亞里士多德反對當時古希臘流行的“外射說”(即視覺的形成是眼睛發射某種物質),認為視覺和其他類型感覺一樣,是外物通過介質傳遞到眼睛而形成。蓋倫和亞歷山大學派進行了眼部解剖,描述了視網膜、角膜、虹膜、淚腺和眼瞼,以及玻璃體和體液兩種液體,但蓋倫最終認為視覺是“外射”與“射入”的結合,晶狀體是形成視覺的器官。受蓋倫影響,中世紀早期包括金迪在內的阿拉伯學者堅持“外射說”。后來,拉齊發現了瞳孔的收縮和擴張;“現代光學之父”伊本·哈希姆(Ibn Alhaytham,965年~1040年)在《光學》一書中指出,眼睛會被強光傷害,兩位學者都發現光線會影響眼睛。阿威羅伊對亞里士多德《自然諸短篇》《論感覺及其對象》做了譯介,最后形成了EpitomeofParvaNaturalia一書,在承認蓋倫解剖學的同時,明確認為視覺形成是“射入”,是在沒有任何眼睛放射物的情況下完成的。此外,他也抓住了晶狀體液和玻璃體液都是光學介質這一事實[4]22。這導致16世紀意大利醫學家對感知光線的部位是晶狀體還是視網膜展開了激烈爭論[19]。蘇黎世大學醫學史學者柯爾賓(Koelbing)[20]認為,帕多瓦學派的維薩里(Vesalius,1514年~1564年)在其《人體結構》一書中,對眼部結構的觀察和認識,明顯受到了阿威羅伊的影響。
3.2 腦卒中及其起因
在西方和阿拉伯醫學史中,醫師們對于腦卒中(中風)非常熟悉,拉齊、哈里·阿巴斯(Haly Abbas,949年~982年)、阿維森納、邁蒙尼德以及拜占庭的醫師們對腦卒中做了詳細的臨床描述,但總的來看,這些研究沿襲著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的解釋傳統,觀察到中風病人呼吸尚存、心臟跳動,因而認為病變部位在大腦,對卒中的定義和治療并不新穎。與此同時,亞里士多德的心源學說(即“心主神志”)影響也很大,阿巴斯綜合了亞里士多德心源說與希波克拉底的腦源說,把血管和血液引入卒中的病理生理。阿威羅伊站在亞里士多德立場上進一步反駁蓋倫,由于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靈魂含有植物、動物和理性三重功能,腦卒中(癱瘓)臨床表現為“理性靈魂的喪失”和“動物靈魂(呼吸)”的存在,由于運動(特別是呼吸)是由兩個器官控制的,心臟和大腦,如果動物靈魂從腦到心的傳輸完全中斷,那么受動物靈魂控制的呼吸在癱瘓病人身上如何存在?然而,心臟病變會很快喪失生命,而中風病人的心臟依然跳動,于是阿威羅伊[4]95認為動脈是關鍵部位,“從心到腦的精神路徑被阻塞而發生,這些路徑就是動脈”,這可能是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指出動脈堵塞造成卒中。此外,阿威羅伊對大腦病變的說法也表示接受,“(卒中)起源于這兩個部位,動脈和腦室”,于是這就把蓋倫的大腦說與亞里士多德的心臟說聯系了起來[21]。古希臘醫師迪奧克利茲(Diocles,公元前375年~公元前295年)是亞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的學生,他經過解剖后認為卒中是因心臟血液流向肢體受阻而出現;哈維在1628年經實驗后提出血液循環說,雖然阿威羅伊支持解剖和觀察,但他關于腦卒中的結論究竟是基于實驗解剖得出的,抑或經過邏輯推理,目前所見資料無法確證,但基于他的哲學傾向,其結論極有可能是基于解剖加推理而得出,即在觀察現象的基礎上,經排除法而得出“心腦二重說”。
3.3 帕金森病及其臨床表現
阿威羅伊另一項貢獻是提出帕金森病并描述了該病的臨床癥狀。在這之前包括蓋倫并沒有明確描述這種疾病及其癥狀,盡管沒有給這種病取名,阿威羅伊認為這種疾病的癥狀是震顫,特別是在四肢和由隨意肌控制運動的器官中。這是一個復雜的運動,它的震動級別因位置不同而不同,通常是由高級指揮中心產生的反作用力(伸展和彎曲),在努力克服彼此的過程中,震顫發生了;另一種情形是一個指揮中心可能會抗拒自我移動而發生震顫,無論哪種情形,該病的治療很不容易。阿威羅伊認為這種疾病是由于神經系統受損而發生,神經系統受損可能是由寒冷或潮濕的物質所引起[22]。除了上述發現,阿威羅伊還探索了性功能障礙問題,是第一個開出口服藥物治療這些問題的醫生之一,還進行了局部或經由尿道的方式治療[23]。通常認為,阿威羅伊醫生的名聲被哲學家的名聲所掩蓋,其醫學成就與阿維森納相比名氣不大,但事實上,阿威羅伊在近代歐洲的聲譽在阿維森納和法拉比之上[24]。1405年,博洛尼亞大學在分配給學生的閱讀書目中包括《醫學通則》,該書成為15世紀后期和16世紀醫學院重要的教科書。德國內科醫生、人文歷史學家舍德爾(Hartmann Schedel,1440年~1514年)在其《紐倫堡編年史》一書中稱阿威羅伊為高超的醫生和智慧的奉獻者;英格蘭作家喬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序言部分提到四位阿拉伯醫生,即伊本·爾薩、阿維森納、拉齊和阿威羅伊,由此可見一斑。
4 結語
阿拉伯醫學在繼承古希臘醫學傳統的同時,也有獨特的創新之處[25]。阿威羅伊的貢獻在于明晰了理論醫學與醫療實踐之間的界限,破除了對傳統醫學和蓋倫的迷信。若以中華傳統文化類比之,形而上者為“道”,形而下者為“器”,形而上學是天地萬物運動變化的永恒規則和依據,而帶有主觀目的的技術是改造現實的手段,阿威羅伊將“道器二分”,給予了“器”以平等獨立的地位,無怪乎西方稱他為“二元論者,帶有濃郁的唯物主義傾向”[26]。阿威羅伊的醫學思想令人直觀感受到西方文明、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差異:學以致知的西方文明執著于形而上的上帝本體和邏輯本體,對塵世生活充滿超越和否定;而實用性極強的中華文明則對六合之外的“天、道”存而不論,采取“其高極乎太極無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的態度;伊斯蘭文明往往介乎于兩者之間,《古蘭經》在構建后世美妙天國的同時,并不否認具象的現世幸福,要求人們重視今生,帶有“兩世兼重”的濃郁色彩。總之,不同醫學范式其背后,往往有著深刻的文明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