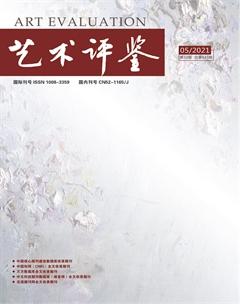宿命堅守,浪漫銀河
符祎明
摘要:作為經歷過香港電影黃金時代、見證過香港電影新浪潮發展與落幕的電影人,杜琪峰絕對是位逆流者。香港回歸前夕,由他領銜成立“銀河映像”,以電影作者冷靜而深刻的自省,堅持原創品格和作者態度、商業與表達雙拳出擊的運營方式,幾乎每年都推出了香港電影的話題之作。經過25年的淬煉,杜琪峰及銀河映像已成為香港地區乃至華語電影世界里兼具市場吸引力和口碑效應的招牌旗幟,作為香港電影的瑰麗奇葩,“銀河映像”及其作品對當今身處巨變商業環境中的電影人也有著特別的借鑒作用。
關鍵詞:杜琪峰 ?銀河映像 ?香港電影 ?黑色風格
中圖分類號:J905
回望香港電影史,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恰逢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杜琪峰與韋家輝、游乃海等人成立“銀河映像”,九七后,香港電影的商業與創作重新布局,資本退潮,影人出走,杜琪峰卻逆流而上,帶領團隊成員以原創性和本土性賦予“銀河映像”品牌特色,以商業和作者電影齊驅發展成就創作模式,一邊以黑色風格鋪就作者電影的創作底色,一邊以癲狂、溫馨、浪漫的商業格調營造都市愛情喜劇世界,以穩定的量產和高水準雙標輸出,成為續寫香港電影傳奇的旗手,書寫著香港電影另一番別具鄉愁之意的時代影像。也正因為由杜氏一手注入的風格色彩和主題追求,銀河映像已成為我們研究杜氏及其作品最好的標本,研究杜氏和銀河映像的一系列作品,亦能幫助我們看到香港創作者們對于當下創作的堅守。
一、逆流而上——回歸商業為創作尋得自由
杜琪峰自1979年拍攝個人首部電影《碧水寒山奪命金》后,恰逢80年代初香港電影迎來新浪潮時期。與同時期“新浪潮”的大多數導演們相同的是,杜與他們都具有電視臺工作背景,不同的是,當他人選擇進入電影界火速成為電影導演時,杜卻逆潮流選擇回歸電視臺繼續甘作幕后編導埋頭工作,這不僅是他為自己出于現實考慮的生計之道,更是為自己選擇的自由創作之路,“電視臺時期”讓他得以有更多的自由去徹悟個人風格。
當九七來臨,香港電影進入不景氣時期,許多香港影人紛紛出走,杜琪峰卻堅守本土,帶眾人成立“銀河映像”,之后迅速飛騰成長。
從現在回望過去,1996—2006年是香港電影不景氣的十年,但“銀河映像”卻在成立后的這十年期間,以商業電影和作者電影雙拳出擊,幾乎每年都能貢獻出香港電影的話題之作,且至今仍保持產量和水準的雙標輸出。這份漂亮的成績單,幸得杜琪峰所秉持的“銀河映像”理念,彼時的香港,市場跟風現象嚴重,電影的同質化、傳統類型片的套路化儼然成風,杜琪峰卻能保持清醒的認識,“他們在類型的固有因素之中努力創新,無論是在角色塑造、題材意蘊以及美學風格上都獨樹一幟。甚至可以說,銀河映像的成功正是因為他們不走傳統類型片的固有套路”。
可以說,杜琪峰對商業的正視和回歸,帶領團隊堅持作者電影與商業電影的齊驅發展模式,在商業類型片中以原創性和作者性來實現表達,并反哺促進商業電影的創新,也為他們尋找到難得的創作自由,才得以成就如今的“銀河映像”。
二、“文”“武”兼備——成就“銀河映像”商業與創作模式
20世紀80至90年代,杜琪峰導演了《八星報喜》(1988年)《吉星拱照》(1990年)等多部賣座電影,接受并經歷商業電影的洗禮,為杜琪峰提供了能夠安心進行個人創作的著陸地。
此后,杜琪峰及“銀河映像”的創作路徑依然清晰,既能拍《孤男寡女》也能拍《槍火》,能拍《瘦身男女》也能拍《PTU》,當拍攝商業電影讓投資方賺錢到滿意后,作為回報,投資方會投資杜琪峰拍攝真正想表達的作者電影,如此操作,“銀河映像”的商業模式得以成功建立。
“銀河映像”的商業電影和作者電影雖然在制片操作模式上被完全兩分,但杜氏并不止步于將兩者彼此割裂,而是有意促進兩者相互影響與各自發展。杜琪峰帶領“銀河映像”的創作者對作者性的堅守,并對兼具原創性和主題性的文本、形式進行不休不止的嘗試和探索,也由此得以讓杜氏及銀河映像的作者電影和商業電影在各自的形式和外延上持續創新,產生反哺商業電影內涵的可能,如同《大塊頭有大智慧》,在商業基礎上成功加入圍繞“因果”這一主題性的內容,對大支佬這個出世與入世,在因果間得到頓悟的獨特人物的塑造路徑得以建立。
談及杜氏在商業與作者表達兩者間的融合,可以從“神探”系列作品中做深刻體悟,從早在1995年杜琪峰為邵氏影業公司拍攝《無味神探》開始,至2008年銀河映像時期的《神探》,“神探”系列已經不斷演變,經過融入“銀河映像”都市男女愛情喜劇元素后,在2013年混搭“神探”與“男女”,“黑色”與“喜劇”,迭變而出涵納多類型元素的《盲探》。“‘銀河映像諸多成功作品的風格元素都在里面可以追尋到蹤跡,拼貼雜糅,使它成為‘銀河風格的集大成者”。
三、黑為底色,暗夜生輝——黑色寫意完成浪漫表達
得益于電視臺時期拍攝大量的金庸古裝電視劇,杜琪峰深受金庸作品的影響,也使得他“已經把古裝世界拍到了現在的電影里面”,致使杜氏作品中的人物具有魔幻色彩和浪漫色彩。得益于黑澤明、胡金銓、“新浪潮之父”梅爾維爾等導演和其作品的影響,杜氏形成區別于吳宇森式含有高度識別符號化元素的暴力美學,選擇將瞬間的暴力化為一剎那的燦爛、光輝,賦予暴力以可供描寫的美感,經個人化處理,表現為更為寫意和浪漫的風格。而如此的寫意浪漫創作風格,皆是杜氏放置于黑色風格之上,完成對宿命主題的表達,并由此鋪就而成“銀河映像”的風格基調。
在此不得不談及杜氏對“銀河映像”的影響,銀河創作團隊從極具實驗意義的《一個字頭的誕生》(韋家輝導演,韋家輝、司徒錦源、鄒凱光編劇)開始,不僅在敘事結構上進行極度風格化的嘗試,更在視覺風格上拉開踐行黑色風格的序幕,之后的《兩個只能活一個》(游達志導演,韋家輝編劇),《暗花》(游達志導演,司徒錦源、游乃海編劇),包括杜琪峰親自操刀的《暗戰》《槍火》《PTU》《黑社會》系列等,皆是杜氏和“銀河映像”團隊在其確立的黑色風格基調之上完成對人物和情節的敘事創新。正因為此,銀河映像才創作出旗幟鮮明的風格序列作品,確立了自身的品牌風格特征,為杜氏和銀河映像確立了成功的市場定位,贏得一眾專業人士和觀眾的忠實擁躉。
仔細品味杜氏和“銀河映像”的作品,便能發現杜氏常著眼于人物與人物之間的疏離感以及不確定的命運,以極具夸張和富有造型意義的畫面設計附著于人物表現之上,在光線結構的設計上常將主體放置在照度較高的高光照明區域內,由布光在視覺上形成舞臺造型空間,襯托造型空間內的主體完成主體造型,并常能創造性的利用現場的光源實現大光比的造型用光,成為杜氏和“銀河映像”影像風格的顯著視覺特點。以靜待動的場面調度、穩健的景深鏡頭和富有節奏感的長焦鏡頭調度完成鏡頭運動,形成營造一切視聽節奏感的基礎,加之前文分析中提到的風格化布光所營造的造型空間,與富有韻律感的人物動作和人物位置關系形成影片的空間感,配以音樂共同構建起電影的整體視聽節奏。以《槍火》為例,片中有近1/3片長的音樂,在配以音樂化處理的槍聲音效下絲毫不顯冗余和令人疲倦,與高度風格化的畫面造型、鏡頭運動和剪輯匯集成杜琪峰式的視聽交響。
也不得不說,這些堪稱癲狂般的天才式構想能得以實現,注定與“銀河映像”上下一心苦尋和堅持自我表達的理念脫離不開,《大事件》開片近乎8分鐘的長鏡頭曾讓《指環王》的攝影指導望而卻步,但最終沒能難倒銀河兄弟們自食其力,完美實現。也正因為他們日日夜夜齊心協力,杜氏和“銀河映像”的長鏡頭才所向披靡,《三人行》中近10分鐘一鏡到底的槍戰場面完全爐火純青。
四、黑色宿命,癲狂執念——執著追尋探索風格化主題
就像“黑色”永遠是杜琪峰所追求的風格,宿命則是他永恒的主題,兩者一道構成杜氏和“銀河映像”作品的風格品牌。從《一個字頭的誕生》和《兩個只能活一個》開始,不僅拉開了杜氏和“銀河映像”的風格序幕,也開啟了對于黑色宿命的追尋。
這種氣息在由杜琪峰奠定的“銀河映像”風格基調的警匪世界里更加突出,有時甚至是殘酷。不管是《非常突然》中緝拿完悍匪卻被草莽流寇團滅的一眾警員,還是《暗花》中如棋子般的宿命和徒勞,亦或是如大衛·波德萊爾所說“完全出人意料”的《PTU:機動部隊》,林雪飾演的肥沙倒地后丟槍開啟“蝴蝶效應”,最后卻在同一地點再度跌倒將槍拾回,終結劫匪,為整個暗夜畫上圓滿句號。
在杜琪峰的作品序列中,黑色宿命是其風格底色和執著主題。《無味神探》寫人生的悲苦,也是寫宿命的殘酷。《大塊頭有大智慧》中李鳳儀一心向善,卻難逃惡因之果,最終慘遭謀害,悲涼至極。《神探》的主角陳桂彬神經錯亂,能看透人性幽暗,在冥想中進入罪案現場,透查真相,卻逃不過孤苦生活,臆想著妻子活在身邊,最后死在辦案現場,才終得解脫。《盲探》的配角小敏一家,三代追愛卻個個凄慘。媽媽自殺,外婆瘋癲,小敏在路上苦苦追尋,卻不得真愛。
這種高度化的風格追求在被看作“銀河映像”成立20周年“獻禮片”的《樹大招風》中亦有沿襲,“三大賊王”或心狠手辣,或隱忍自恃,或驕橫跋扈,但皆各自為營,糾葛自身,傳聞四起卻渾然不知,最終難逃欲望和命運使然,想趁時事之風攀登“喜馬拉雅山”樣的人生巔峰,臨在歷史性的謀面前,卻各自以意想不到的終結方式落幕賊王的一生,不禁令人唏噓。
這種黑色宿命,縈繞于杜氏和“銀河映像”的敘事世界中,意外與死亡纏繞的宿命精巧又深邃,也使得宿命的主題被賦予隱喻內涵。
五、堅守本土,仰望星空——用“銀河”影像記錄時代映像
之所以稱為“銀河映像”,一方面是杜及團隊本著重視原創性作為品牌特色,另一方面則是他們一貫地將香港本土作為立足點,用影像記錄時代變化中的香港,抒發香港人對本土的切身感受。懷著對香港土生土長的情誼,杜氏帶領“銀河映像”以影像方式書寫著“香港家書”,故此,影片中的香港舊市容和古建筑也常與片中人物妥帖相融,營造出杜氏鄉愁的圖景。
這種“杜氏鄉愁”在創作《文雀》時分外典型,在停停拍拍的中途,杜琪峰用近兩年的時間找到“影院化”的影像風格樣式,并以“舊中有新,新中有舊”的方式,使得影片既具備西方人的視野,又具備香港的本土傳統,成為影片別具一格的特色所在。杜琪峰安排片中人物在香港的許多舊建筑、景點、街景中穿插出現,這些景點包括香港中上環的舊區:孫中山博物館、英皇書院、荷里活道的舊警署總部,中央書院和附近的街道,還有舊式茶餐廳、冰室等,在內景選取上以格調古舊又平民化的舊式唐樓為主,配以融合東方器樂音色的浪漫旋律,使得影片中的香港出落得陌生與冷艷,在這種距離感和陌生感之下,給予港式鄉土一種新的圖景展現。這不僅是用影像完成記錄,更是將影像的時空與建筑空間所包含的鄉土空間進行融合的一場實驗。
杜氏和“銀河映像”的堅守,并不止步于懷舊,而是重在新與舊的融合。而“舊中有新,新中有舊”的同樣還有對時代的直覺,港人在時代的風中如文雀般,雖“并不附著于這塊土地,而是隨時出入,或北上,或移民他國,過一陣子也會回歸,像飛鳥般自由飛翔,但會心系香港,這敢情是香港這城市的特色,香港有趣也正在此”。這也正同杜氏和“銀河映像”在處理香港本土創作和北上進軍大陸電影市場問題時的方式如出一轍。
在經歷《黑社會》系列電影與大陸審查制度博弈的過程后,杜琪峰在《放·逐》中以更為隨性的方式邊放逐邊重新尋回自我,并以滿足市場和審查需求先行的《蝴蝶飛》進行試水,后在《毒戰》中摸索出與大陸電影市場和審查制度相契合的合作方式。
不論是杜琪峰與其他六位新浪潮時代的導演向“膠片”致敬的短片集《七人樂隊》還是杜氏風格延續之作的《黑社會3》,亦或是片單計劃中的商業大制作《萬王之王》,皆是杜琪峰所帶領的由他與韋家輝、游乃海組成的“鐵三角”, 及鄭保瑞、羅永昌等其他“銀河映像”的同仁,連同朱淑儀、丁云山等幕后功臣們堅守本土,所看到的新一片星空。
六、結語
杜琪峰從20世紀70年代進入香港無線工作學習,經歷過80年代“香港電影新浪潮”,90年代在大都會(邵氏與無線合營)期間,與周星馳合作的《審死官》大破香港電影票房記錄,在1995年執導《無味神探》,迎來電影生涯中的重要轉折點,次年,即97回歸前夕,杜琪峰與韋家輝、游乃海等人成立“銀河映像”電影公司。悉數杜琪峰這一路,親歷了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羅曼蒂克消亡史,當看到其他影人或紛紛出走好萊塢,或紛紛選擇北上,徹底將重心移至大陸,而杜琪峰卻和“銀河映像”的伙伴們堅守本土,在商業電影與作者電影之間切換自如,順暢游走,既有警匪世界的黑色為底,亦有都市男女愛情歡喜的熠熠星光。
杜琪峰之于“銀河映像”,“銀河映像”之于香港電影,不正是宿命。說來宿命,皆盡殘酷,仰望星空,便是銀河。
參考文獻:
[1][美]大衛·波德萊爾.娛樂王國:香港電影的秘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210.
[2]王海洲.《盲探》:“銀河”經驗的粹聚之作[J].電影批評,2013(05).
[3]杜琪峰,吳晶.時代的影像者·影響者——杜琪峰導演訪談錄[J].當代電影,2007(02).
[4]杜琪峰,羅卡.不斷嘗試 積極求變 杜琪峰訪談[J].電影藝術,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