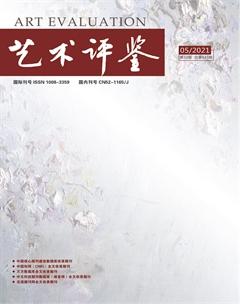淺析《推手》中的“咀嚼文化”
王怡婷
摘要:《推手》所塑造的細致入微而又一針見血的跌宕情節描繪出了中西方文化碰撞出的一場家庭悲劇。雖然這種悲劇由于“家丑”的遮羞布而往往隱形,上演在由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員組成的小家,卻也能拼湊出中西文化相遇時難以調和的窘境。這種互斥的文化特點在《推手》中,由于言語的完全阻礙、限定的時代背景、老人的情感依賴以及三番五次的事故設置,而變得相互拉鋸和不可調和,甚至沒有了周旋的余地。重重障礙中,李安巧妙地運用飯桌、食物這一咀嚼出的語言來展示中西方文化的雞同鴨講。
關鍵詞:《推手》 ?餐桌文化 ?中西文化差異
中圖分類號:J905
飯桌文化在中國語境里并不是個冷僻的字眼,西方的飲食形式與我們大相徑庭。《推手》多次巧妙地運用飯桌這一場景以及圍繞著飲食不可或缺的食物,表現沁入骨髓的飲食習慣如何留下了不可互通的語言烙印,再描摹了這種如同巴別塔寓言中的變亂語言又是如何扭曲相同的意圖,從而使得矛盾一觸即發。
一、中西方食物的初次登場以及背后的多重象征
電影的一開始常被提起有韻味——“此時無聲勝有聲”,朱師傅和馬莎生活的畫面如同剪切拼湊一般天差地別,又由于鏡頭的移轉而整合在同一空間。不得不說,李安導演特意選取了現今看來甚至有點刻板的元素,讓這種中西方文化的異質性在電影的一開場便急速走向了天平的兩端,讓這部電影的主題開門見山。太極的緩慢運轉配合著窗外節奏感極強的高強度長跑,室內爆炒飄香的中國菜和恒溫旋轉的烤箱面食展示著極其不和諧的生存狀態。就在這段毫無對話的日常生活慢鏡頭中,一聲巨響猝不及防地發生在午餐時段。
這聲巨響便發生在朱師傅用錫紙代替保鮮膜包裹著飯碗放入微波爐之時,中西方食物的第一次交鋒在這聲巨響中直接敘述出了潛伏在兩人之間的矛盾。看完整部電影之后,覺得開頭的午餐鏡頭頗有暗喻之意:朱師傅就好像這碗隔夜的大米一般,即使做出了讓步之后裹上了自認西洋的部分,也在這個西方家庭的小微波爐里難以生活;而馬莎沖向廚房對老人的怒聲解釋也成為了開篇第一句臺詞,讓人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中國公公和洋兒媳平素生活尷尬而又緊張的氣氛。
中西方食物與觀眾的初次見面便通過設計情節描繪了一個如此明顯的矛盾,然而除去馬莎啃著的干餅干和綠葉菜與朱師傅捧著的濃油赤醬面面相覷之外,中西方食物在同一餐桌上的同排陳列更帶來的是兩種迥異的飯桌文化之間的摩擦。依舊以影片開頭的沉默片段作為例子,這段鏡頭中花了好幾秒的時間去拍攝馬莎在用餐時看向朱師傅的眼神——其中的情緒似乎透露出她對于這個中國老頭享用美食時發出的忘我聲響而感到無可奈何;在之后的四人晚餐餐桌上,馬莎要求兒子喝完牛奶才能去看電視,朱師傅便覺得這西洋女人老是拿做買賣的方式和孩子做規矩……歸因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發生在飯桌上的那些看似無關痛癢的小問題實則根深蒂固,難以互通。可以想象類似的相斥觀念在老人和兒媳婦之間總會以千奇百怪的方式上演,而飯桌文化的摩擦是李安選取的一個絕佳角度,小而真,很鋒利。
故而可見,《推手》將中西方相差甚遠的觀念通過食物的多重象征去顯現,而實際上影片也不僅僅運用了以小見大的表現方式。多數影評認為洋媳婦馬莎在朱師傅搬出去住之后內心也發生了細微變化,她對自己的譴責通過她嘗試做起油炸春卷的那一幕具象起來。伴隨著那句“這都怪我”,春卷這一中國傳統食物又成為了影片中心人物內心活動的傳達介質,從而食物所象征的語言又反顧自身、含蓄地從細微處順應著故事的脈絡。
二、中式食物在《推手》中的大篇幅呈現和使用所蘊含的飯桌文化
在中西方食物差異所造成的語言變亂中,中餐元素的描繪更為細致和深刻。中式食物在影片中的多次出現從幾個維度展示了其在中國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它所代表的語言。
影片中幾乎所有中式食物都圍繞著朱師傅這位主角而展開,服務于他的每一筆刻畫。朱師傅主動使用食物這種語言的情況并不太多,比較明顯的一次出現在他和陳太初識的片段之中。這廂朱師傅好好教著太極拳,那邊陳太和大伙其樂融融地包著包子,朱師傅不得不故意制造契機加入包包子的隊列中,試圖和年齡相仿的中國老太搭搭話。
“不錯嘛,薄皮大餡,捏得又結實”。
“沒什么啦,北方人嘛,都喜歡做些面食”。
“你什么地方人啊”?
“北京來的”。
“來多久了”……
兩三句有關包子的對話,之后便說到了兩人自身的情況,一切并非純屬偶然,而是朱師傅本就精心設下的“局”:加入包包子隊列,就能開啟談話并且認識對方——朱師傅心里和明鏡似的。可見在傳統的中國文化觀念里,僅僅是參與制作食物就可以制造出交流與對話的契機,更不用提在享用美食的過程中為了保持熱乎的氛圍而源源不斷涌現的話題了。中國社會中的人情關系,尤以陌生人間的交際為代表,往往正是從約飯開始的——在中國人長久以往的認知里,發出去的請客邀約便是成功的一半。
很多時候,朱師傅使用這種語言是無意識的,那些依賴于飯桌的表達讓觀者瞥見了一個孤獨的中國老人一次次向外小心翼翼的試探。在朱師傅和洋兒媳的關系中,相較于馬莎向內收縮的自我封閉狀態,朱師傅其實更原意向外尋覓一種融洽的氛圍和關系。還是在影片開頭的兩人獨處橋段,馬莎在廚房享用午餐,而原本端著碗想坐在大飯桌吃飯的朱師傅短暫考慮以后,還是轉身坐在了馬莎對面,可以預想到馬莎或許會感到尷尬和煩躁,然而對于朱師傅而言,這是一種讓步,一種對于飯桌規矩的讓步。這個小細節所傳達的中國元素十分明顯,即中國人的飯桌文化本身不僅僅關乎食物,更關乎家庭成員間的交流,從而也逐漸形成了圍坐用餐的傳統規矩。悠久的合餐制歷史幫助中國家庭形成一種向心力,牢牢地圍坐在一起;同時使得分餐的行為一反常態——分餐和分床有著同理的意味,可以說分餐似乎是一種感情和關系分裂的象征。馬莎的想法很簡單,吃飯不過是關于食物的程式,而在朱師傅為代表的中國理念里,吃飯的意義被泛化了,和人吃飯變成了重點。
可也正如上文所言,這種試探是被拒絕的,從馬莎的眼神中就可以察覺。
中國人的飯桌文化內涵頗豐,除了上述的合餐制習俗,不分公私筷的習慣也使得為別人夾菜成為了一個尋常的舉動,而這一舉止所包含的關切卻是一分不少的。《推手》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家四口圍坐在飯桌前吃晚飯的場景尤其精彩,朱師傅的夾菜行為看似細微,卻又一次表現了他對于家人本該和和氣氣、相親相愛的理解。馬莎為丈夫盛了餡餅,朱師傅便向兒子盤里夾了一塊蹄膀,這正是通過食物表達親近與關心的典型范例。而后朱師傅忽然看向兒媳,夾起蹄膀用眼神詢問她——盡管朱師傅并未與兒媳婦有太多交流,卻始終接受她為家中的一份子。可以說通過夾菜這一飯桌上的微妙語言,影片對于中國飯桌風俗有著相當到位的掌握。
朱師傅的關心還是吃了閉門羹,而馬莎禮貌的拒絕也出于自身對于食物的理解——在西方實行的分餐制中很少見傳達關心意味的相互夾菜,同時紅燒蹄膀著實不符合她的口味,故而出現了拒絕,或許這種拒絕并不帶有抵觸老人的情緒,但由此可以見得,兩人間的試探屢遭對方的拒絕,晃蕩中的家庭矛盾一直存在且處于懸置之中,這也是《推手》中的主人公所展現出的痛苦和失衡無解的原因,歸根結底還是文化底色的兩相互斥。而通過這些細節所塑造出的朱師傅形象,向外探知卻遲遲得不到回應,最后他所選擇的搬離小家實則隱含著對于“家”理想瓦解的默許,這也是《推手》讓中國觀眾感同身受、不禁為這個老人落淚的一個原因。
三、圍繞飯桌展開的變亂語言引致的失衡關系
《推手》作為一部描寫中西方混合家庭的電影,自然并不存在電影視角上的“反派”之說,全片也不過是形形色色的普通人之間的故事,然而正是這些本質善良的角色由于使用的表達介質大相徑庭,而被扭曲了本意,造成了誤解和不解。李安確實選擇了言語不通這一極端的要素來阻礙人物之間的交流,但口頭語言也僅僅只是表達的一種形式,甚至在“朱師傅要求出門散步”等鏡頭中,是可以由肢體語言輔佐從而達到溝通之用的。故而相比起語言不通,更獨特的是《推手》利用一次次不同人物組合的用餐這一介質,通過展示飯桌上的語言如何變亂曲解人的原意,解釋同一家庭中人物關系的“通天塔”構筑為何如此困難。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場景便是那僅有一次的四人晚飯,作為朱曉生“在夾縫中求生”處境的首次暗示,這頓晚飯的餐桌和菜肴設置就花費了不少心思。西餐和中餐像楚河漢界一樣分列在同一大桌之上,馬莎和兒子使用刀叉、朱師傅操起筷子,朱曉生則兩副餐具都準備妥當。朱師傅和兒媳同時向朱曉生發出交流的信號,兩面“受敵”的朱曉生左右翻譯著,卻因為疲累和煩躁而無法翻譯周全。比如朱師傅對于吃肉的理解,實際上是以解釋的語氣在表達,然而其兒子并不能一模一樣地轉述給妻子,反而在妻子產生疑惑時糊弄了過去,導致妻子懷疑朱師傅是否是在抱怨。四人飯桌的語言就此遭到了變亂,在幾個回合后由于交流的阻礙而逐步變響的兩種語言最終引發了朱曉生的怒火。“Just eat!”他的一聲令下讓大家重回飯桌,然而剩下了什么呢?剩下的只有中西方成員都能感受到的尷尬與不快的氛圍,還有本就難得的交流戛然而止。
圍繞著飯桌的變亂,甚至可以落到食物這一簡單的要素上。馬莎是素食主義者,理解不了濃油赤醬的大葷對健康的增益;而朱師傅信奉著中國的飲食傳統,認為“只吃菜葉子”根本沒法養生。兩人向朱曉生夾菜,即使是相仿的動作、一樣的關切,卻因為對于食物本身帶有的偏見而難免讓兩人都不解和困惑——就吃這個,能行嗎?可以想象脫離飯桌的變亂會有更多的表現模式。電影中對于寶貝孫子杰米的施教,雙方不同理念的妥協結果居然是為杰米規劃出“中國時間”和“美國時間”,這種割裂式的教育著實讓人擔憂。可以說出發點相同,朱師傅和馬莎由于接受的文化不同而選擇了不同的表達方式和介質,從而引發的對立和沖突掩蓋了原本的善意,使兩人之間乃至整個家庭的氣氛都不時地沉重起來。透過飯桌上的無序交流和中西食物間傳達的錯誤信息,構筑良好關系的“通天塔”就此停止修建,家人間的關系經歷著沒有休止的失衡。
《推手》的實質是悲觀的,只有其中一方率先放下雙手才能結束推手動態的周旋,而影片中家庭矛盾的懸置則是通過朱師傅的放手得以解決。“搬離家庭”對于一個中國老人而言是一項挑戰,對于體格精壯的朱師傅而言更意味著最后的巨大讓步,甚至退離了他安身立命的傳統文化觀念。眾多觀點認為這是一場和解,以中國文化的包容和貫通結束了懸置的矛盾,自然地便隱去了主人公無奈又無言的個人情感,忽略了對于朱師傅而言這是一種家庭悲劇的實質。朱師傅個人的悲劇背后所映射出的依舊是中西方文化間的不斷“推手”以及兩者構筑的小家中被懸置的、層出不窮的大小矛盾。
四、結語
談及《推手》,勢必會談起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更為值得細品的或許是李安如何運用種種細節引導觀者發掘出家庭關系失衡的蛛絲馬跡。飯桌在電影中三番五次的出現,暗示著信息的傳達如何變異而最終失靈,導致這個家庭失去了人際交流的平衡。雖然《推手》一步一步安排著悲劇的上演,似乎強調著這便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必然結果,但在如今的信息化時代,在人類共同體不斷加速建構的進程中,隨著相互了解的遞進、文化代溝的不斷填補,即便是帶有習俗烙印和文化特征的餐桌語言也不再是難以跨越的鴻溝,把變亂的語言再次“統一”已經變得觸手可及。
參考文獻:
[1]張慧.《推手》的中西文化主題闡釋[J].電影文學,2017(07):125-127.
[2]譚淑林,李芳媛.從跨文化視角解讀李安“父親三部曲”中的中西家庭倫理觀——以《推手》為例[J].才智,2013(35):272+274.
[3]李娜.東西方文化的沖突與融合——解析李安電影《推手》和《喜宴》[J].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013(03):194-195.
[4]楊浩,韓貴東.李安家庭三部曲中傳統文化的失落與變奏[J].電影文學,2016(19):6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