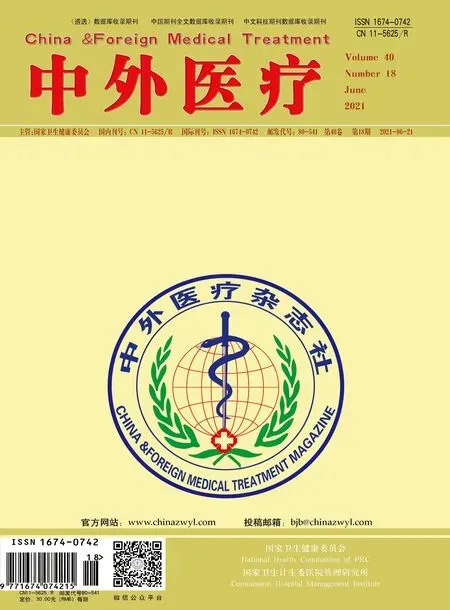探析植物乳桿菌胞外產物對非酒精性脂肪肝損傷保護作用的研究
徐燕,林星,王勝強
重慶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綜合科,重慶 400030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具有廣泛的作用,是世界上最常見的慢性肝病。 NAFLD是代謝綜合征的肝臟表現,在肥胖和糖尿病患者中非常常見,包含從簡單脂肪變性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纖維化和終末肝硬化的一系列肝臟病理變化。在10~20年的時間中,有2%~3%的NAFL患者和15%~20%的NASH患者會發展為肝硬化,到下一個十年末,NAFLD將會成為導致肝病、肝移植和肝癌的主要原因。盡管近年來對NAFLD的研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其發病機理仍知之甚少,治療選擇也受到限制.NAFLD治療的基礎是生活方式的改變,包括飲食和習慣的改變,運動的增加和體質量減輕。但是,很少有患者能夠達到其目標體質量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因此,開發用于NAFLD的有效療法是重要的臨床目標。
1 腸道微生物失調與肝疾病
腸道微生物包含多種微生物(主要是細菌),有助于消化,提取能量并拮抗病原體的定殖。腸道微生物是指正常的腸道菌群,可能是由多種環境,免疫或宿主因素,以及沙巴病毒,胃液pH值變化或腸蠕動障礙引起。在脂肪肝疾病中,從描述性人體實驗中獲得了腸道疾病和肝損害相結合的證據。14 CD-木糖和果糖呼氣試驗相結合,確定了小腸細菌與增加的小腸細菌之間的NASH聯系證據還表明,NAFLD患者的微生物數量發生了變化。在動物實驗中,微生物處理可提供強有力的證據,證明肥胖癥和NAFLD中腸道菌群受到調節。小鼠的肥胖癥和胰島素抵抗相比,兩種不同的飲食方法可引起小鼠體質量減輕,從而導致大量的微生物生態。添加抗生素后,胰島素抵抗(NAFLD的一個關鍵特征)得到改善[1]。細菌仍然很重要,另一項研究表明,無胚胎小鼠肝纖維化的嚴重性增加[2]。例如,向幼鼠注射低劑量抗生素會導致結腸微生物區系的不斷變化,從而導致更多的SCFA產生以及肝臟脂質和膽固醇的代謝[3]。很少有人對人類進行過類似的實驗。這些結果表明,腸道微生物的變化可用于提高人胰島素敏感性,這可用于治療脂肪肝[4]。為支持這些發現,微生物菌群的代謝物和作用(微生物代謝物)似乎根據宿主的代謝表型而不同。腸道微生物疾病可通過影響脂肪因子、抗炎劑、抗炎劑和脂肪酸的氧化而直接影響脂肪組織,然后對下游肝臟產生重要影響[5]。盡管有這些發現,但腸道細菌的總數和分布,不同群體的相對豐度,某些有害微生物的存在,微生物生長的代謝功能,宿主遺傳學或這些因素的組合在NAFLD中是否在發病機理中起著重要作用。另外,迄今為止很少受到關注的微生物群組分,例如真菌,可能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例如,念珠菌可以分解淀粉并釋放被諸如普雷沃特氏菌(Bacteroides)和瘤胃(Firmicutes)之類的細菌發酵的糖,這增加了腸道中食物的能量攝入,而腸道也是肝臟使用的能源[7]。
甘油磷脂途徑中的代謝產物膽堿、甘油磷酸膽堿、磷酸膽堿等明顯增加;添加植物乳桿菌胞外產物后,甘油磷脂代謝途徑中的重要中間代謝產物顯著減少,從而改善了膽堿代謝,對脂質有益。另外,磷脂的減少意味著肝脂質產生的減少,表明植物乳桿菌胞外產物FRT4和FRT10可以通過調節甘油磷脂代謝來調節肝脂質代謝。植物乳桿菌胞外產物治療組中的D-麥芽糖、麥芽三糖、蔗糖和麥芽五糖顯著減少,從而減少了脂質的產生[6]。 此外,嘌呤、嘧啶、氨基酸等也發生顯著變化,具體作用有待進一步研究,見圖1。

圖1 植物乳桿菌胞外產物的降脂機制
FRT4和FRT10均可顯著減少甘油磷脂代謝途徑中的膽堿和磷酸膽堿(P<0.05)。FRT4可以顯著降低甘油磷酸膽堿和sn-甘油-3-磷酸乙醇胺(P<0.05)。膽堿是維持肝功能的必需營養物質,是磷脂的重要組成部分,膽堿主要從小腸吸收,并在肝臟中完全代謝[7]。膽堿也是磷脂酰膽堿(PC)的重要前體,主要涂有極低密度脂蛋白顆粒的磷脂。膽堿在極低密度脂蛋白(VLDL)中也起著重要作用,VLDL是腸道中的宿主微生物,并與co相互作用,Ne NAFLD是其發病機理的潛在因素。膽堿代謝的主要靶標可能是肝臟,主要是磷脂酰膽堿(PC)。先前研究表明,膽堿攝入量與NAFLD風險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性。該結果與先前的研究不一致:在小鼠中,膽堿相關的代謝產物(例如膽堿,磷脂酰膽堿和3-磷酸甘油)減少。報告說,膽堿越多,肝脂肪變性,NASH和小葉炎癥的風險就越大。在該研究中,與CT組相比,結果顯示HFD導致膽堿代謝減少,這可能減少VLDL從肝細胞流出并促進炎癥。膽堿的生物利用度降低可能導致小鼠和人類的NAFLD和葡萄糖代謝的改變。 FRT4干預組的膽堿濃度明顯低于模型組 (P<0.05),植物乳桿菌胞外產物干預后觀察到的甘油磷酸膽堿明顯降低。過量膽堿、甘油磷酸膽堿、磷酸膽堿和CDP-膽堿也與脂肪積累呈正相關,與先前的研究一致。即肥胖小鼠中甘油磷脂代謝產物水平的增加與脂肪積累相關[8]。先前的研究還表明,血漿游離膽堿水平與肝脂肪變性和纖維化呈正相關。與其他飽和脂肪(如棕櫚酸酯和肉豆蔻酸)相比,硬脂酸是TG合成的非常弱的底物。用植物乳桿菌胞外產物治療后,單糖向肝臟的轉運增加,這促進了肝脂肪的產生和脂肪變性。肥胖引起的胰島素抵抗的增加與肥胖小鼠肝臟單糖和二糖水平的增加呈正相關。單糖可以直接激活肝SREBP-1和激活肝脂肪酶。 SREBP-1的活化進一步刺激脂肪酶和脂肪積累。在該項研究中,發現添加植物乳桿菌胞外產物后,在喂食HFD的小鼠中SREBP-1被下調。因此,推測植物乳桿菌胞外產物可通過調節肥胖小鼠肝臟中的甘油磷脂代謝和葡萄糖代謝來增強肝臟脂質的積累[9]。
2 植物乳桿菌胞外產物對非酒精性脂肪肝損傷保護作用
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通常會患有全身性慢性炎癥。高脂飲食引起的肥胖小鼠肝臟,肌肉和脂肪組織中各種炎癥因子的表達水平升高,例如白細胞介素6(IL-6),TNF-α 和白細胞介素1(IL-1)[10]和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CP-1)等,與胰島素抵抗的發生有關。腸道上皮是與腸道微生物相互作用的最大橫截面,而腸道自然免疫系統是與菌群與宿主之間相互作用相關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這種共生關系導致病原微生物的破壞,同時促進了對共生體的耐受性,從而創造了一種有益的生態位,并不斷與腸道微生物接觸。腸道菌群可以通過幾種機制引起慢性全身性炎癥。宿主共生細菌通過病原體相關的微生物模型(PAMP)與病原體相關,包括LPS、脂蛋白酸(LTK)[11],鞭毛蛋白,雙鏈或單鏈RNA和DNA以及上皮細胞。細胞特異性電荷受體(TLR)和胃腸道樹突狀細胞 (樹突狀細胞,DC)會影響免疫系統。 TLR是完整的膜模式識別受體家族,在先天免疫系統中起重要作用,并且在維持這種平衡方面非常重要。宿主通過3種方式識別細菌細胞:①通過與黏膜DC的TLR相互作用;細菌遷移后,與淋巴樣M細胞上皮DC相互作用而不會降解;連接到腸上皮細胞,呈現PAMPDC[12]。PAMP結合導致主要反應基因My D88與銜接子蛋白向TLR的髓樣分化相關。My D88蛋白的第二個域與白介素1受體相關的IRAK激酶 (IRK1和IRK4)相互作用。IRK4通過融合另一種銜接蛋白TNF受體相關因子TRAF6使IRK1磷酸化。TRAF6與增殖相關的蛋白激酶MAP2K,轉化生長因子TAK,TAK結合蛋白1或NF-κB誘導的激酶NIK相關。因此,IκB激酶(IKK)磷酸化NF-κBIKB抑制劑磷酸化并激活,釋放NF-κB,遷移到細胞核,并觸發各種細胞因子,趨化因子,粘附分子和急性期,蛋白質轉錄如IL-1β,IL-1β IL-8在大多數細胞中激活NF-κB并抑制細胞凋亡[13-14]。見圖2。

圖2 腸道微生物群、宿主先天免疫和代謝炎癥的作用機制
通過消化革蘭陰性細菌在腸道中不斷產生細菌LPS,它是與微生物相關的因子。它與CD14受體形成復合物,并由免疫細胞表面上的TLR4受體建立,以誘導TLR4誘導炎癥反應它可以觸發炎癥級聯反應,包括途徑)[15]。TNF-αB刺激TNF-αTNF-α[16]釋放引起脂質過氧化和肝細胞纖維化,從而促進脂肪肝進程,脂多糖可破壞腸道微絨毛。并破壞腸道抑制功能,引起腸道通透性增加,致病菌和LPS遷移,并進入肝門靜脈,然后肝細胞功能受損并促進脂質變性。植物乳桿菌胞可以改善腸道菌群失衡,降低致病菌的數量,提高腸道菌的防御能力,進而影響腸道上皮細胞。
綜上所述,植物乳桿菌NCU116是該研究的主題。通過建立調節腸道菌群、便秘、高脂血癥、結腸炎和糖尿病的動物模型,可以全面評估該細菌的體內活性及其潛在的益生菌特性。C1通過在小鼠中施用不同劑量的植物乳桿菌NCU116來評估益生菌對腸道微生態平衡的影響。植物乳桿菌NCU116能促進乳桿菌和雙歧桿菌的生長,抑制腸桿菌和腸球菌的生長,此外還能產生短鏈脂肪酸,降低血脂水平,抑制氧化應激,調節血清細胞因子有一定的作用。研究證實,植物細菌NCU116對腸道菌群的調節有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