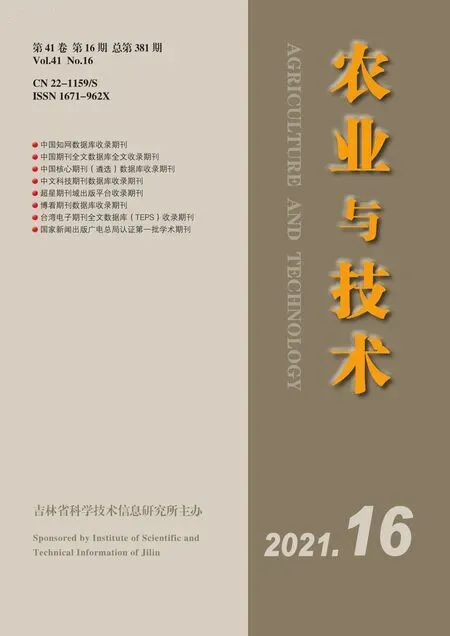陜西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增收效應研究
吉瑞 陳云橋
(延安大學,陜西 延安 716000)
近年來,在政府惠農支農扶農政策傾斜下,農民收入水平在不斷提升。2006—2019年,陜西省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年均14.06%的增速持續增長,相比同階段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高出2.9%。城鄉居民收入比從2006年的4.10下降到2019年的2.93,城鄉收入差距逐年在縮小,但是仍然比2019年全國的城鄉居民收入比高出0.29,并且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絕對差距從2006年的7008元增加到2019年的23772元,可見解決陜西省農民增收問題任務仍然艱巨。農民增收問題一直以來都是黨中央關注的重點,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上提出要推進農村產業融合發展,通過支持和鼓勵農民參與創業,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來增加農村居民收入,讓農村一二三產業之間的融合發展成為促進農業經濟增長、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因此要提升陜西省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深入探究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農村產業融合就是以農業產業為基礎,依托地方農村資源、獨特的生態環境優勢和旅游資源等,通過農業產業與二三產的聯動與重組,模糊產業邊界,拓展產業范圍,多維度延伸農業產業鏈,形成農業生態旅游、文化創意農業、“互聯網+農業”等農業新業態、新模式。目前在學術界對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增收效應的研究主要有2種不同的結論。部分學者認為,農村產業融合可以延長農業產業鏈條,增加農產品的價值,通過融合互聯網等先進科技元素解決農產品銷售問題,并且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解決農民就業難的問題,把農業的增值產業鏈和增值收益留在農村,實現增加農民的收入。還有部分學者則認為,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尚處于初期探索階段,在多數地區還未形成規模化的發展,融合模式同質化嚴重,容易出現惡性競爭的現象,可能并未實質性地實現農民增收。因此,目前陜西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程度,能否有效促進農民增收,還需針對陜西省實際情況進一步分析,在對陜西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測算的基礎上構建回歸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分析,探究農村產業融合的增收效應。
1 陜西省農村產業融合水平測算
1.1 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在現有測算農村產業融合度的相關實證研究中,目前還未形成官方的或者普遍認可的融合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和規定的測算方法,所以本研究根據陜西省的農村產業發展實際情況以及對相關研究的分析借鑒,構建出以下指標體系后,運用熵值法對陜西省2006—2019年的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進行綜合評測,具體見表1。

表1 陜西省農村產業融合的評價指標體系
1.2 數據來源
本文所構建體系中的各三級評價指標數據主要來源于《陜西省統計年鑒》和《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化肥施用強度、農村非農就業比例、城鄉居民消費支出比等指標數據以2006—2019年陜西省的統計數據為基礎數據,通過計算而得到。
1.3 農村產業融合度的測定與分析
本研究選用熵值法對陜西省的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進行測算,在計算出各三級指標的權重基礎上加權計算出陜西省2006—2019年每年的綜合評價指數。由于指標體系中選取的各三級指標單位不盡相同,數據之間也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進行綜合評價指數計算之前需要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具體的測算過程如下。
1.3.1 數據標準化處理
為消除各指標間的量綱影響和取向正負的影響,對各指標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標準化處理。
正指標公式:
負指標公式:
式中,Xij為第j項指標的第i個指標值的原始數據,Yij為指標值原始數據經過無量綱標準化處理后所得到的數據。
1.3.2 熵值、權重計算
計算出每個指標數據占該指標的比重,公式:
求出第j項指標的熵值Ej,公式:
計算出各指標權重Wj,公式:
1.3.3 計算綜合評價指數
運用線性加權求和法計算出陜西省2006—2019各年農村產業融合度的綜合評價值RID,計算結果見表3。公式:

表3 陜西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數
由計算結果可見,近14a陜西省的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整體水平上保持持續增長,融合程度逐年上升。也可以看到其中融合發展水平2006—2009年增長緩慢,從2010年開始增長速度提升,2016年融合發展水平相較無顯著明顯增長,2017年開始逐年加速增長。這些階段性的特征主要與陜西省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關政策的實施以及整體經濟環境有關。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中首次提出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陜西省開始實施各類型試點項目,可見從2017年開始成果顯著,融合發展水平大幅度提升。近年來,隨著黨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重視,支農扶農惠農傾斜政策的落實,農村大學生回鄉創業,農村基礎建設與服務體系越來越健全,為陜西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陜西省開始把產業融合發展作為推進農業現代化發展、拓展農業多功能發展的重要抓手,通過創建農村產業融合示范園,推行多元化的融合發展模式,順向延伸形成農業全產業鏈,逆向延伸建設高品質的農業原材料基地,拓展農業多功能產業集群發展。同時從測算出的綜合指數發現,當下陜西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還未大規模開展,尚處于初期探索階段,可以看出整體的融合水平還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間。
2 陜西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增收效應分析
2.1 變量選取
由于是分析陜西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增收效應,本文涉及到的變量主要為陜西省農民的收入水平以及陜西省的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此外,通過分析文獻可知,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還會受到農村金融發展效率RFE(農村貸款/農村存款)、農村固定資產投資水平RFA(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第一產業GDP)、地區經濟發展水平GDP、城鎮化水平URB(城鎮人口/總人口數)、基礎設施建設水平INF(農村公路里程/農村人口數)的影響。考慮到需要避免因為遺失相關解釋變量而造成內生性問題,以及因為忽略掉一些對被解釋變量產生影響的因素而出現異方差,因此要更準確更全面地分析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增收效應,需加入上述的變量進行逐步回歸,進一步分析兩者之間的關系。
被解釋變量為陜西省農民收入水平IN,用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來表示。解釋變量為陜西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RID,用由計算所得的2006—2019年陜西省每年的綜合評價指數來表示。
2.2 數據說明
本研究選取陜西省2006—2019年共14a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為降低異方差對分析研究的影響,對以上各變量取對數進行實證分析。所采用的數據來源于《陜西省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4。

表4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為更直觀地觀測陜西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與農民收入之間的關系,描繪了散點圖,具體見圖1。從圖1可以看出,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隨著農村產業融合水平的提升而增加。但兩者之間的關系是否如圖1所示,還需進一步通過計量模型進行檢驗分析。
2.3 模型構建
為驗證陜西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對農民收入的增收效應,構建以下實證模型:
lnNIt=β0+β1lnRIDt+β2lnRFEt+β3lnRFAt+β4lnGDPt+β5lnURBt+β6lnINFt+εt
2.4 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2.4.1 逐步回歸
對被解釋變量lnNI與解釋變量lnRID構建的模型M1進行回歸,然后逐步將其它解釋變量加入模型中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在每引入一個解釋變量后對模型進行F檢驗,檢驗整體模型的顯著性和對各解釋變量進行t檢驗,剔除掉影響模型顯著性的變量。在逐步回歸的過程中發現加入變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化水平、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后模型不顯著,因此將其剔除掉,所得到各模型的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從回歸結果可看出模型M1、M2、M3的R2均接近1,表示估計的回歸方程與樣本觀測值擬合的較好;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各模型的F統計值均遠大于臨界值,對應的P值均<0.05,因此通過F檢驗,表示在3個模型中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線性關系;根據模型中各解釋變量的t統計值可知,模型M1、M2、M3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解釋變量均對被解釋變量有顯著的影響;異方差檢驗采用懷特檢驗法,發現模型M1和M2存在異方差問題,用加權最小二乘法對模型進行修正處理解決異方差,最終修正后得到的結果見表5;由于此次實證分析選用的是14a的時間序列數據,所以用LM檢驗進行自相關檢驗,模型M1、M2、M3中卡方統計量Obs*R-squared對應的Prob值均>0.05,因此不存在自相關問題。

表5 回歸結果
2.4.2 回歸結果分析
根據模型M1的回歸結果,變量lnRID的系數為正可知,農村居民的收入隨著農村產業融合水平的提高而逐漸增加,農村產業融合水平每提高1%,陜西省農村居民收入將會增加0.6791%。在進行逐步回歸的過程中,剔除掉了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化水平和基礎設施建設水平3個變量,最終得到M2與M3的回歸結果。通過分析模型M2和M3的結果可以發現,在回歸分析中加入其它可能影響陜西省農民收入的因素情況下,農民收入也仍然隨著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漸增加。在模型M2中,加入變量農村金融發展效率,由回歸結果可知,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每提高1%,農村居民的收入會增加0.5832%;模型M3中,在加入了農村金融發展效率與農村固定資產投資水平的情況下,農村產業融合水平每提高1%,陜西省農村居民收入將提高0.4733%。
3 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在測算陜西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的基礎上,以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和測算所得的農村產業融合度綜合評價指數為基礎數據,逐步回歸實證分析了農村產業融合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研究發現,陜西省農村產業融合程度從2006年的0.0096到2019年的0.1756,提升了0.166,近十幾年融合程度在逐漸提升,并且通過實證檢驗得出,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可以有效提升農民收入水平。現階段陜西省農村產業融合還處在初期階段,存在不少需要改進的問題,如融合發展模式單一、面臨金融困境等。因此,為了加速農村產業融合發展進程、拓展融合發展范圍、深化融合發展程度,實現增加農村居民的收入,提出以下建議。
不同地區結合當地特色可以以設施農業、生態農業、旅游農業、智慧農業等為導向,充分發現利用當地的特色農村資源、旅游資源等,深度開發利用獨特的資源稟賦,發掘農業農村的新業態,如休閑觀光、康養服務、文化體驗等。在互聯網時代,農業的發展也要融合大數據、“互聯網+”等先進科技元素,拓展農村電商貿易、生態循環農業、認養農業等方面的服務,滲透融合好大數據、物聯網、地理學信息系統等先進要素來建設智慧鄉村。如,延安市的認養農業,依托延安市特色的蘋果產業,打造“互聯網+農業”模式,形成一種簡化農產品銷售過程的新型農業經營形式,提升農產品生產質量的同時解決銷路問題,保障農民收入。
政府因地制宜制定金融扶農政策,解決產業融合過程中對金融要素的需求。因為農業特殊的季節性、周期長、風險存在不可控性等特點,并且參與農村產業融合的專業大戶、農業合作社等經營主體還大多處在創業探索階段,回報率會偏低,金融機構傾向把貸款投入到有貸款擔保、風險小、投資回報率高的工業、服務業,融資難、慢、貴的問題是創業階段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普遍面臨的困境。因此,產業融合發展過程面臨的金融困境需要政府財政投入、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的共同發力,提供對口的金融支持。因此政府需要因地制宜且針對不同領域采取一些金融扶持政策,完善農村金融制度主要組成部分的農業產業化融資體系,如采取財政補貼抵款利息、政府提供貸款擔保等,提升經營主體獲得貸款的可能性,緩解融資困境。
拓展經營主體的融合發展模式,破除單一的生產經營方式,支持引導當地的龍頭企業、專業大戶、農村合作社和農戶之間在自愿互利的原則上,可以建立訂單合同機制,形成“企業+基地+農戶”、“企業+家庭農場”等經營主體融合模式,通過農產品購銷合同的形式穩定農產品的價值,增加農民收入。此外,構建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新型經營主體間的股份合作機制,以“按股分紅+務工收入”、“按資分紅+二次返利”的形式使農民從產業融合發展中獲得更多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