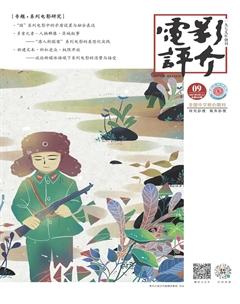中國早期電影類型體系建構與全球文明互鑒未來之路
郭歌
中國最早公認的電影放映,始于1896年8月6日上海徐園“又一村”游藝活動上放映的活動影像;中國最早的電影是豐泰照相館拍攝的《定軍山》(豐泰照相館,1905)等一系列戲曲片;中國早期類型電影的商業性較強……這些都是中國電影百年歷程中得到大多數人認識、在中國電影史中公認的觀點。然而實際上,如果我們能以更加包容的眼光看待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中國電影史,突破既有觀念中的電影的定義標準及意義標記,以電影本體論去理解和豐富中國電影在誕生(拍攝/放映)之初的歷史語境,那么不僅能認識到中國電影從出現、發展到建立類型體系這一或可標志中國電影成熟的過程中,中外電影創作與思想文化的相互映照與借重,還能為當下處于全球化發展時期的中國電影提供珍貴的歷史經驗。
一、中國電影的初始形態與交流借鑒中的變化
與中國電影起始相關的首要歷史節點,便是中國獨立制作的電影出現之前,本土公開的“放映”活動。中國最早的公開“放映”活動并非“電影放映”,而是單張照片的連續“影像放映”。1885年11月21日至23日,一位叫顏永京的留學生在上海格致書院用“西法輕養氣隱戲燈”放映了一組外國風景“影戲”。在美國留學時,顏永京接觸到了以投影技術為基礎的影戲畫片,并將一部分收藏帶回國內,展開了“西法輕養氣隱戲燈”的放映。這次公開放映的作品以英美各國自然風情為主,形式類似于幻燈片,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電影,但卻在上海市民中引起了極大反響,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在中國用來描述電影的“隱戲”一詞也被傳為“影戲”,并就此逐漸沿用下來。得益于出現在同一時期的照相術,電影與照片,或“活動影像”與“單張影像”的聯系深刻地銘刻在了與時間相關的現代技術譜系上。顏永京放映的“西法輕養氣隱戲燈”雖然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電影,但可以將其視為與電影相關的一種初始的影像形態。伯格森在先于電影的誕生撰寫、與盧米埃爾電影公映同年出版的《物質和記憶》中,開篇即提出了“運動切片”的概念,即將連續變化的圖像加以分切,試圖以連續的運動切片來重構運動本身。這一對電影活動的理解方式在西方古典思想中亦有涉及,古希臘哲學家芝諾在著名的“芝諾悖論”中提出了多個難以通過自然知覺反駁的命題,例如“飛矢不動”,即飛射出的箭矢在其經過的每一個點上都是靜止的。這一過于重視“特權性瞬間”的理念在近代被“平均化的任意瞬間”所取代,但為人們理解電影留下了珍貴的思想理念,即拋棄“不動的切片+抽象的時間”之后,以“真正的運動→具體的持續”這一思路,將被簡化為切片的運動還原于持續的時間中[1]。由盧米埃爾兄弟發明、借由商人傳入中國后再于上海徐園放映的成熟電影系統,就是由照片式的影像在均勻的時間內通過畫面的組接和投影放映系統組成的。無獨有偶,中國第一部電影的制作人與“導演”任慶泰正是開辦豐泰照相館的攝影師,他以拍戲裝照聞名京城,且對西方“影戲”始終懷抱熱情。1905年,任慶泰意識到活動影戲院里放映的影片時長過短,片種只有滑稽片與西洋風景片,難以吸引觀眾,于是借當時由京城遍及全國的京劇熱潮,與譚鑫培進行合作拍攝了中國的第一部電影——戲曲片《定軍山》(任慶泰,1905)。《定軍山》以固定機位拍攝譚鑫培在舞臺上出演《定軍山》的完整過程,拍攝完成后在前門大觀樓影戲院公映,引起了觀眾的熱捧。這一具有開創性的歷史事件既是傳統文化與最新技術的結合,又是照相與電影攝錄兩種媒介技術的“西學東漸”,同時構成了從幻燈片式的“影像放映”到連續時間內運動影像的攝制與播映在中國的首次本土實踐。
盧米埃爾兄弟的電影放映首次在巴黎公開七個半月后,歐洲商人在上海閘北西唐家弄徐園內的“又一村”游藝活動上放映了名為“西洋影戲”的電影。此后,各國商人加倫白克、雷瑪斯等逐漸將電影這一舶來品引入中國的茶館與戲院,與煙火、戲法、傳統曲藝等節目一并出現在觀眾面前。這時的西洋影戲只是市民階層休閑娛樂活動中尚不重要的組成部分,茶樓戲院中最重要的節目依然是中國人喜聞樂見的戲曲演出。但與此同時,中國本土電影業開始逐步發展,外國風光片培育出來的觀眾群體成為中國電影的支持者;很快,美國早期好萊塢電影的戲劇性和歐洲電影的寫實主義也成為中國早期電影學習借鑒的范本。由于技術條件的限制與拍攝經驗的缺乏,中國早期電影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借鑒了戲劇影片的拍攝形式,例如攝影機位置固定不變,拍攝舞臺全景;演員遵循傳統戲曲男女不同臺的規矩,并由畫面左邊入場,右邊出畫,在鏡頭前進行舞臺化的表演,直到200尺一盒的膠片拍完為止。[2]在《青石山》(任慶泰,1906)、《艷陽樓》(方沛霖,1906)等一系列戲曲片后,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故事片《難夫難妻》(張石川、鄭正秋,1913)誕生。《難夫難妻》在戲曲表演和拍攝形式上,結合了文明戲(即演變自西方話劇、宣揚現代思想的戲劇形式)而成。影片講述廣東潮州地區的乾坤兩家人,經過一番熱鬧繁瑣的封建買辦婚俗儀式,將一對從未見過面的新人送進了洞房。《難夫難妻》的全部角色均由文明戲的演員但任,影片通過呈現社會上青年男女婚戀問題,試圖引起觀眾討論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其中崇尚自由思想、抨擊包辦婚姻的西方進步思想十分明顯。同一時間,徹底淪為帝國主義殖民地的香港,對西方電影在形式上的借鑒更為深刻。華美影片公司的黎民偉拍攝了《莊子試妻》(黎民偉,1913),講述莊子為了考驗妻子是否忠貞自己而假裝死去,水性楊花的妻子果然帶著情人來到莊周的墳墓前騷擾。短短兩本影片中,滑稽表演與傳統倫理的結合與充滿戲劇性的橋段使影片大受歡迎,美國人布拉斯基將這部電影帶回了美國,使《莊子試妻》成為中國第一部“出口”海外的電影作品。[3]此后,20世紀中后期蘇聯電影的涌入又將蒙太奇理論、現實主義美學與形式主義美學匯入了開創期的中國電影理論中,蘇聯革命影片也為中國電影開啟了另一條迥異于好萊塢電影的創作路徑。在漫長的百年間中,中國電影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交流借鑒中由傳統戲曲片發展為文明戲影片,再向更為成熟的故事片發展;這一過程中,中國電影始終接收并反饋著好萊塢電影、歐洲電影、蘇聯電影、日本電影等外國電影的訊息。
二、中外早期電影的商業競爭與中國類型片體系的建立
20世紀早期,在以歐洲電影為代表的西方電影展開了對中國市場的電影營銷后,中國電影也在對西方電影的借鑒中逐漸突破了相對單一的商業環境,建立起了中國本土電影的體系。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早期好萊塢電影取代歐洲電影作為主要電影作品,進入了中國的茶樓和影院。這些電影不僅對中國早期電影的生產和后續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培養了中國最初的電影觀眾。在好萊塢工業體系的啟發與劇情片的引領之下,中國第一代電影人在制片體系的基礎上,建立了初步的類型片體系。
在與好萊塢電影的商業競爭中誕生的中國類型電影體系中,較為成熟的類型主要有冒險動作片、滑稽喜劇片與愛情片三種,其中涉及的類型元素包括言情、家庭倫理、古裝、神怪片、兒童、偵探等不同的亞類型,“風格上中西雜糅,傳統與現代并置”[4]。第一種是多集冒險片。冒險片通常篇幅較長,轉折較多,以成套的形式配合宣傳發行。當時的好萊塢電影習慣在城市報紙上以“緊張”“俠義”“刺激”等要素進行宣傳吸引觀眾,中國電影也在這樣的氛圍中以歐美電影為師,開始探索、自制冒險片。影片中的男主人公勇敢聰慧,女主人公美麗善良,男主人公經常與特別設置的反派角色為了寶藏、遺產或女主人公展開追逐搏斗,畫面中充斥著大量跳樓、跳車、陷入烈火、被人追殺等驚心動魄的動作鏡頭,在冒險故事中結合了犯罪、驚悚景觀等多種元素。冒險片的黃金時期集中于20世紀20年代,好萊塢冒險片中通俗易懂、緊張刺激的場面,在影院中沒有專業翻譯、說明書也多為英文的情況下,受到中國觀眾的熱捧。1920年,商務印書館借鑒了好萊塢冒險片的做法,推出了改編自美國偵探小說《焦頭爛額》的商業電影《車中盜》(任彭年,1920)。這部電影采用典型的偵探破案形式,講述火車上的乘客莫名丟失行李,大偵探倪歌德在賣花女的幫助下抓到竊賊,并追回了藏匿在地窖中的贓款。與后世的偵探片相比,《車中盜》的情節并不復雜,甚至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推理元素,但這部電影仍可以視為中國類型電影的鼻祖。這一年,洋行職員閻瑞生借鉆戒賭馬未中,后來遇到佩戴貴重首飾的妓女謀財害命,逃亡于松江、上海、青島等地,終于在徐州車站被捕。這一轟動一時的案件被廣泛吸納于小說與文明戲中,商務印書館影戲部門也借“閻瑞生熱”與洋行職員等合作,于次年推出了中國第一部長故事片《閻瑞生》(任彭年,1921)。這是中國電影首次將社會熱點事件搬上銀幕。《閻瑞生》票價雖然不菲,但具有強大的票房號召力,在一星期的連續放映中盈利4000余元,創下了當時中國票房紀錄。這一商業成績大大刺激了剛剛起步的冒險電影,也為類型電影的創作與商業發行積累了經驗。
第二種是滑稽喜劇片。這一類型影片主要借鑒歐洲同類型電影中卓別林、基頓與林戴等優秀的喜劇演員的表演與鏡頭形式。這些電影通常時間較短,滑稽片的長度在兩本左右,被安排在長篇或劇情片之前放映;而具有一定劇情的喜劇片長度在5~8本左右,代表影片有商務印書館、中國影片公司和明星影片公司嘗試拍攝的《飯桶》(盧壽聯,1921)、《憨大捉賊》(任彭年,1921)、《滑稽大王游滬記》(張石川,1922)、《勞工之愛情》(張石川,1922)等,其中充滿了模仿卓別林與洛克等歐洲喜劇演員通過面部表情、肢體動作制造滑稽笑點的橋段,例如追汽車、扔面粉、踢屁股、打架等。
第三種則是愛情劇情片。愛情劇情片的故事相對復雜,更加依賴演員表演與鏡頭語言傳遞人物關系信息,在中國的創作與傳播建立在前兩種影片基礎之上。中國觀眾在觀影經驗豐富后,對劇情片的興趣與欣賞水平均獲得提升,也開始關注著名導演和演員的作品。當時被稱為“白珍珠”“寶蓮”的女演員博爾懷特、美國著名導演格里菲斯都是中國觀眾競相捧場的對象。中國導演但杜宇模仿歐化的生活與好萊塢式的戀愛故事形式,拍攝了《海誓》(但杜宇,1921)。摩登少女福珠與青年畫家周選清相愛,兩人約好如負對方就跳海而死。后來福珠在重金聘禮的誘惑下準備與表兄成婚,卻在舉行婚禮時幡然悔悟,決定跳海自盡。周選清得知愛人悔婚,追至海邊,一對有情人美滿團圓。在《難夫難妻》與《莊子試妻》之后,封建禮教對年輕人自由婚戀觀念的束縛已經徹底減弱,而歐美愛情片中自由戀愛帶來的煩惱成為青年戀愛故事中的主題。這部影片同時涉及了西方愛情片中女主人公在自由選擇中面臨的誘惑與痛苦,以及“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美好結局。這一時期,國產愛情電影中除了少數鄉下人之外,男女主角與其他主要人物全部身著西裝,住在歐化的園林及房屋中,這些源于西方電影中的場景布置與人物設計,使影片帶有新派和洋化的色彩,也使故事增加了與觀眾的距離感。
三、以史鑒今:當下中國電影的全球多元發展思路
任何一個后發的產業,對于新發產業的模仿和依賴都是不可避免的。西方電影豐富的電影類型與創作方法,為中國早期電影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經驗與成長養料。中國類型片體系的建立不僅標志著中國商業電影市場的形成與成熟,更標志著中國電影擺脫了戲曲電影與文明戲電影中依靠作為拍攝對象的戲劇敘事的傳統,電影本身成為表情達意、講述故事的獨立媒介。在出于商業競爭目的、以模仿走出第一步之后,中國電影作為國家民族精神的載體,開始逐漸根植于中國社會現實的民族心理、審美習慣、道德觀念與審美情趣之中。在鏡頭語言的進步上,早期戲曲片作為一種時空綜合藝術,更多屬于空間的范疇;而這批類型片突破了最初以固定機位的取景為內容,鏡頭本身在空間上保持靜止、在時間中線性前進的形態。拍攝方式上,將攝影機與放映機融為一體的攝放機在多家影戲公司投入使用,賦予影片以統一的抽象時間;而無論是直接借鑒蘇聯蒙太奇學派,或通過美國影片間接地受到蒙太奇美學的影響,中國電影都自20世紀20年代的類型片開始,借由蒙太奇活動影像與獨立于放映機的活動攝影機獲得了自身的本質,即在綿延的時間范疇上創造新事物,并以空間的時間化重構現實素材、制造幻覺的能力。從這一角度上講,商業競爭環境中中國類型電影的成熟孕育出了綿延百年的中國電影藝術。
從改革開放、市場化改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如今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電影與世界的聯系愈加深廣。在中國電影發軔之初就已經埋下了伏筆的電影之間的競爭在如今的電影院中更加明顯,“國產電影保護月”與圍繞“好萊塢市場霸權”“民族貿易主義”等議題的爭論甚囂塵上;以生產國家、類型風格為基礎劃分而成的類型電影格局也影響更加深遠。“文化上出現的全球化現象并非只是單一的趨同性,它也可以帶來多元的發展,因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著自己的特征,若想掩蓋或抹去這種特征,就只能導致世界文化的倒退。由此可見,全球化只有通過本土的接受和實踐才能得以實現。[5]”中國電影的理論、創作與實踐在全球化背景下前所未有地受到世界的廣泛關注,一方面在于中國對外開放以來創造的經濟奇跡,另一方面也是西方世界與資本主義文化對中國電影這一相爭百年的對手的注視。通過縱橫交錯的敘事影像與電影事實,中國民族文化正借由電影媒介實現流動,將歷久彌新的歷史故事與人文精神轉化為電影影像,向本土文化圈之外的廣闊遠方進行傳播。當下,中國蓬勃多元發展的電影創作實踐與市場態勢,在電影初期的發展歷程中已經可見端倪。在類型片的創作中,滑稽喜劇片傳承至今日,在兩岸三地出現了馮小剛領銜的“馮氏喜劇”、徐崢代表的搞笑冒險喜劇、王晶代表的滑稽鬧劇等類型;早期的冒險片在20世紀30年代結合武俠小說的熱潮形成了中國特有的武俠類型電影,當下冒險片中的中國元素也在不斷增加,形成了功夫冒險片、武打俠客片、夾雜其他元素類型的武打冒險片等,《環太平洋》系列(吉爾·德·莫·托羅)、《2012》(羅蘭·艾默里奇,2009)、《火星救援》(雷德利·斯科特,2015)等西方電影中,超級英雄拯救世界也都需要華人的力量,中國文化正以獨具特色的力量吸引著世界電影人參與到傳播中華文化、構筑中國形象的電影創作中。在國際傳播的語境中,中國電影的創作者及從業者仍在全球范圍內堅持與不同民族文化之間進行對話與互動。依靠中國如今的電影產業經濟實力與文化生產水平,新時代的中國電影已經不僅滿足于對外國影片進行持續借鑒與參考,而是全方位、多元化地對外輸出人才、技術、資金、創作經驗與民族文化。
結語
中國早期電影的形態變更和產業布局,與電影史教科書上的寥寥數言相比,具有風格更為復雜、延伸更為廣闊、方向更加多元的特征,這正是中國早期電影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全球獨一無二的特色。以更為包容的眼光深入歷史、剝開各種復雜的因素和現象探究中國電影的起源,也是當下建立中國電影學說“知來路,明去處”的必要所在。
參考文獻:
[1][法]吉爾·德勒茲.電影1:運動一影像[M].謝強,馬月,譯.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6:15.
[2][3]于丹,王柬.中國電影的起源[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4:17,21.
[4]秦喜清.華語電影工業方法與歷史的新探索[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121.
[5]王寧.全球化與文化:西方與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