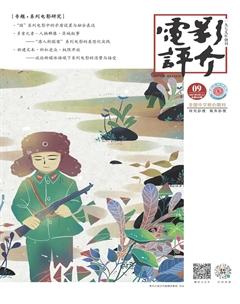破題與轉型:21世紀主旋律電影敘事策略解碼
李鼐
2019年10月1日,電影《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上映,拉開主旋律電影獻禮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帷幕。《我和我的祖國》和《中國機長》分別拿下19.57億元、17.34億元票房,占據國慶檔票房冠亞軍位置。2020年國慶檔,經歷疫情洗禮的中國電影市場呈現井噴式增長,截至10月9日12時,《我和我的家鄉》以18.71億元票房奪得檔期冠軍,最終收獲票房3.86億美元,全球年度排名第三。票房冠軍《八佰》則以4.62億美元票房,奪得全球票房年度冠軍。可喜的成功背后,傳遞的是中國主旋律電影的崛起。無論商業表現還是主旋律觀念傳遞,都達到了口碑與票房雙贏的效果。對于“中國力量”的深層次認同,中國電影市場以票房和市場口碑向全世界傳遞了最強音。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主旋律電影,自1987年系列政策加持下發展迅猛,空前繁榮。1989年歷史題材劇情片《開國大典》首映,標志著我國主旋律電影創作進入政策支持下的良性發展階段。從1991年開始,人物傳記類主旋律電影大量出現,如《焦裕祿》(1990)、《周恩來》(1992)、《毛澤東的故事》(1992)等,在創作方式上與20世紀80年代電影呈現明顯區別:敘事視角下移,善于采用泛情化敘事策略,深受觀眾歡迎。在革命歷史題材電影的敘事手法上,多以宏大敘事手法重現了我國戰爭年代的悲壯歷史,在敘事結構方面兼具紀實性與藝術性。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電影市場進入生產創作與票房的寒冬期,主旋律電影在國家政策和資金的雙重扶持下呈現疲態。創作模式刻板、同質化嚴重的問題,導致觀眾出現審美疲勞,對主旋律電影產生抵觸情緒。進入21世紀后,主旋律電影遭受中國商業電影市場的和國外娛樂大片的內外夾擊。經歷了沉重的打擊后,走上了主動迎合商業化電影市場運作邏輯的改革之路。
近十年的中國主旋律電影進入了改革的快車道,力求摸索出一條切實可行的口碑與票房雙贏之路。跨入新世紀后,中國電影創作的商業化氣息濃重,集聚藝術性與商業性的創作模式初步形成。主旋律電影是兼具宣教功能和政治屬性的文化產品,只有將觀眾吸引進電影院,傳播功能才能得以發揮,進而繼續擔負起引領社會精神文明的重要責任。主旋律電影的轉型主要從類型化創作、敘事策略轉變、“高概念化”制作模式和跨媒介敘事等方面著手,縮短了創作語境和現實語境間的距離,將主旋律電影展示在中國電影觀眾面前。
一、新世紀中國主旋律電影的破題之路
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主旋律電影創作延續了真實歷史題材選取,創新性地融合了藝術性虛構,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雙重認可。《建國大業》(2009)、《十月圍城》(2009)、《建黨偉業》(2011年)、《辛亥革命》(2012)、《湄公河行動》(2016)、《紅海行動》(2018)、《烈火英雄》(2019)、《攀登者》(2019)、《中國機長》(2019)、《我和我的祖國》(2019)、《八佰》(2020)、《我和我的家鄉》(2020)等作品,追溯歷史河流中閃光的回憶,經由藝術化處理和主觀化表達,形成了中國主旋律電影創作的新的敘事策略。
21世紀主旋律電影破題之路的關鍵就是分析和處理好敘事視角的多元化。現實主義題材的大量出現,驅動中國主旋律電影紀實性的民意回歸。敘事視角的多元化,賦予了宏大敘事背景下的小人物有了更多的呈現可能。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由七位優秀導演選取七個共和國發展中的歷史瞬間組成,而每一個瞬間都是從個人或群體的視角見證。這部電影集錦片視角新穎多變,即迎合信息碎片化的主流傳播習慣,又契合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主題演繹。《我和我的祖國》顛覆了以往獻禮片“群英會”的套路,以精良扎實的故事為核心,將宏大敘事的大片模式變為個人敘事的短片模式,采用“大事件+小人物”的選題視角。《我和我的家鄉》是《我和我的祖國》的姊妹篇,連續兩年收獲的口碑和票房足以說明此次嘗試的成功。《我和我的祖國》以七個十年中的重大歷史事件為故事底色:開國大典、兩彈一星、女排奪冠、香港回歸、北京奧運會、航天航空與扶貧和閱兵檢閱。七支國內頂尖制作團隊對這些“歷史現場”進行故事化處理和藝術加工,描摹出一組組鮮活生動的小人物,牽引觀眾走入全民記憶。全片真正的對焦在于喚醒人們潛意識中的集體懷舊,從微觀的個人化視點切入,以小見大,以點帶面,把歷史閃回成片段式的、具體可感的生命過程與人生經驗。以當下眼光穿越時代迷霧,重建虛構敘事與歷史真實的關系,這是艱難的致敬,既不能脫離和割裂,也不能囿于復刻和還原。傳統的電影創作思路已經無法滿足信息爆炸年代受眾的觀影習慣和訴求,中國電影市場對敘事視角的下移、信息量的高速讀取、優質內容的故事填充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21世紀中國主旋律電影的轉型之路
21世紀以來,電影文本理論研究水準普遍提高。媒介形態錯綜復雜,傳播形式日趨多樣,使全民審美能力飆升。完成了階段性的從電影文本的內向研究、媒介環境的外向分析和電影受眾群體分析的全域提升。在從電影大國到電影強國的逐夢旅途中,截止到2019年,生產電影總計1037部。電影市場的蓬勃發展,促進了全產業專業化和智能化提升。中國主旋律電影作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既帶有強烈的中國特色,又承擔著重要的意識形態宣導職能。縱觀21世紀以來的主旋律電影轉型策略,主要體現為以下三個方面:類型電影的敘事模式創新、藝術與技術深度結合的“高概念”電影和跨媒介視角下的敘事策略。
(一)類型電影的敘事模式創新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城市工業經濟和中下層居民數量迅速增長,類型片在西方好萊塢電影生產體系中萌芽。類型電影作為一種電影制作方式,具有對藝術產品進行標準化處理的特征。類型電影具有情節公式化和人物定型化的特點,其分類包括西部片、愛情片、歌舞片、喜劇片、懸疑片、戰爭片和災難片等多種類型[1]。媒介深度融合背景下的中國主旋律電影創作在類型電影創作方面迎合創新,突破單向度的意識形態灌輸,扁平化的人物形象塑和慣式的大團圓結局,基于宏大敘事小人物的典型故事進行了深度挖掘和普世表達。大量高品質的主旋律類型電影問世,也標志著中國主旋律電影類型片初見端倪,如科幻片《流浪地球》、災難片《中國機長》、戰爭片《八佰》和《金剛川》以及富有中國主旋律電影獨特氣質和創新意識的集錦片《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
類型化主旋律電影的出現,體現出中國電影對專業制作人、電影分級制度等電影專業體系建設的必然要求。在中國第五代導演集體沉默的現實面前,大批青年導演在加入電影創作主體的同時,也引入了更加規范的電影創作體系。告別了傳統的“唯明星論”“唯導演論”的傳統單向度判定標準,觀眾對電影文本價值的判斷也愈發清醒。中國主旋律電影在類型化的道路上,從具有情節公式化、人物定型化、影像圖解化三個方面均有所突破。《中國機長》遵循了從遭遇空難到順利得救經典災難片“危機營救”的敘事模式,采用了線性敘事的典型敘事結構,在情節設置中嚴格遵守戲劇創作的“三一律”原則。在人物形象的設計上,追求角色性格鮮明、有血有肉。尤其注重群像塑造,“去英雄化”是中國主旋律電影極具特色的意識形態表達。大量運用平行式蒙太奇和交叉式蒙太奇,以及經典“最后一分鐘營救”的懸念設計。
2020年10月1日,電影《我和我的家鄉》上映,繼電影《我和我的祖國》開創了中國主旋律電影集錦片的本土電影類型之后,延續“好故事+好導演+好演員”的強強聯合,將電影文本創作的類型化賦予了濃重的中國敘事色彩。家國情懷是中國主旋律電影敘事的內核,《我和我的家鄉》圍繞我國扶貧攻堅進程,經由藝術化處理呈現較大成功,用《北京好人》《天上掉下個UFO》《最后一課》《回鄉之路》《神筆馬亮》五個故事描摹出中國小人物大精彩的凡塵浮世繪。在“泛娛樂化”的話語體系下,借助電影類型化的范式,巧妙地融合了六位導演鮮明的個人風格。情節搭脈城市與鄉村,蘊含著對家鄉的熱愛和惆悵,對家鄉與城市融合發展的欣喜。從小人物的低視角,平視身邊的事件:家鄉有了醫保卡、美麗鄉村行、以智扶貧初見成效、荒漠變綠洲和高知當村官。這些故事均采用線性敘事手法,將跌宕起伏的劇情進行了生動演繹。故事的主角張北京、記者老唐、范老師、閆飛燕、馬亮等淡化高光,以更貼近生活的方式回歸現實底色,貼合觀眾審美價值取向和觀影規律。
(二)藝術與技術深度結合的“高概念”電影
20世紀70年代,“高概念”作為術語由美國廣播公司電視節目主管巴里·迪勒(Barry Diller)提出。其中包括借助技術打造視覺影像奇觀、智媒大數據市場分析、跨媒介視角下的敘事策略。
近十年來,中國主旋律電影在技術層面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帶來了一場場視覺奇觀。以《流浪地球》《攀登者》《金剛川》等為代表的國產影片具有較高的技術含量,體現了中國電影產業工業化的進步和成果。首部“硬科幻”電影《流浪地球》在2019年春節檔公映,取得了超過46億元的票房成績。該片講述了中國英雄拯救地球的故事,這種單一線索敘事風格格外符合災難片的敘事邏輯和客觀需要。觀眾的信息處理能力是有限的,大量特效鏡頭的出現無疑會影響影片的敘事空間,所以該類型影片更傾向于劇情簡單、敘事流暢。從以上兩點可以看出,《流浪地球》是一部標準的“高概念”主旋律電影。本片以高水準的特效制作助力藝術創作,開啟了中國電影創作群體的意識形態延伸,點燃了中國觀眾對本土科幻電影的希望。作為中國科幻電影史上首部“現象級”大片,《流浪地球》的上映同樣吸引了海外媒體的目光。本片畫面極具觀賞性,采用電腦CG技術繪制了大量的原創場景,如外太空、殘破的地球表面、太空船以及大量的戰爭場景。“奇觀”的重要體現就是對未知世界的窺探。同時在服裝、化妝、道具方面也是盡量貼合影片的創作背景,進而達到藝術和技術的完美結合。
2013年Netflix(網飛)公司的網劇《紙牌屋》全球同步首播,標志著智媒大數據市場分析正式應用于影視劇集制作。該劇是基于數據調查運算得出的結果,作為現象級的熱播劇集,也將影視大數據推上了神壇。中國主旋律電影走入市場的那一刻起,就意味著必須面臨整個行業的競爭。基于數據運算,稀缺題材可謂極具優勢的選擇。故此,《攀登者》得以問世。本片以登山探險為題材,填補了中國主旋律電影的空白。20世紀,受到拍攝技術和國內電影產業發展水平的限制,諸多電影題材和類型都無法呈現。得益于中國電影市場的迅速成長,這一切皆有了可能。
(三)跨媒介視角下的敘事策略
在跨媒介視角下,電影敘事的通俗化是必要因素。中國主旋律電影如果想進入良性創作循環,就必須直面市場、贏得票房和點擊量。在融合文化的大背景下,亨利·詹金斯提供了“跨媒介敘事”的視角,即“一個跨媒介敘事的故事穿越不同的媒介平臺展開,每個平臺都有新的平臺展開,每個平臺都有新的內容為整個故事做出有差異的、有價值的貢獻”[2]。在Netflix、Disney+等流媒體平臺不斷打造高品質電影的今天,“院線電影”和“網絡電影”之間只有觀影模式的區分,內容愈發趨于相同,疫情更加推動了基于網絡的流媒體平臺與電影制作者的直接對接。影院儀式感下沉至網站付費觀看,一旦被觀眾熟識習慣,那么雙線并行的局面,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實現。面對這樣的媒介局勢,主旋律電影最大的任務就是在每一個平臺實現傳播效果的最大化,提高社會影響力和商業價值。
結語
縱觀近十年的中國主旋律電影,呈現出敘事視角多樣、題材類型豐富、技術含量較高和海內外市場廣闊的特點。首先,主旋律電影題材豐富,數量眾多,票房穩步上漲。回顧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中國電影產業全線關停。國內外電影產業格局發生巨變,好萊塢大片缺席,主旋律電影占據市場半壁江山。危難時刻,唱響主旋律,提升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樣是觀眾的心理需要。其次,主旋律創新續航能力成為產業發展的原動力。2021年3月,《阿凡達》時隔12年的第二輪全球公映,第一個票房日就直沖榜首,讓所有正在為國產票房高歌猛進而雀躍的中國觀眾為之唏噓。面對高品質的好萊塢電影,中國電影尚有距離。面對問題,我們并沒有停滯不前,電影創作者和學者都在不斷自省、不斷進步,并相信只要保證旺盛的創造力和持續的技術研發能力,完成超越只是時間問題。最后,中國主旋律電影未來可期。2021年喜迎建黨100周年,定檔的主旋律電影近20部,其中不乏高質量作品,既反映了市場需要,也表現出中國民眾對國家的熱愛和認可。
參考文獻:
[1]蔡青.試論新世紀以來國產主旋律電影口碑與票房的雙贏之路[ J ].學術論壇,2019.
[2][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體和舊媒體的沖突地帶[M].杜永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