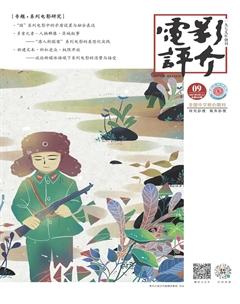《燕尾蝶》的符號化自我詮釋和跨文化價值彌合
徐競
在文化融合視域下,不同地區(qū)、不同題材的影片通過踐行“自我表達、美美與共”的理念,使電影藝術成為具有“國際化”特色的文藝作品。《燕尾蝶》通過巧妙組合語言藝術、配樂和色彩等電影要素,生動塑造了多元文化形態(tài)。本文以《燕尾蝶》為研究素材,以多元文化視域為研究背景,對片中蘊含的自我呈現(xiàn)方式及內(nèi)涵進行分析,為跨文化背景下的電影藝術創(chuàng)作提供啟示。
在文化融合交流環(huán)境中,電影《燕尾蝶》借助宏觀敘事角度來傳遞影片主題,通過將大量文化符號遷移至銀幕,關注大眾命運的發(fā)展變遷來敘述影片創(chuàng)作目的,用細節(jié)敘事感染觀眾,實現(xiàn)人物與敘事視角的有效融合。導演巖井俊二試圖以電影藝術的方式表達個人對現(xiàn)代生活方式與精神思維的反思。該片通過精準把握日本文化的立足點,借鑒中西方文化內(nèi)容,兼顧國家層面敘事、自我內(nèi)涵表達和國際傳播等多維內(nèi)容,實現(xiàn)了藝術性、文化性與傳播性的平衡發(fā)展,為觀眾呈現(xiàn)了一幅基于多元文化基礎上的“國際之都”畫面。
一、自我表達的意蘊生成:敘事主旨的生動詮釋與建構
電影藝術是推動跨文化交際的重要平臺,其憑借立體形象的影視畫面、趣味鮮活的影視劇情,使觀眾直觀感受多元文化的差異性,也使跨文化交際以影視化語言的方式得以直觀呈現(xiàn)。[1]《燕尾蝶》以人性深度、社會銳度等視角來表現(xiàn)創(chuàng)作者對現(xiàn)實事物的觀察與闡釋,其一方面具有現(xiàn)實的殘酷性,另一方面具有獨特人文關懷下的人性溫暖。影片借助多線敘事手法,以對比畫面的形式切換恢宏場景,實現(xiàn)了對“異域文化”的完整展示。
(一)“元都”:符號化的價值空間
巖井俊二的《燕尾蝶》以獨特的電影鏡頭關注邊緣群體面臨的殘酷現(xiàn)實,通過將主人公“鳳蝶”的成長與蛻變置放于虛構的移民城市“YEN TOWN(元都)”之中,為觀眾生動呈現(xiàn)了包含多元文化的空間意境。城市名稱“YEN TOWN”是一座虛幻的城市,其中“YEN”是日元的意思,為影片帶來濃濃的金錢氣息,將所有故事沖突、人物情景都置放于“金本位”的城市氛圍之中。實際上,“元都”是對東京的藝術化塑造,但巖井俊二所選擇的視角并非抨擊或排斥“元都”,而是以厚重的筆觸關注“元都”的人物命運,生動展現(xiàn)了“元都”中蕓蕓眾生為實現(xiàn)個人夢想而努力奮爭的現(xiàn)實百態(tài),渴望喚醒當代日本社會大眾對夢想的探尋,以及對多元文化的理性接納與全面包容。該片通過塑造生活理念迥異、文化語言和價值夢想完全不同的人物故事語境,在虛構的生活場景中,用藝術化的手法鼓勵大眾追尋自我價值。
(二)“元盜”:群體化的精神象征
《燕尾蝶》以孤立、單設的方式呈現(xiàn)城市內(nèi)的不同場景,繁華都市、舊貨市場等不同敘事場景分別蘊含了相應的生活階層及生活方式,傳遞了不同價值觀狀態(tài)下的人物角色風格與價值個性。影片沒有對人物形象進行“符號化”處理,而是通過對“元盜”群體的生活狀況進行抒寫,用人物故事描繪了移民群體在日本社會被邊緣化的現(xiàn)象,為觀眾生動展示了日本社會底層的生活狀態(tài)。影片將故事背景構架于虛構城市“元都”中,將鏡頭對準大量有淘金夢想的外國移民群體“元盜”,由于“元盜”們多沒有正式工作、社會地位低下,為了生存只能從事各種違法生計,深受日本土著居民的厭惡與痛恨。比如,影片塑造的反面人物“偽造之王”劉梁魁,其夢想仍然是發(fā)財后能衣錦還鄉(xiāng),生動揭示了傳統(tǒng)文化蘊涵的“鄉(xiāng)土情結”。影片通過對人物細節(jié)的準確刻畫,使“元盜”們的文化特質(zhì)得到深刻、可信的表達。該片亦通過塑造典型的移民群體人物形象及描繪其在社會中的“邊緣化”現(xiàn)象,真實還原跨文化狀態(tài)下的日本社會。
(三)自我:形象化的敘事主題
《燕尾蝶》以文化展示為基礎視角,以跨文化傳播為主要敘事目的,以鮮活的鏡頭語言呈現(xiàn)主旨思想,通過將文化交流蘊含于相關人物角色及故事之中,使用藝術化的影像方式講述,采用微觀視角來敘述“追求價值、實現(xiàn)自我”的影片主旨。該片描述了一群渴望在“YEN TOWN(元都)”實現(xiàn)夢想和自我價值的“元盜”,他們義無反顧地追尋夢想。導演巖井俊二選擇“飛鴻”“劉梁魁”等人作為外來者群體代表,生動呈現(xiàn)了不同文化形態(tài)下的邊緣群體對實現(xiàn)自我的迫切渴望。逃亡中的飛鴻在使用偽鈔時,被警察逮捕,并被嚴刑拷打死于監(jiān)獄。在飛鴻即將死去時,音樂響起,導演將“蒙太奇”的創(chuàng)作手法與音樂旋律相融合,此刻銀幕呈現(xiàn)出飛鴻“街上狂奔,向往自由”的內(nèi)心幻覺,傳遞了影片的價值觀;這一蒙太奇畫面推動了影片敘事情節(jié)發(fā)展并積累了情感體驗。《燕尾蝶》通過合理使用鏡頭語言、音樂藝術和對比性畫面,展現(xiàn)了創(chuàng)作者的藝術水準,使該片成為研究、認識跨文化語境下自我表達的重要示例。
二、文化空間的多維構建:敘事要素的現(xiàn)實映射與表達
《燕尾蝶》借助鏡頭語言、音樂和色彩藝術向觀眾表達了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與差異,渲染了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奮斗觀,使文化各異形態(tài)下的觀眾皆能夠找到精神共鳴和心理呼應。雖然影片沒有給出跨文化環(huán)境下不同文化的融合相處之道,但影片彰顯的“表達自我、展示自我”的敘事主旨,使其整體超越了文化差異,引發(fā)了不同文化環(huán)境下的大眾情感共鳴。
(一)跨文化交流的語言文化傳播
語言是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也是推動跨文化交流的關鍵途徑。從語言角度看,電影所采用的語言形式、字幕和翻譯語境等內(nèi)容,既幫助觀眾了解影片的深層敘事,也使觀眾生動感受、體會其中蘊含的深層含義。《燕尾蝶》將日本置于“國際化發(fā)展”的框架之中,其中所涉及的“移民問題”,是對日本文化的生動記載,該片通過巧妙使用漢語、日語與英語之間的混亂對比,以語言交流不暢的方式生動講述日本文化并未做好跨文化交流準備的客觀現(xiàn)狀。《燕尾蝶》通過采用多種語言形式,彰顯了自身豐富的跨文化特征。女主角“鳳蝶”生活在中國移民區(qū),周圍環(huán)境中使用了大量漢語,而主人公作為日本華裔的“二代移民”,只會講英語和日語,卻不會說漢語,暗示了身份迷失,也為跨文化環(huán)境下推動不同文化交融提出了相應反思。在影片中,還出現(xiàn)了阿拉伯語等語言,創(chuàng)作者借助打造多語種的生活環(huán)境,彰顯、傳遞了不同文化環(huán)境下“移民”們對自我認同的內(nèi)心訴求,傳遞了渴望“平等對話”的意愿。《燕尾蝶》中呈現(xiàn)的文化差異,生動展示了多元文化環(huán)境下,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交流,并通過構建文化包容、尊重差異的語言環(huán)境,為推進跨文化傳播提供了有效啟示。因此,在電影的跨文化傳播進程中,需要充分利用語言藝術,以融入情感、交流語境的方式,將超越影片語言的情感內(nèi)涵與文化素材融入其中。
(二)音樂詮釋成就價值理念傳遞
《燕尾蝶》的配樂推動著影片敘事主題不斷向前發(fā)展。當下世界音樂文化多元,通過發(fā)揮音樂藝術獨特的文化交流優(yōu)勢,能夠在多元文化場景下,用音樂表達特殊情感。該片借助多元化音樂呈現(xiàn)了跨文化傳播形態(tài)。影片既展示了西方古典鋼琴、吉他曲等藝術,又使用了中國音樂《南海姑娘》,為大眾呈現(xiàn)出一幅趣味形象的藝術畫面。創(chuàng)作者通過對《南海姑娘》進行重新編排,使用軍鼓、弦樂等多種音樂形式,實現(xiàn)了影片的藝術價值超越。該片以美國音樂人Frank Sinatra創(chuàng)作的My Way作為音樂基調(diào),其中歌詞“And did it my way”既是影片的故事主旨,也是導演借助影片載體進行的自我反思表達,并且,收錄了My Way的磁帶也是影片中改變眾人命運的重要“密碼”。音樂My Way不僅推動了影片敘事情節(jié)發(fā)展,亦是影片人物角色的生動展示。因此,My Way既是影片的音樂主旋律,也是對“日本移民群體”內(nèi)心向往自由、渴望實現(xiàn)夢想的生動寫照。導演通過將美國音樂融入日本文化,并以其他民族移民群體的視角進行敘述、呈現(xiàn),以音樂藝術為載體傳遞了多元文化。
(三)多元色調(diào)鑄就情感立體面
電影藝術作為國際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是推動世界文化融合的重要工具。面對多元文化傳播環(huán)境,電影藝術要彰顯文化自信,進而使不同文化形態(tài)、精神理念能夠生動傳遞、推介給世界。在電影創(chuàng)作過程中,創(chuàng)作者需要對本國民族文化進行挖掘、利用,充分滿足不同群體了解多元文化的現(xiàn)實訴求。[2]在電影《燕尾蝶》中,導演用宏大的社會敘事視角包裹影片主旨,以濃厚的文化碰撞形式,實現(xiàn)了跨文化傳播的影視化展示,拓寬了觀眾的鑒賞視野。該片通過選擇暗黃色、幽藍色為色彩主調(diào),烘托塑造了灰暗的敘事氛圍,結合影片劇情向觀眾傳遞出影片人物角色內(nèi)心的迷茫。《燕尾蝶》色調(diào)使用極具新意,導演主要使用黃色、紅色和藍色等色調(diào),在影片開篇、結束部分,均以航拍鏡頭與逆光黃色背景,表現(xiàn)未來的無法預知以及對未來的無限期待。影片的大部分畫面均采用黃色基調(diào)以平衡電影劇情,為觀眾呈現(xiàn)充滿暖意的藝術畫面。導演用紅色色調(diào)來表達人性的溫暖底色,用藍色表現(xiàn)人物死亡,傳遞悲涼的人物情感與悲情的故事情節(jié)。同時,影片《燕尾蝶》在拍攝、制作過程中,使用手持拍攝鏡頭、逆光拍攝等手法,在充分利用膠片寬容度優(yōu)勢的基礎上,為觀眾呈現(xiàn)自然的敘事前景。
三、跨文化傳播的現(xiàn)實啟示:敘事價值的彌合與融通
電影藝術作為承載文化的重要載體,在不同文化融合持續(xù)深入的背景下,逐漸發(fā)展成為跨文化交流、融合的關鍵窗口。《燕尾蝶》借助直觀影視畫面,生動表達、立體呈現(xiàn)了大眾渴望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情感內(nèi)涵,成功跨越傳統(tǒng)、單一的文化形態(tài)。
(一)鏡頭影像關切現(xiàn)實問題
影片通過對諸多場景進行泛光處理,不僅使畫面更加唯美,也使影片整體形成虛幻基調(diào),讓原本虛幻的故事情節(jié)具備一定說服力。在整部影片創(chuàng)作過程中,巖井俊二更換了個人的執(zhí)導風格,盡可能從積極、正面的視角來勾勒人物角色形象,通過描述一群對金錢有著巨大渴望的“元盜”群體,感召當代日本人彌補自身所缺乏的價值活力。影片巧妙使用鏡頭語言、音樂等元素來傳遞不同文化的交流與碰撞,積極探尋極具特色、個性的文化主題。[3]導演通過篩選不同文化狀態(tài)浸染下的人物故事,塑造了各色的人物形象,增添了影片的內(nèi)容深度。該片力求借助影像畫面,將不同文化形態(tài)以共生、共在的方式,呈現(xiàn)更加豐富的文化元素,導演鏡頭下的鳳蝶紋身“燕尾蝶”,象征主人公們在時而絕望、悲切的人生中,仍然保留自身內(nèi)心對自由的渴求與希望,映射出日本社會底層的現(xiàn)實焦慮。
(二)大眾視角傳遞宏大主題
《燕尾蝶》以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為敘事基調(diào),通過熱情觀照現(xiàn)實社會,構建出具現(xiàn)實文化意義的文化傳播體系。日本社會獨特的發(fā)展歷史,決定了其文化氛圍中存在明顯的中西文化劇烈碰撞與沖突的現(xiàn)象,尤其是日本民族的“悲情性格”使其在不同文化間“搖擺”“游離”。因此,面對跨文化傳播環(huán)境,創(chuàng)作者要通過觀察生活、分析生活,選擇合適的文化素材,進而以最佳文化態(tài)度表達自我、展示自我。《燕尾蝶》是導演巖井俊二在創(chuàng)作電影《情書》后的第二部長片,亦是在多語境下開展跨文化傳播的影視化嘗試。作為同名小說的影視化改編,巖井俊二打破了以往個人執(zhí)導的“清新唯美”風格,而是通過使用更加濃烈的筆觸關注人物的精神世界與情感反思,以復雜、多種線索的方式勾勒主人公對自我價值的情感探尋。影片將鏡頭對準劉梁魁、飛鴻等外來群體,通過刻畫他們對自我價值的積極探尋,映射現(xiàn)代日本社會的文化缺失狀態(tài)。[4]同時,在影片敘事過程中,巖井盡可能保留了外來群體的原有文化形態(tài),為多元文化碰撞交流提供了展示空間。
(三)跨越文化界限傳遞人生理念
導演將敘事場景始終置放于文化沖突、跨文化融合的時代場景之中,實現(xiàn)了影片故事線、人物命運線與主旨思想線的充分融合,為多元文化下的跨文化傳播營造出鮮活的視聽空間。影片在開拍之前,導演先后到新加坡、中國等地進行實景考察,以尋找本真、鮮活的文化內(nèi)容,正是被上海的發(fā)展節(jié)奏、城市活力所震撼,巖井俊二確定了電影《燕尾蝶》的創(chuàng)作基調(diào)。[5]從本源上看,正是不同民族的跨文化交流、碰撞,才形成了本片獨特的敘事主題與藝術風格。影片以多元文化交流為敘述視角,將多種文化下的人物角色進行碰撞,增強了影片敘事張力。[6]比如,主人公“鳳蝶”作為華裔二代移民,可以流利使用英語和日語,卻缺失了母語漢語。
《燕尾蝶》以多視角的方式對大量視覺元素進行生動表達,呈現(xiàn)了多元共生的文化形態(tài),蘊含著創(chuàng)作者獨特的審美標準,影片在細膩的人物形象、豐富的故事情節(jié)和考究的音樂藝術中實現(xiàn)藝術升華。電影藝術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往往將國際化理念融入敘事主題、敘事素材之中,但部分影片由于過多重視情緒表達,而使影片呈現(xiàn)自我文化表達的“邊緣化”問題。因此,在電影創(chuàng)作過程中,創(chuàng)作者一方面當重視保持和推介本民族的文化本色,另一方面,發(fā)掘異域文化的深厚內(nèi)涵,以此共同碰撞呈現(xiàn)跨文化交流下多元共生的文化影像藝術。
參考文獻:
[1]梁虹.“一帶一路”語境下中國電影跨文化傳播的思考——以《大唐玄奘》為例[ J ].中華文化論壇,2017(3):61-64.
[2]蘇喜慶,杜平.行為鏈視域下的電影跨文化翻拍[ J ].電影評介,2017(15):82-85.
[3]涂青青.民族性與普適性:典型國家跨文化電影傳播評述[ J ].電影評介,2018(20):97-100.
[4]王譽俊.全球語境下的中國電影海外傳播——基于跨文化受眾的半結構式訪談[ J ].當代電影,2018(6):148-152.
[5]張建德,韓曉強.亞洲電影理論:世界電影與亞洲電影[ J ].電影藝術,2019(6):25-32.
[6]劉迎新,曲涌旭.日本民族性對日本電影的影響[ J ].文藝爭鳴,2020(02):190-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