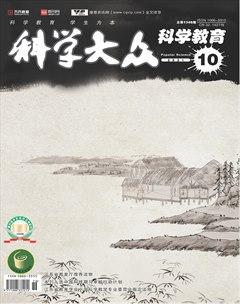《一千英畝》的生態空間批評解構
王雷雷
摘 要:本文從文學地圖敘事、時空體敘事和生態女性主義空間三個交叉研究熱點切入簡·斯邁利的《一千英畝》,幫助讀者更好地在文本與理論層面的實踐中解讀這部小說。
關鍵詞:一千英畝; 生態批評; 空間批評; 文學地圖; 時空體; 女性主義; 敘事
中圖分類號:I712.074?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6-3315(2021)10-106-002
近年來,在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領域內“空間”作為一個研究術語成為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文化議題。尤其是自20世紀后半葉起,西方學術界自地理學學科內部開始經歷了一場“空間轉向”(spatial turn),研究者們逐漸將批評興趣轉至“空間”本身,并將之看作一種重要的解讀范式【1】。由于“空間”的概念本身具有很強的適應性和契合性,幾乎可以和絕大多數的文學批評思潮進行交叉研究,所以空間批評理論在文學界應用越來越廣泛,并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簡·斯邁利的暢銷小說《一千英畝》是1992年美國普利策獎和國家書評人協會獎的得主,被批評界美譽為美國中西部的《李爾王》。從一開始在數學標題(一千英畝)中,斯邁利就以她的數字、直徑、尺寸、限制和最重要的對空間的獨特感知向讀者和評論家提出了挑戰。作者的感知明顯超過了農場長度和寬度的膚淺概念,有著獨特的空間體驗。本文就以這部小說為例,結合西方空間批評領域的新動向,從文學地圖敘事、時空體敘事和生態女性主義空間三個交叉研究熱點切入,幫助讀者更好地在文本與理論層面的實踐中將生態批評和空間批評理論研究結合起來。
1.文學地圖敘事
從文學界到科學界,人們一直習慣于以時間的線性順序來闡述故事和定位事件。近來學界才開始轉向關注基于空間結構的闡述模式,將敘事學(narratology)與空間化的講述模式聯系起來,衍生出一系列關于空間敘事理論(spatial narratives)的研究,嘗試從敘事學角度理解時間與順序的意義生成。弗蘭科·莫萊蒂(Franco Moretti)在文學批評領域采用了文學地圖來探尋空間化敘事的可能性。他在《圖表、地圖、樹圖:文學歷史的抽象模型》一書中提出可以采用大數據可視化方法來解讀文學作品中以地圖、圖表等空間形式出現的敘事結構。莫萊蒂給出了兩個基本點:首先,地圖“突出了文學形式的空間邊界(place-bound)性質:每一種形式都有它獨特的幾何形狀、邊界、空間禁忌和最喜愛的路線。其次,地圖揭開了敘述的內在邏輯:一個由情節組合在一起并自我組織的符號域。文學形式是兩種同樣重要的力量相互沖突的結果:一種來自外部,一種來自內部。文學史慣常的、本質上唯一真正的問題是社會、修辭及它們的關系”【2】。
小說《一千英畝》一開篇就是這段話:“在686號縣道上以每小時六十英里的速度,你可以在一分鐘內駛過我們的農場。686號縣道向北和卡博特大街相交,形成一個丁字路口。卡博特大街也是一條鄉間的柏油大道,唯一不同的是它向西五英里縱貫卡博特鎮......沿著澤布倫河的曲線繼續延展三英里......地球毫無疑問是平坦的。”【3】
作者好像在繪制地圖,她使用了數字、長度、角度和形狀等數學和幾何術語間接地告訴我們農場的長度和寬度:知道被隱喻為李爾王的農場主拉里夢寐以求的農場大小是1000英畝,長度和寬度需要通過使用剩余的可用細節來計算。長度是由以規定的速度(每小時六十英里)在農場前經過的時間(一分鐘)決定的。這種對空間數學測量的強調在小說中一再出現;作者一開頭就談到了“我(吉妮)父親擁有的六百四十英畝的廣袤土地”,吉妮強調她最初選擇的測量方法,指出“這輛(別克)車是六百四十英畝的精確測量方式,而車速使廣袤的土地也變得渺小”。同時埃里克松一家的三百七十英畝土地被拉里所覬覦,因為這樣“我們就能擁有從686號縣級公路和凱博大街交匯處向外延伸的一整圈土地”,“一千英畝,就這么簡單”。作者不斷使用數學術語來比較大小和尺寸,一千英畝上復雜的社會關系被圈在這小小的地圖上,拉里的霸權地位和野心在這里展露無疑,而三個女兒,特別是大女兒吉妮在地圖中被邊緣化,但又無法擺脫這張地圖,和土地一樣成為被剝削的對象。
數字話語還被用來描述意象,強調文本對象的視覺維度,在父親拉里眼里,“整整的一片,六百四十英畝,貸款早已付清,什么錢都不欠了。這片黑色的土地平坦、富庶、松軟,裸露于風雨之中,和地球表面任何一片土地別無二致。”而吉妮看到的是“水源毒化了,表層土壤毀了,機器越買越大”。起初吉妮“認為我們(和二妹羅絲)會在這一千英畝上相伴永遠”。但“過去卻在我腳下萎縮溶解化水,而在其中心的,變化得最厲害的就是羅絲”。通過使用表示顏色、形狀、大小、位置的文字,作者繪制了一張生動的地圖。她告訴讀者,需要反復的精確觀察才有權發表觀點,而不能囿于囫圇的理解。
2.時空體敘事
巴赫金的“時空體”(chronotope)中強調“時間的標志要展現在空間里,空間則要通過時間來理解和衡量”。在時空體中,歷史時間在特定空間中凝固靜止,這個空間“充塞了時間,而且是狹義的歷史時間,即過去歷史的時間”(錢中文,1998:275)。作者一開篇就測繪地圖,卻得出了一個令人困惑的結論:即與科學家的發現相反,地球是平的。在這里,人們可能會困惑為什么作者復位了這種地心說。原文中過去時的was可能暗示了一個遙遠的過去,在莎士比亞創作《李爾王》的時代,當時人們無疑認為地球是平的,任何人如果持有異議,就會經歷伽利略的災難性命運。因此,在一個群體中反對公認的事實(信念)是危險的,甚至是致命的。而斯邁利似乎在冒這個風險,試圖挑戰男性的統治地位。她的《一千英畝》是當代的《李爾王》,時間的嬗變使父女關系被重新解讀:遙遠的過去李爾王大女兒和二女兒為了父親的領地露出種種丑惡嘴臉,傷透老父親的心;小女兒則是正義的化身,為老父親奪回領地。當代“李爾王”拉里的大女兒吉妮和二女兒羅絲卻是被困在父親一千英畝的土地上,傷痕累累,小女兒凱瑟琳背負著兩個姐姐的殷切希望擺脫了父親的控制在大城市安了家,卻轉過頭來成為父親對付兩個姐姐的幫兇。斯邁利的文本敘事創造了一種挑戰男權的閱讀自然的方式,一開始自然空間和女性一起被禁錮在過去的維度,而女主人公吉妮要打破時空維度,和土地一起解放出來。
書中還提到“一分鐘”的時間現在被呈現為一個非常巨大的空間,土地因為車速從廣袤縮小到微不足道。談及對空間的感知,坐在快速行駛的汽車上,一千英畝的確會變得無足輕重;但當時間線被拉長,涉及拉里祖孫三代人在這個空間中的探索和生活,狹小的空間也變得開闊和厚重,因為作者需要數百頁文字才能告訴我們那個空間里到底發生了什么。時空體反映了小說世界中時空動態變化的節奏,斯邁利的小說可以從具體到抽象,構成一張張并置的地圖,也可以通過時空的嬗變從抽象到具體,對那個空間上發生的事情(感知、思考和感覺)實時展示,反映女兒和妻子對父親、丈夫和情人的復雜情感和現代農民對抗工業化的充滿心酸的現實境遇。
時空體超越了膚淺的外觀,提醒讀者注意目力所及的層面下有著另一番天地:“當我還是一個稚齡學童,在學校里學習哥倫布其人其事的時候,不管老師怎么說,我總認為遠古的文明自有其道理。地球儀也好,地圖也好,都無法讓我相信澤布倫縣不是宇宙的中心。毋庸置疑,澤布倫縣的地面確實是平的。在這里任何滾動的球體(諸如種子、皮球、滾珠之類)到最后必然會停下來。一旦停下來,它必然會扎根到厚達十英尺的表層土當中去。”。歷史的凝固使小小的澤布倫縣成為吉妮心目中宇宙的中心,女性的悲哀就在于被困在狹窄的、依賴的、私人的、生育的、家庭的、自然的劣位空間。
3.生態女性主義空間
空間與女性的交叉研究催生了女性主義地理學(feminist geography),其多樣化研究中兩個議題尤為值得關注。其一是空間對女性身份構建的重要影響。其二移動性(mobility)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移動性是美國文學的深層結構之一,長期以來為男性所專有。男性可以在不同空間自由穿梭,而女性往往被束縛在有限的空間。提及哥倫布證實了作者的發現使命:吉妮最后空間意識覺醒,要完成從女性劣位空間到男性優位空間的跳躍,追求自由獨立的人格。女性主義把女性身體和土地進行類比,并認為兩者都被男性所利用。事實上,作者看透了美國男性對土地和女性的看法是如何反映了他們的空間意識:“他擁有這塊土地”;她還提示男性擁有優位空間后衍生的權力秩序“農民們能根據農場的情形迅速猜測到其主人如何”,以及“農場的外觀如何,取決于農場主的性格。”
此外,空間秩序的展現隱含著權力運作的模式。《一千英畝》對土地的看法粗看充滿了美國的夢想,因為它把美國描繪成一個“開放的土地,為強大、雄心勃勃、自力更生的個人提供無限的機會,讓他走上頂峰”[5]。但細讀會發現這絕對是對美國夢的批判。它首先破壞了家庭和個人的幸福;其次它是純粹男性化的,充滿對女性的剝削。換句話說:“吉妮通過講述她的農民祖先對價值所有權和不斷增加生產的意識形態的堅持,通過反諷男性創造性暴力完成的國家建設的主流敘事,將土地和婦女被毒害和被迫緘默的緣由追溯到美國夢”[6]。作者一再暗示她希望找到新的探討維度,解構傳統的女性疆域,沖破空間束縛,實現獨立自主的夢想。這可能是女性擺脫以性別歧視為基礎的宗法社會的重要女權要旨,而宗法社會的支柱是將婦女作為土地對待。小說的中心陳述:“我認為,景觀路兩邊所見向我揭示,目力所及的層面之下有著另一番天地”。作者把地球描述成平的是試圖打破土地和女性被惡意對待的封閉圈,不希望“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農場”一直遭遇迫害。作為小說主人公和敘述者的吉妮想去別處安身,而不是回到男性主導的狀態。但農場禁錮著她,使她無處可去。作者就安排她像種子一樣,放棄線性運動而選擇垂直向下發展,在深深的土層中扎根,探索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的視角,找到生活的希望。
4.結語
像“會扎根到厚達十英尺的表層土當中”的種子一樣,作者深入視野以下的空間,其主要目標是為被迫緘默的女性和被毒害的土地說話,賦予她們希望。從地形上看,她冒險進入了一層層的話語和土地,從“十英尺厚的表層土下”挖掘出了自然和人類的真相。生態批評常常承載著道德、警示和教益;經常為了有益于虛構的人物,在道德上具有啟發性。空間敘事通常都會呈現被凝視客體的預期的力量;它發出的聲音是可推斷的、與心靈相通的;它產生的意義是預言性的”[7]。生態批評和空間批評的結合在未來將發揮愈來愈舉足輕重的作用。
參考文獻:
[1]馬特.城市生態批評理論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
[2]Morett,F.Graphs,Maps,Trees:AbstractModelsforaLiteraryHistory[M]LondonandNewYork:VersoPress,2005
[3] SmileyJ.A Thousand Acres[M]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1992
[4]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5] Slotkin, R.. Regeneration Through Violence: The Mytholog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1600-1860[M]. Middleton, Connecticut: Wesleyan UP,1973
[6] Carden, Mary P. “Remembering/Engendering the Heartland: Sexed Language, Embodied Space,And Americas Foundational Fiction in Jane Smileys A Thousand Acres.” Frontiers,1997:181-202
[7] Cunningham,V.“Why Ekphrasis”Classical?Philology,102.1(Jan.2007):5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