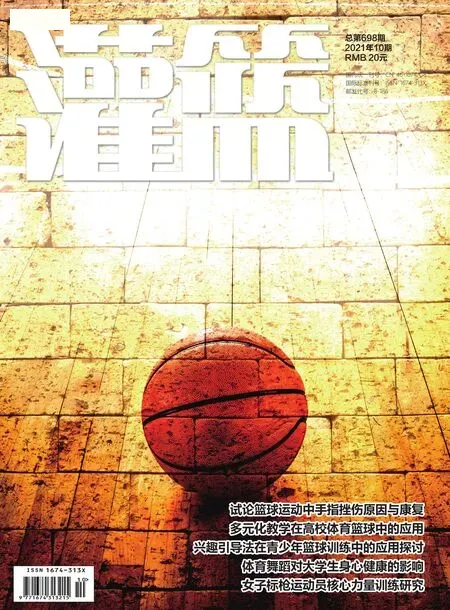新媒體時代體育運動員偶像化的現象分析
張彥 上海體育學院
新媒體的快速發展,為體育運動員從“榜樣”到“偶像”轉型這一過程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運動員的偶像化發展為體育的發展帶來一個新的突破點:促進運動項目的普及和推廣,帶動體育產業經濟增長。但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仍存在著“過度娛樂”等方面的問題。本文通過分析新媒體時代背景下體育運動員偶像化的現象,試圖概括總結出這一現象背后的產生原因,為運動員偶像化發展提出建議。
一、新媒體時代體育運動員偶像化的表現
新媒體,是指在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基礎之上出現和影響的媒體形態。[1]在新媒體時代下,信息的傳播速度更快、內容更廣。新媒體的出現為體育運動員“偶像化”轉變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具體表現如下:
(一)運動員“粉絲”群體擴大
新媒體時代下,運動員們的日常生活和比賽訓練等都受到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運動員開始擁有自己的“粉絲”團體,尤其是那些“明星”運動員。他們擁有大量的粉絲,而這些龐大的粉絲群體背后,都有一系列強大的粉絲團體支撐,微博超話、專屬貼吧等等,都彰顯著粉絲群體的龐大。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媒介生產方式有了更大的改變,其中以受眾參與媒介方式的改變最為矚目。除此之外,這種方式也深刻影響了與媒介緊密相關的偶像生產。隨著新媒體平臺的不斷擴大和發展,運動員們也逐漸走上了“偶像”之路,擁有一大批粉絲群體。
當然,體育運動員偶像化的表現還不止于此。在許多體育賽事中,如全國乒乓球錦標賽、中國女排超級聯賽,幾乎場場都座無虛席,且其中年輕觀眾所占比例較大,甚至還出現了高價倒賣門票的情況。這種以前只會出現在明星演唱會的情景,如今也搬到了運動場上。
(二)運動員跨界熱潮的出現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運動員跨界參加活動,“體育”跨界“娛樂”成為當下最流行的現象。其中,最受矚目的當為“明星運動員參加綜藝節目”,如中國女排參加浙江衛視《來吧冠軍》節目,與“娛樂明星”展開面對面的“較量”;明星籃球運動員加盟《這!就是灌籃》節目,擔任領隊,與素人球迷一同追逐籃球夢想;短道速滑運動員參加湖南衛視《向往的生活》一起體驗砍柴生活的鄉村生活,和朋友們分享比賽時候的趣事……這些運動員的跨界對于受眾來講無疑是新鮮的,而絕大多數跨界參與到綜藝中的運動員,或多或少都在節目中展現出作為一名運動員的“模范作用”,如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吃苦耐勞的寶貴品質等。他們在節目中的表現,時時刻刻都彰顯了“偶像”作用,用長久積累下來的體育精神帶領大眾去了解體育、喜歡體育,這也是為什么近年來體育運動員跨界參加娛樂節目逐漸變多的原因之一。
(三)體育題材影視作品受到追捧
近年來,有關體育題材的影視作品逐漸在市場上受到追捧,不管是講述網球運動的《網球少年》,或是國球的《乒乓》,再到2020年大熱的關于排球的《奪冠》,都收獲了一大批粉絲,并激發了一批人燃起對體育運動的熱愛,從而帶動他們去接觸、學習該體育項目。而關于體育運動題材的影視作品數量逐漸增多,其實也從側面反映出運動員偶像化的現象。在這些影視作品內,運動員的形象塑造其實逐漸趨于一個“偶像”的形象。隨著時代的變遷,“偶像”的定義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從側面來看,“偶像”反映了當代社會文化的多樣形態。其在具體的歷史時期展現出不同的“社會—個體”“集體主義—個人主義”“大眾文化—精英文化”等多重、雙向的互動和博弈關系。綜上,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中的偶像以及人們對偶像的崇拜,“不僅反映出人們思想行為的變化,也折射出社會時代的轉變”。[2]而影視作品中的運動員形象也正好反映出現實生活中運動員逐漸“偶像化”的這一現象。
二、新媒體時代體育運動員偶像化的成因
(一)媒介技術的發展和平臺的推動

新媒體的快速發展,帶來了新聞傳播業的巨大變革。根據CNNIC在2020年9月發布的第四十六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9.40億,較2020年3月新增網民3625萬,互聯網普及率達67.0%,較2020年3月提升2.5個百分點。[3]其中,微博、微信用戶占網民比例最多。這些平臺的出現一方面促進了網民對體育事件的參與;另一方面,也為運動員與網民的交流提供了新的渠道。
互聯網技術的興起使得傳播工具的種類逐漸增多,而人們在不斷適應新興傳播工具的過程中也逐漸找到了更加適合自己的那一個,社會模式也隨之發生了變化。[4]2008年北京奧運會首次通過互聯網、手機等新媒體平臺推出。2016年里約奧運會期間,在中央電視臺發布、互聯網通信傳播及二次創作的各種機制下,形成更加開放與民主的傳播方式。[5]競技體育的魅力往往是其他活動所不能比擬的,它時刻吸引著大批人群的關注。通過網絡直播、短視頻等新媒體觀看比賽現場中運動健兒們奮力拼搏的場景,觀眾可以通過畫面,更直觀地感受到比賽的氛圍,體會到比賽現場的激烈以及運動員比賽過程中散發出的魅力;除此之外,在微博、抖音、花椒直播等平臺上,觀眾還能看到賽場之外運動員們的生活,褪下了“冠軍”光環,他們獨特的個性和與平時不一樣的“反差”給受眾以不一樣的體驗。體育運動員們憑借著各種新媒體平臺,表現出自己脫離賽場時更為“真實”的一面,憑借媒介平臺的傳播來散發自己的個人魅力,收獲了一大批“迷妹”“迷弟”,成為新一屆的“體育偶像”。
(二)運動員的優秀表現和個人魅力
李豐榮等人在《體育粉絲與當代大眾體育》一文中提到了我國體育明星的產生與發展。20世紀90年代,中國女排等一些運動員代表肩上背負著民族重任,帶著愛國主義情懷而成為全民偶像,到了二十世紀初,一大批運動員因為運動成績以及其延伸出來的外型、談吐和才藝等成為體育偶像;自里約奧運至今,就有一大批個性鮮明或者顏值出眾的運動員圈粉無數,成為新一屆的體育偶像。
通過觀察這些能成為“體育偶像”的運動員們,我們可以發現他們身上有一個共同的特質,那就是有較強的競技實力,取得過優異成績。雖然當今社會“唯金牌論”已經漸漸退出主流,但不可否認的是,受眾往往更喜歡實力與個人魅力并存的體育明星,因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夠配得上他們心中“偶像”的稱號。
(三)運動員形象塑造的轉變
以往的運動員媒介形象主要集中于各種相對比較單一的場景之中,例如:體育賽事報道、運動員活動報道或者廣告。[6]這類媒介形象的塑造主要是在強調運動員在賽場上獲得的成績以及其身份特征。隨著社會文化觀念向著消費多元化的演變,體育運動員的媒介形象也逐漸開始向多元化發展,褪去賽場上的冠軍光環,更加真實、接地氣的形象正在慢慢展開。新媒體背景下,各平臺在傳播過程中更注重人文關懷,媒體的關注點更多的放在了運動員的身體情況、當天狀態和傷病上,對于沒能取得優異成績但是在賽場上拼盡全力,努力到最后一刻的運動員也給予了高度的贊揚和鼓勵。大眾們比起金牌,更樂于看到運動員身上所傳遞出來的積極陽光的正能量與永不言棄的人格魅力,因此,那些雖然沒有奪得第一名但仍舊保持樂觀心態的運動員就受到了大眾的喜愛,搖身一變成為新一代的“體育偶像”。
(四)“飯圈文化”的深入
“飯圈文化”最早來源于娛樂界,隨著運動員的跨界活動,“飯圈文化”也逐漸深入到體育圈中。眾所周知,粉絲團隊的助力是支撐偶像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離開了粉絲的支持,也就沒有所謂的“偶像”可言。粉絲是一個龐大的團體,粉絲個體聚集組織而成的“粉絲社群”往往在大眾文化當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傳統媒體往往更關注于運動員的競技成績,而新媒體則更注重運動員的娛樂性和互動性。在此情形下,出現了一大批以“娛樂化”方式走紅的現役運動員,他們或因帥氣的外表、或因開朗的性格,收到除“體育迷”之外的大批“粉絲”的追捧。如今公眾不僅關心運動場上的運動員,也關心鎂光燈下、私人領域中的運動員。[7]運動員們在平時嚴格訓練和比賽之外也有了放松的機會,與“粉絲”們的互動也能讓他們收獲滿足感,而且還能夠不斷積累自身資本,不管對于運動員本人還是粉絲來說,都是大有裨益的。在該傳播過程中,運動員相當于一個傳播者,在泛娛樂化背景下,越來越多的運動員也逐漸擁有自己的粉絲及后援團。運動員們在充當“偶像”的同時也更加敢于表達自身的看法。
結合上文提到的隨著新媒體的不斷發展,體育新聞傳播工具和方式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傳播工具的改變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變得更加迅速、便捷。而正是得益于這種改變,粉絲社群才能逐漸壯大和興起。
三、運動員偶像化帶來的影響
一方面,運動員偶像化發展可以吸引一批本不是“體育迷”的粉絲參與到體育運動中來,通過偶像的力量來帶動喜愛他的人們去了解體育、參與體育,從而起到宣傳運動項目,傳播體育精神的效果。除此之外,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偶像”運動員還能通過代言、廣告等一系列活動拉動體育產品的消費,促進體育產業的經濟增長。
另一方面,運動員偶像化發展還存在一定問題。絕大多數受到熱捧的“偶像運動員”往往會被邀請到娛樂節目之中,由此產生的訓練問題和跨界問題之間的矛盾也需要及時解決與調和。
四、結語
新媒體時代下,運動員的一舉一動都廣受關注。無論是中國女排、中國跳水“夢之隊”還是中國乒乓球隊等,越來越多的中國運動員的良好形象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國人不斷拼搏、爭取成功。運動員在偶像化過程中不僅要保持初心,做好本職工作,傳播體育精神;更要時刻牢記使命,不能主次不分,要積極傳播偶像的力量。
新時期,運動員更要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扎扎實實做好自己的事,做一個合格的“偶像”。而媒體平臺也要傳遞好正確的體育價值觀,從而塑造出優秀的具有榜樣力量的“偶像運動員”。
——評《休閑體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