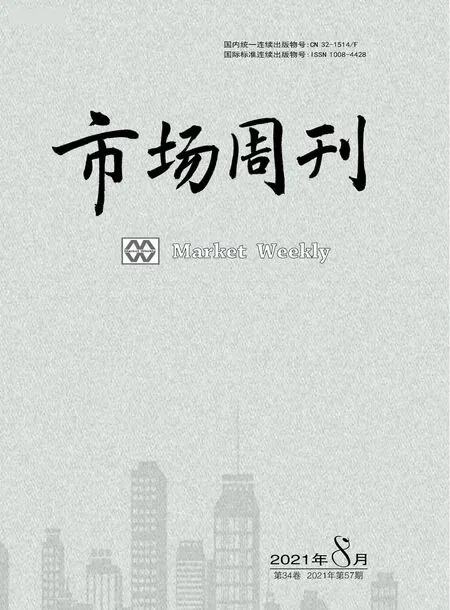定向降準政策對商業銀行信貸投向的影響
王 寅
(南京財經大學,江蘇 南京210023)
一、引言
2014年,為引導商業銀行提高配置到“三農”和小微企業的貸款比例,改善經濟結構性失衡局面,中央銀行首次對符合特定條件的商業銀行適當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到2019年底,定向降準政策共實施了15輪(見表1)。定向降準的貨幣政策針對不同銀行的特點,實施不同的準備金率,并且不斷拓寬考核口徑,以期有針對性地釋放流動性,促進信貸結構的調整。從定向降準的實施對象來看,還是以農商行和城商行為主,商業銀行配置給“三農”企業的貸款小微貸款只要達到一定比例,即可享受定向降準優惠。定向降準是否精準落地,就是要看定向降準釋放的資金是否如期流向薄弱行業,緩解“三農”企業和小微企業的融資約束。因此本文主要從銀行信貸投向變化尤其是商業銀行的小微企業貸款和“三農”企業貸款變化的角度探討定向降準政策的實施效果。

表1 定向降準政策時間表

續表

續表
二、文獻綜述
現有的關于定向降準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的實證分析,對于定向降準政策的效果學者們持不同觀點。部分學者肯定了定向降準的有效性。彭俞超和方意認為我國以定向降準為代表的結構性貨幣政策能夠促進產業升級。張景智認為定向降準政策引導信貸流向的效果明顯。王粲和林朝穎發現定向降準政策的實施縮窄了農業融資缺口,使定向企業的融資缺口得到緩解。劉琦、董斌基于2010~2018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掛牌企業數據,研究發現定向支持企業的信貸可得性明顯高于非定向支持企業,融資成本低于非定向支持企業。
部分學者對定向降準政策的有效性持不同觀點,認為定向降準的政策效果有待商榷。林朝穎等利用定向降準政策實施前后農業上市公司數據,發現單純的定向降準政策作用明顯,提高了農業企業的信貸可得性,但與全面降準同時實施時,政策效果會大打折扣。黎齊發現定向降準政策釋放的流動性外溢到其他行業,沒有通過銀行信貸渠道實現政策預期效果。陳書涵等發現定向降準提高了政策扶持企業的短期信貸可得性,但長期貸款變化不明顯。
現有文獻,學者們觀點不一,但總體上還是肯定定向降準的政策效果。從分析角度看,大部分學者主要從企業端角度出發,但基于銀行角度分析定向降準政策效應以及定向降準銀行信貸渠道傳導機制的文獻相對較少,因此本文從定向降準對商業銀行信貸投向影響角度出發,探討定向降準政策的政策效果。
三、定向降準的傳導機制
傳統的存款準備金制度主要是貨幣當局通過投放基礎貨幣的方式,達到向整個社會提供流動性的目的,商業銀行在這個過程中擔當了重要的角色,通過信貸供給,向非金融部門提供資金流動性,所以銀行信貸渠道是存款準備金制度的一個重要的傳導方式。定向降準政策是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創新,其傳導途徑與傳統存款準備金制度相似,不同點在于,定向降準政策是對達到一定要求的商業銀行實施的準備金率的優惠,主要目的是扶持小微企業、涉農企業的發展,其傳導路徑如圖1所示。

圖1 定向降準政策的傳導機制
定向降準政策對商業銀行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信貸規模,二是信貸結構。首先,定向降準政策會使銀行信貸規模擴大。銀行享受了準備金優惠,其在央行存放的準備金減少,可貸資金就會增加,由于銀行信貸投放的乘數效應,整個銀行體系的貸款總量就會增加,市場就得到了更多的資金流動性。整體資金規模擴大,那么流向定向扶持企業的資金也會增加。其次,定向降準政策影響銀行的信貸結構。商業銀行出于自身經營利潤最大化的需求,可以通過選擇是否向定向扶持企業發放貸款、發放貸款的比例決定是否享受準備金優惠。如果定向降準政策給予銀行的準備金優惠不足以彌補銀行向小微企業、農業企業放貸的風險,那么商業銀行可能放棄定向降準的優惠,將資金投向其他風險收益更加可觀的行業。如果央行給予的準備金優惠力度較大,有利可圖,那么商業銀行將會調整信貸結構,將資金更多地投向政策扶持行業。由于定向降準政策對象是動態調整的,所以銀行每年都會面臨調整信貸結構的選擇。政策范圍內的銀行可以改變信貸結構,減少小微企業貸款、涉農貸款,放棄新一輪定向降準優惠,也可以維持信貸結構滿足政策要求,繼續享受定向降準優惠。政策范圍外的銀行則相反,可以改變信貸結構,增加小微企業貸款、涉農貸款,在新一輪定向降準政策中享受政策優惠,也可以維持原有信貸結構,放棄準備金優惠。
四、定向降準政策的效果及原因分析
(一)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余額增加
2011年我國出臺了小微企業劃分標準,小微企業數據從2015年才開始統計,2015年之前的小微企業貸款使用小型企業及個體工商戶貸款來代替。2018年,央行用“普惠金融領域貸款”代替“小微企業貸款”數據,小微企業數據出現了很大斷層,為了不影響分析,因此選用數據截止到2018年的第一季度。
從圖2可以看出,商業銀行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波動幅度較小,總體呈現平穩增長,這與我國一貫推行的穩健的貨幣政策基調相一致。小微企業貸款余額的變動在圖中體現得不明顯,但總體也是呈現一個增長的趨勢。小微企業貸款余額同比增長率變動相對較大,2014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相較于2014年第一季度有所下滑,但到了2014年第四季度和2015年第一季度就有了明顯提高,2015年第二季度有一點下滑,之后的兩年左右時間小微貸款增長率保持平穩上升的態勢。直到2017年的第三季度,小微貸款增長率下滑明顯,這種下滑態勢一直持續到了2018年的第一季度。

圖2 人民幣各項貸款和小微企業貸款余額及增長率
結合定向降準的實施情況來看,定向降準在2014年第二季度首次實施,但2014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相較于2014年第一季度增長率反而有所下滑,一直到第四季度后才開始上升,一是由于政策傳導的時滯性,二是推行新政策,大部分銀行起初持觀望態度。2015年至2016年上半年,隨著定向降準的操作頻率上升,力度加大,商業銀行擁有了更多的可貸資金,所以之后的兩年內小微企業貸款增長率也保持了平穩增長的水平。可以看出定向降準政策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商業銀行對小微企業貸款的投放,對引導商業銀行信貸資源流向扶持企業有正面影響。2016年2月實施定向降準后,一直到2018年2月,央行都沒有進行定向降準操作,但小微企業貸款余額增長率在2017年第三季度之后才持續下滑,2018年2月定向降準操作也沒有立刻使小微企業貸款增長率上升,這也表明了定向降準政策的傳導存在一定的時滯性。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商業銀行的小微企業貸款增長基本與央行的定向降準政策滯后2~3期,但定向降準政策確實對商業銀行信貸投向起到引導作用,促使商業銀行將資金更多地投向小微企業,緩解小微企業融資約束,促進小微企業的發展。
(二)商業銀行對涉農貸款的投放相對謹慎
我國金融機構涉農貸款到2018年才開始統計,為了保持數據的連續性,選用2013年第一季度到2019年第四季度的數據進行分析,用“三農”貸款余額進行分析,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和中經網。
從圖3可知,“三農”貸款余額增長平穩,逐年遞增。農戶貸款余額同比增長率在2013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一季度波動較大,此后增長率相對穩定,而農業和農村貸款余額同比增長率的變動趨勢較為接近,從2014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第四季度增長率呈逐漸下降的趨勢,但2016年第四季度開始到2017年第三季度出現了明顯的提高,隨后到2018年第四季度又有所下降且一直持續到2019年第四季度。結合定向降準的實施來看,“三農”貸款同比增長率的變化與定向降準政策實施并不一致,存在一定的時滯效應,比如2016年第四季度“三農”貸款的增加可能就是前面定向降準政策實施的滯后效應,也可能是受到2016年國家對三農領域政策的影響,如“三農”領域固定資產和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增加。總體來看,定向降準政策對商業銀行“三農”貸款的刺激并不如小微企業那么有力,并且存在一定的時滯效應。

圖3 “三農”貸款余額及其增長率
(三)定向降準政策效果的原因分析
一方面,與定向降準政策的扶持企業自身特點有關。小微企業分布行業廣泛,具有規模小、經營調整周期短、經營策略靈活、成長性高的特點。而我國農業產業雖然規模大,但存在很多不足,如基礎設施落后、經營周期長、農產品價格較低、農民增收困難、質量效益低等問題,大而不強。所以,同為定向降準的扶持對象,小微企業由于其自身特點,相比于農業企業更容易獲得信貸資源,緩解融資約束。
另一方面,是商業銀行基于自身經營收益和風險的考量的結果。銀行經營有三大原則:安全性、營利性、流動性,所以銀行為了降低流動性風險和不良貸款率,在選擇借款對象時會謹慎評估借款對象的經營風險和償債能力。對于經營風險小、償債能力強的企業,銀行愿意為其提供更多的貸款;而對于經營風險大、償債能力弱的企業,商業銀行就會謹慎對待,減少對這些企業的貸款額度,所以,商業銀行對“三農”和小微企業貸款供給抱有謹慎態度。定向降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引導了商業銀行信貸投向薄弱行業,但是從小微企業和農業企業的經營風險和償債方面來看,商業銀行更傾向給小微企業更多的信貸資源。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對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和“三農”貸款余額及增速的變化分析,發現定向降準確實能夠引導商業銀行將信貸更多地發放給小微企業和“三農”企業,但是由于小微企業和三農企業自身的行業特點和銀行經營的收益與風險考量,商業銀行更傾向于把信貸投向小微企業,定向降準政策對小微企業的扶持效果明顯。基于以上理論分析和描述性分析的結果,本文提出以下兩條政策建議。
第一,政策強度影響商業銀行信貸結構調整的選擇。因此可從政策強度入手,采用差別定向降準政策。一方面,對不同性質的銀行采用差別定向降準政策。由于各類銀行的性質、特征、服務定位不同,其風險收益也存在較大不同,定向降準政策對不同銀行的沖擊不同。針對不同性質的銀行實施不同的降準強度,就可以擴大定向降準政策對所有銀行的激勵作用。另一方面,銀行每年可以動態調整信貸結構選擇是否享受定向降準優惠,因此,可以給予連續符合定向降準政策審核要求的銀行更大的降準力度,以激勵商業銀行更多地將信貸資源投向定向企業,促進“三農”企業和小微企業的發展。
第二,調整定向降準政策的審核的要求,使其更加精細化和具體化。商業銀行只需在小微和“三農”貸款比例要求中滿足其一,就可以享受準備金優惠。這就給予了商業銀行選擇的空間,考慮到貸款的質量、風險以及其他政策因素,各個商業銀行的選擇會逐漸趨同。如本文分析發現,商業銀行更傾向把信貸資源投向小微企業。2018年的定向降準政策又提出了“普惠金融貸款”,“三農”貸款和小微企業貸款一同被劃入其中,籠統的劃分標準只會給商業銀行趨利避害的機會,使其更傾向于把貸款投入某一領域,達不到對所有政策扶持企業的扶持效果。因此,要想定向降準能夠更好地將信貸資源引向目標行業和企業,應該更加精細化定向降準政策的要求,將標準精細到不同貸款主體,不同比例要求,削弱商業銀行信貸投向的傾向性,達到更好地扶持目標企業和目標行業的政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