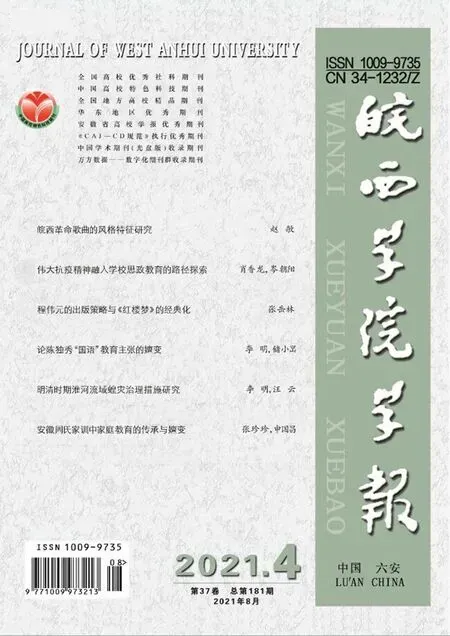論陳獨秀“國語”教育主張的嬗變
李 明,儲小旵
(1.安慶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安徽 安慶 246011;2.浙江農林大學 文法學院,浙江 杭州 311300)
一、“國語”的含義及名稱演變

但五四前后所說的“國語”,有兩種含義,一是指民國時期的全民共同語,二是指中小學語文。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今序(1951)》:“‘國語’這個名詞雖然在辛亥革命前后已曾為進步的改良主義者所提倡,但社會并不理睬。‘五四’后,就在一九二○年,學校語文課程也發生了突變,首先把小學兒童三千年來一貫誦讀的文言文改為白話文,因而把課目名稱‘國文’改為‘國語’。”[4](P11)為什么將中小學語文也稱為“國語”呢?大概中小學語文教學內容為白話文,故此稱中小學語文為“國語”。
二、早年的陳獨秀:“國語”教育的先行者和實踐家
“為了創造全國統一的語言,陳獨秀后來在革命工作之余,做了一生的研究工作。”[5](P60)早在1904年,陳獨秀就提出“國語”教育的主張。他在《國語教育》一文中說:
現在各國的蒙小學堂里,頂要緊的功課,就是“國語教育”一科。什么是國語教育呢?就是教本國的話。……一是小孩子不懂得深文奧義,只有把古今事體,和些人情物理,用本國通用的俗話,編成課本,給他們讀。……一是全國地方大得很,若一處人說一處的話,本國人見面不懂本國人的話,便和見了外國人一樣,那里還有同國親愛的意思呢?所以必定要有國語教育,全國人才能夠說一樣的話。……本國話究竟比外國話易學些,若是學習三年,大約就可以夠用了。免得官話一句不懂,日后走到外省外府,就像到了外國一般,實在是不方便哩[6](P42)。
上段陳獨秀的論述中出現了幾個與語言學有關的關鍵詞:“國語”“俗話”“官話”。我們在這里要簡單地解釋一下各自的語言學含義。“國語”“官話”其實是一個意思,即民國時期的全民共同語。“俗話”應該與書面語相對應,其實指當時的口語。以上陳獨秀所說的話,歸納起來主要有兩點主張:一是要言文統一;二是使用一個全國通行的標準語。當然陳獨秀倡導“國語”教育目的,不僅是為了普及“國語”,更深層的目的是打破陳舊的文言文的束縛,盡可能讓更多的群眾學習知識,了解國內外正在發生的時事,從而達到開啟民智的作用。陳獨秀的主張,可以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審視。可以說,提倡“國語”,陳獨秀并非第一人。“國語”運動,是從1897年開始的[7](P85),直接原因是“他們目擊甲午(1894)那一次大戰敗,激發了愛國天良,大家推究原因,覺得日本的民智早開,就在人人能讀書識字,便歸功于他們的五十一個片假名”[7](P91)。于是福建的盧戇章第一個提出切音運動,其實質是用一種拼音文字代替漢字,但這種主張“有兩個大缺點,所以終于行不通”[7](P99),結果失敗了。陳獨秀提出的“國語”教育主張,正好處在“國語”運動的第一個階段——“切音”運動時期。這一時期,“國語”運動的“宗旨是‘言文一致’,還不甚注意‘國語統一’”[7](P91)。而陳獨秀不但提出言文統一,還提倡使用全國通行的標準語,在當時來說,這種觀念非常富有前瞻性,走在時代的前沿,可惜黎錦熙先生的《國語運動史綱》并未記載陳獨秀的這一功勞,有點遺憾。
再說“國語”運動的第一個階段——“切音”運動的失敗,除了黎錦熙先生所說的“切音”本身存在兩個缺點外,不得不說,失敗還有其他的原因:一是提倡者通過政府部門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語言改革,清末政府動蕩不安,官府做事效率低下,改革推行起來也困難重重,因此改革一再延宕;二是“切音”運動忽略了漢語的語言特點,丟棄了幾千年使用漢字的傳統,脫離了廣大群眾。這些因素預示了“國語”運動第一階段失敗的必然性。
陳獨秀不但提出“言文一致”“使用標準語”的主張,他還緊密聯系實際,緊密聯系人民大眾,1904年創辦《安徽俗話報》,用切實可行的方式,推行“國語”教育。他說:
我開辦這報,是有兩個主義……第一是要把各處的事體,說給我們安徽人聽聽,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邊事體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項淺近的學問,用通行的俗話演出來,好教我們安徽人無錢多讀書的,看了這俗話報,也長點知識[8](P18)。
可以看出,該報創辦的主旨有二:一是讓大眾獲知時事消息;二是教育那些因無錢讀書的人學習知識。也有學者認為該報宗旨是“反帝救國,開啟民智”[9](P26),也是“對國民性的初步探索”[5](P51)。該報是“立足于安徽省情的地方性報刊,語言表述迎合了安徽民眾,符合安徽人民的文化審美趣味。報刊在編輯中加入數量眾多的安徽俚語、俗語,‘別要’(不要)‘搭伙’(合作)‘保不住’‘頂要緊’(非常要緊)‘老山里頭’‘肚子都氣大了’‘可管’等地方性語言均取材于安徽百姓的日常生活,契合了底層民眾的表達習慣”[10]。使用的是“俗話”,其實是當時全省通行的口語,中間夾雜了安徽地方性、淺近的方言俗語。陳獨秀從安徽實際出發,用行動做到了言文一致,遠比那些同時代的“切音”運動要實際,起到了直接宣傳“國語”的效果。
但早年的陳獨秀,對“國語”改革的看法甚至有激進的傾向。同時代的錢玄同對“國語”改革的主張遠比陳獨秀激進,他主張廢除漢字和漢文,“采用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語)”[11](P743),而陳獨秀稍有折中,主張先廢漢字,不廢“國語”,但改用羅馬字母書之,他在《四答錢玄同(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中說:
然中國文字,既難傳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至于廢國語之說,則益為眾人所疑矣。鄙意以為今日“國家”“民族”“婚姻”等觀念,皆野蠻時代狹隘之偏見遺留,根底甚深,即先生與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國語之所以不易廢也。……當此過渡時期,唯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11](P738)。
胡適對陳獨秀的看法極為贊同,他說:
獨秀先生主張“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的辦法,我極贊成。凡事有個進行次序。我以為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單音太多,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須先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話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11](P745)。
陳獨秀甚至認為未來全世界統一使用世界語,他在《答陶孟和(世界語)》中說:
此仆對于世界語之感想,而以為今日人類必要之事業也[12](P721)。
從以上語料中可以看出,早期的陳獨秀,對“國語”改革問題持激進觀點,今天來看,不管陳獨秀的觀點正確與否,早期的他走在時代的最前沿。
三、晚年的陳獨秀:“國語”教育的探索者
可以說,陳獨秀對“國語”教育的探索,伴隨他革命生涯。如果說,陳獨秀早年對漢字漢語的看法偏于激進,但晚年顯得比較保守,一心撲在“國語”“訓蒙”的事業中。直到臨終前幾天,還在撰寫《小學識字教本》下篇(乙)部分的第112個“拋”字[5](P855),因此稱他是“國語”教育的探索者,一點也不為過。1940年底完成《小學識字教本》上篇。這是陳獨秀晚年親自制定的“國語”教材——《小學識字教本》(以下簡稱《教本》)教師用書。
對于該書的一些基本情況,我們有簡單介紹的必要。
(一)版本概況
據唐寶林先生《陳獨秀全傳》,“陳可忠也甚為遺憾,為有所彌補,很快遵陳之囑,把《教本》油印了50冊,分贈學術界人士,特別是對‘小學’有研究的學者,包括陳獨秀的朋友和章太炎(作者注:當是章太炎后人)、梁實秋、王撫五等。此事由當時寓居四川江津白沙鎮的臺靜農和魏建功主持,使這部珍貴之作得以存留下來”[5](P858)。該書傳世的版本有多種。1971年梁實秋將保存的油印稿,在臺灣影印出版并再版,但由于政治原因,將該書改名為《文字新詮》,卻沒有陳獨秀的署名,也沒有陳獨秀的敘。大陸1995年第一次出版的《教本》,是據嚴學宭教授抄存王撫五收藏的油印本,巴蜀書社刊布,但刪削改動和錯誤較多。2017年由龔鵬程先生作序、新星出版社出版的《教本》,基本保持了原貌。
(二)撰寫宗旨
全書由“小學識字教本自序”、上篇“字根及半字根”和下篇“字根孳乳之字”組成。編著該書的緣由非常清楚,即推翻舊的傳統的漢字教學方式,創立新的漢字教學方法。他在《教本·自序》中說:
昔之塾師課童授徒而不釋義,盲誦如習符咒,學童苦之。今之學校誦書釋義矣,而識字仍如習符咒,且盲記,漫無統紀之符咒至二三千字,其戕賊學童之腦力為何如耶!即中學初級生,猶以記字之繁難,累及學習國文,多耗日力,其他科目,成受其損,此中小學習國文識國字之法急待改良,不可一日緩矣[13](P145)。
陳獨秀認為舊的漢字教學方法“戕賊學童之腦力”,急待建立新的“識國字之法”。這是陳獨秀編著《小學識字教本》的原因。陳獨秀極力推翻沿用兩千年的童蒙識字方法——六書,自己創立一套新的識字方法。他認為許慎“六書”有誤,導致“中國文字訓詁之學益入歧途”,“原本小學而為變專家之業”。
“中國文字訓詁之難通,乃因誤于漢儒未見古文,不知形義,妄為六書之謬說。許慎又易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聲之說為指事、象形、形聲、會意,中國文字訓詁之學益入歧途,而又依經為義,經文幾經傳寫,往往乖譌,儒者乃從而穿鑿附會,又或故為艱深,以欺淺學,使學者如入五里霧中。說文字之書籍愈多,而文字之形義愈晦,原本小學而變為專家之業,宜其用力久而難通也。”[14](P16)
唐寶林先生認為,陳獨秀撰寫《教本》,“原意是想匯報畢生研究音韻學和文字學的成果,致力于尋找漢字的規律,以解決漢字難認、難記、難寫的問題。此乃是他大革命失敗后竭力鼓吹漢字拼音化運動無人響應后的另覓路徑之為”[5](P854)。
龔鵬程先生認為,陳獨秀撰寫《教本》,除了長期關注“國語”問題外,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當時的學術風氣使然。他認為“當時風氣,論學而不通語言文字,幾乎便缺了入場券,故第一流學者多馳騁于此”[15](P4)。
(三)基本體例
他將漢許慎《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的六書體系推翻,打破兩千年來的識字傳統,原因是許氏六書是“謬說”,給后人識字帶來困難。在推翻許慎六書之后,他自立一套以“字根”及“半字根”孳乳一切漢字的識字方法,即:
取習用之字三千余,綜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為一切字之基本形義,熟習此五百數十字,其余三千乃數萬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結合而孳乳者也[14](P15)。
陳獨秀所說的字根蓋即今之能獨立成字的獨體字,而半字根蓋為偏旁。根據他的方法,即從常用的3000個漢字中提取500多個字根及半字根,分為:
一、象數(7字);二、象天(15字);三、象地(32字);四、象草木(57字);五、象鳥獸蟲魚(82字);六、象人身體(63字);七、象人動作(67字);八、象宮室城郭(40字);九、象服飾(25字);十、象器用(157字),合計545個。再由這些字根半字根孳乳出一切漢字。
(四)后世研究
對于《教本》的內容主旨,學界亦有些研究。羅會祥認為“陳獨秀以極其科學的方法,深入淺出地講明了每個字的來源及其演化,對兩千多年來形成的文字學理論進行了梳理,在蕪雜的各家學說之中,理出了一個科學的體系”[16]。余國慶認為《教本》有四個特色:從字形入手,分析詞的本義和引申義,井井有條;從語音入手,分析漢語同源詞,卓然可信;從文化史著眼,說明字詞的來龍去脈,獨具慧眼;利用新材料與新方法,使字形闡釋見解新穎,超越古人[17](P197-211)。石云孫認為該書是“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本著科學與民主的精神,以字根連及孳乳字為義例,貫以同源詞研究,提供了一個識字教本,用意在改良識字方法”[18]。熊彥清認為該書“在漢字分類,同源詞研究以及某些具體字詞的解釋上都做出了貢獻”[19],多持贊揚肯定觀點。但有些學者將該書解析為同源詞典,如嚴學宭認為該書是“探討詞的歷史演變……揭示詞之間的淵源關系”[20];楊世元認為該書是“探討語詞歷史演變……揭示了語詞之間的淵源關系,目的在寫出一本采諸民、還諸民的‘新文論’”[21]。福建師范大學中文系曾露珠的碩士學位論文將《教本》看成是同源詞研究[22]。以上這些研究雖然指出了《教本》在其體例、文字學和同源詞等方面的價值,但均違背了陳獨秀的初衷——為童蒙識字而作的教材,并非艱深的文字學著作或同源詞典。高雅靚《〈小學識字教本〉與〈說文解字〉釋義比較——以“象人動作”字根為例》將《小學識字教本》的部分字根的釋義與《說文解字》進行了比較,研究角度具有一定的新意[23]。
龔鵬程認為《教本》“恰好是一本專門寫給教師使用的教材”[15](P8)。關于該書撰寫的目的,陳獨秀已有非常明確的闡述:
許叔重造《說文》,意在說經;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尋求字原;拙著《教本》,意在便于訓蒙①。
以上學界對《教本》的研究,雖然有兩篇碩士學位論文和數篇單篇論文,但還存在一個嚴重不足之處,那就是——以上的研究基本圍繞陳獨秀撰寫和出版《教本》的艱難歷程、該書體例、新方法和同源詞的外圍角度進行研究,還未有專門將《教本》與《說文》二者具體單個字釋義進行細致比較、從書本具體內容展開深入探討的著作。
四、陳獨秀《小學識字教本》述評
以上雖然羅列了學界對《教本》的評價,但他們只是從《教本》的出版艱難歷程、體例和同源詞等外圍考察,沒有將《教本》和《說文》進行深入比較研究,因此評價未能深入或認識有失偏頗,故此,我們有必要對《教本》的學術價值和不足作較為詳細的述評。
(一)《教本》是陳獨秀晚年專為中小學生識字而作的教師用書
雖然后來沒能用作中小學語文訓蒙教材,但這是陳獨秀一生中除革命之外所做的專業性的探索之一,即“國語”教育的探索,值得我們后人尊敬。
(二)客觀來看,該書最大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學術上,而非在教育學上
這盡管違背了陳獨秀的初衷,但實際中《教本》也沒法使用,一是因為這只是教師用書,內容也不全(下篇未完成),而且學生用書還未編纂出來,陳獨秀就去世了。
(三)就此書而言,它有非常高的文字學價值
該書的學術創新之處主要有:
1.體例創新
該書運用全新的視角和方法審視漢字體系,推翻沿用兩千年“六書”識字方法,打破《說文》按部首排字的傳統,而代之以字根和半字根孳乳出所有漢字的方法。以往有部分學者都將《教本》看成同源詞著作,其實是對《教本》釋義方式的一種誤解。《教本》對某個字的解釋往往是由一個字根聯想到相關或形近且偏旁易相混的字,它們之間有的并非同源關系。如在解釋“鬥”字的時候,同時也將形近字“門”放在一起進行形體對比[14](P281)。顯然是為了防止學生將“鬥”“門”相混而故意排列在一起進行對比。
2.材料創新
運用許慎未見過的新材料——甲骨文,分析漢字形體構造,解釋字的意義。同時,書中大量引用金文進行論證;在解釋某些字時,還引用外文進行比較論證。如解釋象形字“日”時,引用了Crefe、日文、Ojbwa字、mok字等象形字進行比較[14](P3)。
3.釋義創新
對《說文》中部分字義提出新的看法。主要體現在:
(1)梳理《說文》釋義的脈絡
如“愛”字《說文》訓作“行皃”,陳獨秀認為“愛當為有所貪戀而行遲之義”[14](P332)。又如“討”,《說文》:“討,治也,從言,從寸。”但未解釋其意義的由來。而《教本》做了詳細的闡釋。《教本》:“討,從言猶從辛,從寸猶從手……象手持辛以平草。故《說文》‘討’訓‘治’。”[14](P287)
(2)指出《說文》釋義錯誤
如“鬥”字,《說文》釋作“兩士相對,兵杖在后,象鬥之形”,但《教本》糾正了它的錯誤,認為“鬥”象兩人徒手相斗,并無兵杖在后[14](P281)。又如“雲”,《說文》:“雲,像雲回轉形,古文省‘雨’作‘云’。”陳獨秀認為“‘云’已省便,后假用為同聲之‘曰’,遂加‘雨’以別之。若依許氏古文省‘雨’之說,則篆文反在古文之前矣”[14](P6)。
4.視角創新
《教本》對漢字教學提供了新視角、新思路,如采取分析字形、相近偏旁聯想和比較等方法,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5.釋義遠比《說文》詳細
《說文》解釋字義時,往往用一句話分析字形、解釋字義就結束了。而《教本》對字義的解釋,遠比《說文》詳細,也可算是一種創新。如“玄”字用了一頁半的篇幅進行論述。
以上只是筆者所見陳獨秀《教本》的部分學術價值,然查檢學界有關中國語言學史或文字學史等著作,它們不提或只是用極少的筆墨記述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倡導之功,如王力先生的《中國語言學史》未見記載陳獨秀在“國語”、文字學等方面的貢獻[24];濮之珍先生的《中國語言學史》肯定了陳獨秀、胡適等在書面語改革的貢獻[25](P488);姚孝遂先生的《中國文字學史》指出“在胡適、陳獨秀等人‘文學革命’口號的影響下,一批愛國的知識分子繼而提出了漢字改革的主張”[26](P578);黃德寬、陳秉新先生的《漢語文字學史》認為胡適、陳獨秀等人“高舉‘文學革命’的大旗,打倒文言,提倡白話,實行語文改革……‘漢字革命’……的口號被提出來了”[27](P263)。以上著作,均未指出陳獨秀《教本》在語言學史或文字學史上的學術價值,實乃一件憾事。
(四)《教本》的不足
運用歷史的觀點看這本未使用的“國語”教材,《教本》的不足也是非常明顯的。
首先,該書認為沿用兩千年的許慎六書為“謬說”,是否值得我們思考?難道“六書”之說一無是處?這種認識似乎有點激進,甚至主觀。
其次,運用陳獨秀的545個字根和半字根能孳乳出一切漢字?當然不能。比如民間百姓使用了兩千年的破體字(今稱為俗字),是字根和半字根不能孳乳的,而完全脫離了正字的體系,它們只是符號而已。如漢字中使用了上千年的漢字簡省符號“又”,《教本》是無法說明的。
再次,有些字的訓釋上,有較強的主觀性,甚至有望文生義、以今律古之嫌。“弔”的俗字作“吊”,《改併四聲篇海·口部》引《俗字背篇》:“‘吊’,同‘弔’。”[28](P626)而陳獨秀認為“‘吊’字像自經者以巾束頸而口張,義亦可通”[14](P108)。我們認為,“吊”只是“弔”形體訛變之俗字,并非陳獨秀所說的象“自經者以巾束頸而口張”。
最后,民國時期,部分學者提出漢字簡化的主張,錢玄同、黎劭西、胡適等提出要接受小老百姓使用了兩千年的“破體字”,“處處都合于‘經濟’原則”[29](P581),而陳獨秀推翻漢代以來傳統的漢字教學方法,取而代之的還是舊的識字方法,可以說是破舊立舊。
五、結語
如果說早期的陳獨秀提出多種較為激進的“國語”改革主張、創辦《安徽俗話報》等活動是為了發愛國救亡、發揚科學、開啟民智,而晚年的陳獨秀專注于“國語”教材的撰寫,其目的首先是為了“訓蒙”,改進“習國文、識國字之法”[14](P15),達到以簡馭繁的效果;但陳獨秀撰寫此教材的根本原因是“不欲窮究事物之所以然,此吾國科學之所不昌也”[14](P16),而通過講授漢字形義之間的關系,從而“使受學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此不獨使學者感興趣助記憶,且于科學思想之訓練植其基焉”[14](P16),可見晚年的陳獨秀仍在探索如何提高國民的科學精神,可謂用心良苦。但我們認為,漢字只是漢語的輔助工具符號,從甲骨文到篆書再到隸書楷書,象形意味越來越弱,符號化的味道越來越濃,而還從分析字形結構、解釋其語義演變的方式來教中小學生,似乎脫離了時代,有點保守了。無論怎么說,陳獨秀除了是新文化運動主要倡導者和政治家外,他還是一名“國語”教育的倡導者和探索者,他的貢獻不能被遺忘,我們后人必須重新審視他在教育學史和語言學史上應有的學術地位。
注釋:
① 該句話原出自《實庵先生復陳部長書》,1941年10月13日,該書編輯小組《臺靜農先生珍藏書札》(一),第271頁,本文轉引自唐寶林:《陳獨秀全傳》第858頁,句中的3個“《》”為筆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