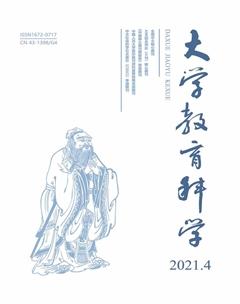疫情沖擊與戰略調整: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的挑戰與前瞻
摘要: 我國高等教育已進入普及化階段。在常態發展條件下,人們對高等教育規模、質量與國際地位等方面持有諸多樂觀預期。新冠疫情的全面爆發,給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帶來巨大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國際高等教育環境、信息技術、社會信任和大學存續前景等方面。不確定性疊加,使基于內外部確定性的常態發展面臨巨大挑戰,根本難題在于知識短缺、資源短缺和制度短缺。在未來普及化發展進程中,我們既要致力于國際高等教育治理與格局重構,將中國高等教育當作世界高等教育新格局的一個中心來建設,又要建立瞬時調節、短期調節和長期調節三層次調節機制,應對自身面臨的嚴峻挑戰。
關鍵詞:高等教育普及化;新冠疫情;不確定性;短缺;前瞻
中圖分類號:G640 ?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0717(2021)04-0046-08
2019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繪制了教育事業發展的宏偉藍圖,提出了高質量普及化發展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務[1]。同年,全國高等教育在學規模和毛入學率分別達到4 002萬人和51.6%[2],標志著我國高等教育已進入“普及化”發展階段。這一成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八大以來在“黨中央堅定不移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堅持優先發展教育,大力推進教育領域綜合改革,持續加大教育投入,教育現代化加速推進”方針指導下取得的歷史性進展[1]。
進入普及化階段后,社會各界更加充滿對高等教育規模持續擴大、質量穩步提高、成為高等教育強國的樂觀預期。產生樂觀預期的理想前提是常態發展下的可預見性和確定性,包括外部環境持續穩定、國內經濟持續向好、高等教育需求持續旺盛,以及知識、制度與資源諸方面的供給能夠滿足基于常態規劃的發展需要。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爆發(下稱“新冠疫情”),誘發對上述樂觀預測的多重不確定性沖擊,國際高等教育秩序、信息技術所能發揮的作用、人際間和國際間的信任、大學存續前景諸方面存在巨大不確定性。不確定性誘發當今世界諸方面的短缺現實,主要表現在與人類生存休戚相關的生產與生活資料短缺、事關人類文明發展與進步的知識短缺、指導或維持與規范人類行為的制度短缺。在多重不確定性與多方面短缺交織背景下,審視我國高等教育普及化進程中的困局、尋求破除困局的出路,解決“我們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道路該怎么走”問題,具有重要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新冠疫情給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帶來多重不確定性
新冠疫情給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帶來的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國際高等教育環境、信息技術功用、人際間和國際間信任、大學存續前景等方面。
(一)國際高等教育環境的不確定性
當今世界高等教育格局是以美國為中心、少數高等教育發達國家為次中心的格局。美國通過所擁有的世界頂尖高校攫取全球智力資源,反復強化其中心地位,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科學技術進步的最大獲益者,并左右世界經濟與社會生產,把控絕對話語權。
在常態發展進程中,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高等教育格局有較強穩定性,難以被打破。新冠疫情爆發后,國家主義、國際權力政治愈發凸顯,多邊主義、全球治理面臨挑戰。中國采取的一系列疫情防控舉措取得重大成功,產生了積極的國際影響。美國政府自身疫情防控措施難見成效,卻將因此帶來的國際形象、國際事務領導力與戰略信譽下滑歸咎于中國和某些國際組織,使國際政治格局面臨巨大不確定性[3]。國際政治格局的不確定性,也不可避免地傳遞到世界高等教育格局。在此期間,美國政府一反常態地自我封閉、顛覆國際化秩序,異化其國際高等教育中心地位之功能,不惜以犧牲自身在國際高等教育格局中的核心地位為代價,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壓中國高等教育,阻礙中國良性發展。
在不確定性作用下,國際高等教育格局可能迎來重構。美國政府的上述行為,表明其雖仍具高等教育強國實力,卻不再具備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之胸懷,國際高等教育已處于某種無中心狀態,格局必然迎來重構。美國以外的高等教育強國、大國有可能利用這次難得的窗口期,調整自身高等教育發展戰略,竭盡所能爭取一批國家的認可,最大限度地吸引國際高等教育資源特別是智力資源,形成以自我優勢為依托的某種高等教育中心,單一中心的國際高等教育體系存在突破可能性[4](P8-9)。舊格局的瓦解、新格局的重構過程,將是充斥著多樣性變革與激烈競爭的過程,其結果必將充滿不確定性。
(二)信息技術功用的不確定性
信息技術是高等教育現代化、普及化發展的重要支撐條件。馬丁·特羅曾指出,“21世紀高等教育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新信息技術對高等教育傳統形式的沖擊”[5](P5-16)。因此,隨著新信息技術發展,在對高等教育普及化發展本質的認識、對高等教育的態度、普及化的條件支持、高等教育制度結構調整、普及化時期的精英高等教育定位等方面必將面臨深刻變革需求和挑戰,“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及各國經濟、社會結構的差異性決定了通過新技術擴大入學機會將采取不斷實驗的方式進行”[5](P5-16)。現在看來,馬丁·特羅是基于常態發展做出的上述判斷。
本次疫情中,國內“停課不停學”“停課不停教”舉措和與國際科技發達國家類似教學手段的實施,雖從形式上、程序上應對了即時性教學難題,但因信息技術生產與開發部門和教師知識儲備有限,信息技術手段和課程與教學資源供給不足,線上教學或為線下學習的“補充”和“點綴”[6],教學過程中只是簡單移植線下教學模式[7],并未體現出相對于傳統教學太大的優越性,致使教師教學體驗感和舒適度欠佳、學生學習獲得感不高、師生和生生交流頻率降低、教學質量保障不足,甚至有教師發出“上網課……基本上是對虛無講課,感覺十分不好”[8](P5-13)的感慨。在此背景下,人們廣泛質疑全面使用信息技術替代傳統教學的思路,對傳統課堂教學表現出空前的認可和懷念。從依托信息技術的線上教學瞬間全面上位卻又迅速“走下神壇”[9]可知,信息技術在未來高等教育中所能發揮的功用尚具不確定性。
(三)人際間、國際間信任的不確定性
新冠肺炎病毒的超強傳染性與人類對其認知的不足,加劇了人與人之間、地區之間、國家之間的疏離,彼此間信任度快速下滑。在國內,由于黨和政府的領導以及廣大醫務人員、社會各領域的共同努力,國內疫情得到全面控制,并陸續復工、復產和復學,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方式發生巨大轉變,地區間人員流動也不同程度存在無形障礙。在國際上,美國借新冠疫情向全世界散布影響中國國際形象的謠言并對中國實施“欲加之罪”式打壓,甚至退出某些國際組織,使國家間信任度下滑。信任的流失,勢必成為未來高等教育普及化發展的一道障礙,不僅辦學秩序、人員流動、跨區域學習不再像以前那樣自然,而且師生到校后必然受到各種防范性制度安排,跨國接受高等教育難度遠大于常態時期。
(四)大學存續前景的不確定性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是制約高等教育普及化進程的關鍵因素。新冠疫情導致的世界經濟與社會大環境不確定性,使大量企業裁員降薪或停產歇業,國內地方政府開展的各種幫扶行動雖有一定作用,但收效低于預期[10]。經濟大環境不確定性不可避免地波及到高等教育,導致大學運行的財政預期不確定性加劇,發展前景的不確定性增多。在國內,疫情一度導致高校無法正常開學,住宿費、后勤營收等重要經濟來源銳減,自負盈虧的民辦高校更是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考驗。為應對疫情沖擊,政府發出了“要過緊日子”的號召[11],各高校積極響應,紛紛削減科研、運行經費。在國外,由于失去經濟營收,“僅僅是春季學期的幾個月內,全美高校就少了80億美元的收入”。雖然“美國‘先大學、后國家的現代化進路使得國家權力始終處于邊緣化狀態”[12],但正是這種權力結構使美國政府不會為大學的存續“兜底”,導致物理學家被解雇、“百年老校”被“永久關閉”[13]。哈佛一項研究預測新冠疫情將持續5年[14],這意味著盡管中國政府的積極防控措施有效地遏制住國內疫情,但國際疫情久久未能得到有效治理,中國將長期面臨巨大的“輸入式”風險,大學正常運行環境面臨巨大不確定性,普及化發展所需的資源供給規模、質量與結構存在多種可能性,普及化發展能否持續、選擇何種發展道路等方面的不確定性增加。
二、多重不確定性暴露出高等教育制度、知識與資源短缺
短缺是一種非均衡供求狀態,而非指絕對的“有”或“無”,供給明顯不足就意味著短缺。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的經典著作《短缺經濟學》曾引起廣泛關注,其突出貢獻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機理及實際運行作了頗為系統的理論描述和說明”[15]。科爾內認為,“短缺,或是作為其他現象的原因,或是作為它們的后果,通過無數紐帶與經濟體制的其他環節……聯系在一起”[16](P12)。短缺的根源在于知識供給不足,知識短缺與制度短缺、資源短缺直接相關——知識短缺直接導致制度供給、資源供給短缺;制度供給決定資源生產規模、結構與質量,并影響知識產生;資源短缺必然產生新的制度供給需求,并使知識生產失去物質基礎。新冠疫情帶來的多重不確定性,暴露出高等教育的知識短缺、制度短缺和資源短缺,各種短缺相互疊加、彼此放大。
(一)知識的短缺
中國高等教育甫一步入普及化階段,就面臨三個不可回避的基本事實:一是普及化進程已處于一個新的時代場景,這是西方國家初入普及化進程時未經歷過的場景;二是在全新時代場景中,“不確定性”與超大規模國家的高等教育普及化交織在一起,形成西方國家從未遇見過的問題;三是能夠處理這些全新問題的知識儲備不足,處于一種新知識的短缺狀態[17]。
“知識短缺”絕非意指知識存量匱乏,而是指已有知識暴露出的結構性短缺,如國際關系、國家治理、物資的生產與儲備等知識的明顯不足,可供參考的全球性重大傳染病危機下的發展道路與經驗短缺。具體到高等教育,表現為普及化發展以及替代傳統教育、應對危機的知識短缺,特別是有關重大疫情下的大學治理與變革、高等教育市場配置與優化、辦學資源供給與儲備、信息技術普及、線上教育的組織與實施、人際溝通等知識的供給滯后。
“知識爆炸時代”并不意味著知識供給充足,也不代表能夠提供有效解決所有問題的知識。新冠疫情及其產生的多重不確定性,使現有知識難以充分應對,進而暴露出諸多困惑與矛盾。或許是因為常態發展過程相對平安、平穩,現行評價制度使經濟理性的組織與個體探索應對全面危機知識的動力不足,代之以名目繁多的“競賽”充斥高等教育各層面。然而新冠疫情及其沖擊前所未有,人類歷史上如此超大規模的國家向高等教育普及化邁進更屬首例,那種“競賽”中產生的“知識爆炸”帶有明顯功利性,其平安狀態下顯現出的整體“方案單一性”、預見性不足,必然使現有知識難以有效應對“競賽”之外的問題。
(二)制度的短缺
制度短缺是制度需求大于制度供給的非均衡狀態。制度不是私人物品,其供給能力和愿望不能由單個制度決定者提供,利益相關者的博弈使制度供給無法達到最佳水平。當相對產品與要素價格、憲法秩序、技術和市場規模中的一種或多種變化發生時,預期成本與收益隨之變化,制度需求也相應變化[18]。當按照現有制度安排不能使制度接受者獲得潛在利益時,制度需求隨即產生,其滿足程度依賴于通過制度調整帶來的收益與資源配置效率,當制度供給滯后時就會產生制度短缺[19]。
新冠疫情發生前,資源配置、招生與就業、科研管理、教學管理、師資隊伍建設、學生管理等制度安排,能滿足高等教育規模、質量、市場以及高等教育功能實現等方面持續向好發展。疫情發生后,制度供求結構發生轉變,制度決定者要在已有制度框架下維持社會穩定、復蘇經濟、調和社會矛盾,制度接受者要求盡可能保證高等教育系統維持運轉、資源配置產生可預期收益。已有制度結構相對于制度變革需求總會表現出遲滯性,制度短缺由此顯現出來。在短缺狀態下,制度決定者以國家行動的方式采取系列應急性措施,包括緊急出臺系列復課復學政策、全面擴大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規模、出臺照顧“抗疫”人員子女的高考招生政策、大幅增加體制內機構工作崗位等,力圖最大可能地化解疫情導致的辦學困境、恢復高校教育教學秩序,并解決社會穩定、大學畢業生就業等緊迫性問題。
應急政策或對策,是對重大危機下制度供給遲滯的瞬時彌補,能夠應對當下之困境,但也必將產生新的制度需求,以解決擴招政策疊加導致的資源配置和人才培養等壓力遞增問題、全面線上教學暴露的教學質量與人際交往問題,以及對信息技術的信心流失問題和照顧性政策帶來的新的社會心理疏導問題等。
(三)資源的短缺
資源短缺存在絕對短缺和相對短缺(結構性短缺)兩種情況。新冠疫情爆發后,國外高等教育表現出顯著的資源相對短缺與絕對短缺,如前文提到的美國百年高校永久關閉現象是典型的資源絕對短缺;為化解資源短缺困境,部分高校不惜解雇科學家或大規模裁員的現象則是典型的相對短缺。國內高校面臨的相對短缺,主要表現在復課復學過程中的網絡資源結構性短缺,特別是城鄉網絡資源供給水平上存在較大差距,如山區農村大學生冒著嚴寒到戶外搜尋網絡信號的情況[20]在城市就少有發生。絕對短缺也有較多表現,如教師上網課時突發疾病,卻因放不下學生而堅持上課[21]的現象是師資隊伍絕對短缺的表現;網絡教學過程中系統頻繁崩潰,以及“過緊日子”的經費預算使科研經費和日常運行經費大幅減少,是技術、硬件、財政資源絕對短缺;線上課程資源良莠不齊,對學生缺乏吸引力,是課程資源絕對短缺。
如果說進入普及化階段是高等教育系統的一大轉變,那么新冠疫情的沖擊則是重大轉折。當面對重大危機時,因缺乏預見性和方案可選擇性,諸多因素疊加就導致產生資源短缺。新冠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是誘發高等教育資源短缺的一個關鍵因素,它使經濟與社會一度停滯運轉;常規發展下的“經濟理性”和“方案單一性”是另外兩個關鍵因素,它們使人們在追逐利益的同時忽視了危機下資源供給機制的探索與建設,進而埋下重大危機下的短缺伏筆,導致高等教育系統在極端情形下難以有效運行。
三、我國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發展前瞻
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中國必然由高等教育大國走向高等教育強國,并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與發展中貢獻中國智慧、經驗與方案。高等教育普及化發展,既包含于高等教育優質化、公平化、終身化、有創新服務能力的教育現代化意蘊之中,同時也對高等教育信息化、國際化提出了高標準、高要求[1]。普及化時代的中國高等教育既要發揮“國之重器”的作用,也要發揮“戰略引擎”的作用[22],因此不僅要著眼于自身普及化發展,也有必要甚至有義務承擔起重構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之重任,并應致力于全球性重大危機下的國內短缺治理體制機制的探索與實踐。
(一)國際戰略上,躋身國際多元高等教育格局中的核心國家行列
美國政府以其逆全球化、逆國際化戰略思維對中國高等教育進行無理挑釁和野蠻打壓的同時,也“意外地”為中國高等教育復興打開了窗口。作為高等教育后發展國家,中國應在堅持融入國際主流體系的同時,努力成為國際高等教育多中心格局中的一個中心,這是我們在普及化階段主動應對國際環境不確定性的重要出路。
1.擺脫“被動隔斷”的邊緣化局面
從新中國成立到新冠疫情發生前,我國高等教育有過3次主動與世界高等教育隔斷的情況。一是1952年院系大調整對原有高等教育體系的顛覆性重構,二是高等教育大躍進的低水平高速趕超,三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完全脫離國際主流高等教育體系的“隨意創造”。上述隔斷均發生于特殊歷史時期,有其歷史必然性[23](P1-12)。新冠疫情發生后,西方反華勢力的借機排擠,使中國高等教育面臨與國際主流體系被動隔斷的巨大壓力。
在過去融入國際主流體系的過程中,中國高等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依附性,主要通過學習、模仿外國經驗實現快速發展,但“西方的學術與教育標準甚至西方的學術與教育話語體系,正在深刻影響著中國的學術與教育,我國的學術與教育將陷入西方主導的結構化體系中難以自拔”,這種被動融入可能導致中國再度被邊緣化[23](P1-12)。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高等教育實力已穩步增強且已進入普及化階段。當面對新的國際環境壓力時,我們應堅持制度自信,發展本土特色的普及化高等教育,避免依附或盲目模仿外國發展模式,并保持和加強與國際高等教育體系的聯系,通過學習有益經驗、總結成就、顛覆性創新,主動保持與國際高等教育的良性融入。
2.奠定國際多元高等教育格局中的核心國家地位
全球高等教育普及化進程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系列全球性問題能否得以解決[24]。大國高等教育能否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充分發揮作用,取決于是否建成高等教育強國。衡量一國是否成為高等教育強國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看該國高等教育在國際格局中是否已經成為一個中心[4](P8-9),因此建議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戰略調整:
第一,以尊重與包容為基本理念建構國際高等教育秩序。以美國為代表的歐美國家建構了一個表面上包容與尊重,而實際上過于自私的教育秩序。在這一秩序下,獲益最大的美國不僅沒有反哺他國的意愿,而且利用優勢反復對世界高等教育資源特別是智力資源進行“極化”,使得強者恒強、弱者恒弱,這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背道而馳。中國是有著包容與尊重傳統的國度,以中國高等教育為基點建構國際高等教育秩序,既能夠對全球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特別是智力資源產生強大引力,也能發揮大國高等教育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形成自主發展經驗。作為核心國家,應有可供次中心和外圍國家學習、借鑒的高等教育普及化發展經驗。那種通過模仿形成的依附式普及化發展經驗,不僅缺乏獨創性而且自主性不足,難以對次中心國家、外圍國家產生沖擊力和吸引力,也就難以樹立牢固地位。因此,中國應努力提煉或形成自主性發展經驗,這些經驗既要服務于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也要能夠在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起到積極影響作用和示范作用。
第三,推動與國際高等教育的雙向融入。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發展階段,意味著國際交流與合作頻率更高、方式更多樣化、內容更廣泛。雖然“疫情穩定后,國際教育的重要性和發展趨勢不會改變,各國之間的教育交流活動不會削弱”[25],但“誰融入于誰”卻是交流與合作進程中的關鍵問題。過去的模仿或依附式發展模式下,中國文化、文明與價值觀的輸出效果欠佳、單向輸入特征明顯,未能產生足夠的國際影響與作用,甚至一度較為被動。雙向融入的意蘊在于,不僅繼續堅持讓資源要素“走”出去,還要把中華文明、文化、價值觀“傳”出去,使世界更好地認識、了解、認可中華文明;不僅吸納外國特別是高等教育發達國家的資源要素“走”進來,還要對其進行中華文化、文明與價值觀的傳播和影響,并且要堅守自主發展底線。
(二)國內戰略上,探索與實踐重大危機下的三層次短缺治理機制
中國“新時代的高等教育正處在重要轉折關頭,目標更高,任務更重”[26],然而初入普及化階段便遭遇重大疫情并暴露出前述三大短缺。知識短缺、制度短缺和資源短缺并非孤立存在,單方面的短缺治理機制難以發揮長效作用,有必要從整體上建構短缺治理機制。科爾內將企業(生產者)在不同情況下采用的調節方式劃分為“瞬時調節”(即對瞬時情況做出適應性反應)、“短期調節”(當“固定資金”不變時采取的策略)和“長期調節”(對未來幾年預期情況的適應,如五年計劃),并把短期調節和長期調節稱為“學習”。“學習”一詞“是在自適應過程一般理論的意義上使用的。生產者在瞬時調節過程引起的問題和損失中吸取了教訓,他將通過更為基本的變化使自己適應持久存在的困難”[16](P30)。在未來的發展進程中,我們應調整高等教育發展戰略,建立瞬時調節、短期調節和長期調節三層次短缺治理機制,以應對普及化發展階段對常態和非常態的知識、制度與資源的復合需求。
1.完善瞬時調節機制,強化危機預警與適應性反應
瞬時調節,是在既定知識、制度與資源供給條件下采取的強制性替代手段,是對短缺“適應性反應”下做出的變通性補救措施。在應對重大事件的瞬時調節方面,中國政府有一整套比較成熟的系統——自上而下的動員機制。改革開放以來,在高等教育領域發生過的兩次經典瞬時調節,即20世紀末的大學快速擴招和本次疫情下緊急出臺的復課復學措施。這種機制效果顯著,特別是后者對促進大學畢業生就業或升學分流、保證大學正常開課、穩定社會秩序等方面產生的作用可謂經典。
自上而下的社會動員雖然能解重大疫情下的燃眉之急,但難以形成長效短缺治理機制。事實上,重大危機已使需求結構發生根本性轉變并形成新的短缺:全面擴招意味著稀釋未來就業機會;應急性增加體制內工作崗位則是預支未來就業機會;線上教育能解決學生上課問題,卻缺乏教學質量保障;“過緊日子”可緩解當前財政壓力,但大學運行尤其是科學研究的財務困窘在所難免;“跑步式”網絡教育建設可能催生資源浪費。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社會動員機制失靈,但它揭示了常態發展下的危機治理短板。今后,應基于危機意識與預警意識完善瞬時調節機制:一是建立預警知識庫和人才庫。應充分發揮大學的知識生產搖籃作用,重點支持應對宇宙、大自然和人類社會重大危機的預警研究,生產預警知識,培養預警人才。二是建立預警制度。針對可能發生的危機,要基于危機意識建立高等教育秩序與資源、大學運行技術與環境、高校破產或退出等預警制度,以正式規則約束行為主體。三是強化危機下的適應性反應能力。財務應急預案、應急技術與設備、管理與運行方案、課程與教學資源等,是發生重大危機時首先面臨短缺的要素,因此有必要增強其適應性反應能力。
2.建立短期調節機制,恢復高等教育常態化運行
重大危機下多重不確定性難題的化解、常態化運行的恢復,要求我們修復知識生產框架、調整與變革制度、改善與儲備資源。
首先,修復知識生產框架。21世紀的大學知識生產模式已發生新的變化,突破了過去追求學術卓越的模式Ⅰ和注重問題解決的模式Ⅱ,“正向突出協同創新的知識生產模式Ⅲ轉型”[27]。普及化階段的高等教育具有多樣化、個性化、學習化和現代化特征[28],知識生產模式的選擇應與之契合,以應對人與自然的演進和發展進程中日益復雜的不確定性。一是要基于三種知識生產模式的分工合作重構知識生產框架。即通過追求“卓越學術”保證知識儲備水平和質量,借助“問題解決”廣泛積累經驗教訓,利用“協同創新”統合智力資源、卓越學術成果和問題解決經驗,使試錯與創新機制更容易發揮作用。二是要基于大學科理念,建構以跨學科、交叉學科為支撐的知識生產框架。當面對人類重大危機時,彼此孤立的知識生產與儲備會顯得能力匱乏,唯有打破學科壁壘建構綜合化知識生產方式,拓寬知識生產視野,才可能有效規避或應對危機。
其次,醞釀與啟動制度變革,調整制度框架。一是建構常態—非常態復合制度框架。即要在現行政策與制度框架下嵌入應對重大危機事件的相關制度,使預算、管理等各種制度覆蓋常態發展和非常態運行兩方面,縮短危機發生時的反應時間,提高制度執行效率。二是修正現有制度與政策:一方面,修正預決算制度,允許提取、留存危機應對專項資金,減輕非常態運行時的政府壓力,同時拓展高校的自主空間,提升其自主應對危機的能力。另一方面,尊重大學邏輯,調整現行科研、教學及其管理制度。首先應厘清科學研究的本真,引導科學研究回歸科學,防范一窩蜂上馬、片面追求或攀比經費或項目等非科學傾向;其次要辯證處理學校教育與網絡教育的關系,科學評價人才培養質量,保護精于學校教育或網絡教育的教師的積極性和創造激情,避免單方面追捧。總之,我們既要使制度良性運行保證高等教育重啟,又要防止因完全回到原有制度框架而產生新的短缺。
再次,推動高校加強資源改善與儲備。中國擁有超大規模高等教育體量,面臨超大規模的資源要素需求。資源要素的儲備數量、結構與質量,決定了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發展的速度與水平。當前,國內新冠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高校教育教學、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等方面也得以全面重啟,國家經濟運行與社會發展已良性復蘇,政府有可能逐步加強對高等教育的資源投放。在未來的發展進程中,政府與高校應共同反思新冠疫情暴露的資源供給問題,加強學校運行必備資源的改善與積累,提升技術資源的研發與改進能力、管理部門的管理與應變能力、教師的線上線下雙重教學能力和人際溝通能力以及課程編制與實施能力、教材建設能力等。
3.建立長期調節機制,創新發展道路
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將是一個相當長時期的發展過程,因此發展道路的選擇顯得尤為重要。探索發展道路過程中,有5個問題值得特別關注:一是普通高等教育擴張式發展已接近尾聲,現行制度框架下通過擴招方式難以持續地、大幅提升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二是由于生育意愿下降和養育壓力遞增,全面放開生育限制的政策效應短期內難以體現出來。三是當前的高中教育是非義務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預備階段,高中教育規模還不能滿足社會需求。四是當前的成人學歷教育機構辦學質量過低,人才培養質量、畢業文憑均得不到社會認可,借助這一渠道實現對普及化的補充,實際意義不大。五是由于身份固化,大部分民辦高校在招生生源、辦學質量、社會聲譽等方面均不理想。上述5個問題是中國高等教育從精英到大眾化,再向普及化邁進的探索過程中積累下來的個性化問題。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發展進程中,我們應創新發展道路,建立長期調節機制,促進高等教育良性發展。
首先,實施高中義務教育制度。一方面,當今社會發展日益加快,社會各領域對從業者的科學文化素質要求大幅提高,初中文化水平已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發展和學生全面發展需要,因此應保障適齡學生全面接受高中教育,實現高中教育全民化。另一方面,逐步將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的教育對象擴大到全體適齡學生。在現行選拔方式下,相當一部分中考落榜學生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這種實際不適應高等教育普及化需要。即便高等教育體系的容量有限、必須淘汰一部分適齡學生,也應在將全部適齡學生納入甄別與選拔對象前提下完成。實施高中教育義務化戰略,不僅可以解決“毛入學率”問題和機會均等問題,更重要的是可以化解高校的生源質量危機。
其次,調節民辦與公辦高等教育的關系。盡管相關法律法規明確規定了民辦高等教育與公辦高等教育的對等身份,但實際執行中仍以舉辦者身份為標志進行分類和貼標簽式分層,這不利于民辦高校的生存發展與辦學質量的提升。在普及化階段,應實施尊重公辦、民辦高校對等地位的“分類但不分層”發展模式,即僅劃分辦學類型而不進行身份、層級或等級分類;改革招生制度,鼓勵民辦高校通過提升辦學水平參與優質師資和生源競爭,使其擺脫邊緣化危機、化解生存困境;建立對等的弱勢高校退出機制,對辦學條件和教育質量缺乏保障、生源嚴重不足的學校,均應依法依規使其退出高等教育系統,以此推動兩類高校樹立質量意識、危機意識。
再次,推動成人高等教育轉型。成人高等教育因入學與畢業條件的過低難度、受教育者動機與目的的過強工具性、教育效果的差強人意,其教育意義日漸淡化,在學歷教育體系中的存續價值日趨下滑。尤其是疫情過后全日制高校“專升本”招生規模的急速提升,嚴重沖擊了成人教育的生源,令此類教育面臨生存危機。因此,建議推動成人教育退出學歷教育行列,轉向實施職后非學歷教育,致力于滿足成年人提升工作能力、改善生活質量、拓展業余生活空間等方面的需要,其學歷教育功能可代之以全日制高校的MOOC或類似教育形式。
綜上,新冠疫情對初入普及化發展階段的中國高等教育系統產生了深刻負面影響,高等教育自身應積極應對而不是消極承受。高等教育“改革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29]。短缺性和不確定性的出現是中國高等教育普及化發展階段面臨的重大挑戰,同時也是重新建立在國際高等教育格局中地位的最佳契機,還給發展模式選擇、高等教育治理變革提供了切入點。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冠疫情帶來的不只是危機,還帶來了某種非預期作用。在今后的普及化發展進程中,中國高等教育能否把握這一節點進行深層次變革,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1] 中國政府網.繪制新時代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 建設教育強國的宏偉藍圖[EB/OL].(2019-02-23)[2021-03-26].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23/content_5367993.htm.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9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EB/OL].(2020-05-20)[2020-05-30].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005/t20200520_456751.html.
[3] 周方銀.新冠疫情背景下國際格局走勢與中國的應對[J].當代世界,2020(07):4-10.
[4] 羅華陶.重大疫情后國際高等教育格局將會顛覆和重構[J].高等理科教育,2020(04).
[5] [美]馬丁·特羅.從大眾高等教育到普及高等教育[J].濮嵐瀾,譯.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3(04).
[6] 沈忠華,鄔大光.大學生在線學習成效及滿意度的影響因素探究——基于結構方程模型的實證分析[J].教育發展研究,2020(11):25-36+59.
[7] 樂傳永,許日華.高校在線教學的成效、問題與深化[J].教育發展研究,2020(11):18-24.
[8] 孫周興.除了技術,我們還能指望什么?——由新冠疫情引發的若干技術哲學思考[J].上海文化,2020(04).
[9] 鮑威.疫情中走下“神壇”的線上教學[J].高等理科教育,2020(03):7-9.
[10] 李卓,包益紅.新冠疫情下經濟不確定性之不確定研究[J].經濟評論,2020(04):46-54.
[11] 李克強.各級政府都要過緊日子,決不允許搞形式主義[EB/OL].(2020-05-28)[2020-08-04].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0/05-28/9197298.shtml.
[12] 徐娟.美國與德國大學高層次人才引進中三種權力的影響差異[J].高等教育研究,2019(07):97-103.
[13] 孫志成,等.核物理學家被解雇,百年高校永久關閉!疫情阻斷生源,英美大學損失慘重[EB/OL].(2020-08-03)[2020-08-04].https://xw.qq.com/cmsid/20200803A03E8Q00.
[14] 搜狐網.哈佛預測新冠將持續五年,哪些專業將成為社會發展新趨勢?[EB/OL].(2020-07-16)[2020-08-04].https://www.sohu.com/a/408024104_763433.
[15] 李振寧.科爾奈經濟思想的精華[J].經濟研究,1986(09):24-31.
[16] [匈]亞諾什·科爾內.短缺經濟學[M].高鴻業,校.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6.
[17] 程亞文.新知識短缺的歷史與今天[J].讀書,2018(12):3-11.
[18] 羅必良.新制度經濟學[M].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5:133-135.
[19] 任群,阮文彪.論農村制度結構性供給短缺及創新策略[J].現代經濟探討,2010(04):75-78.
[20] 劉柯辰.女大學生雪中坐2小時 3800米高山上找信號上網課[EB/OL].(2020-03-25)[2020-08-04].https://edu.sina.com.cn/l/2020-03-25/doc-iimxxsth1126348.shtml.
[21] 彭佩.開在病房里的“課堂”[EB/OL].(2020-04-01)[2020-08-04].https://edu.rednet.cn/content/2020/
04/01/6968248.html.
[22] 原春琳.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巖:中國高等教育不能身子進入普及化,腦子停留在大眾化,習慣停留在精英化 [EB/OL].(2020-09-15)[2021-04-06].https://s.cyol.com/articles/2020-09/15/content_kvAmXzf4.html.
[23] 賈永堂,羅華陶.新中國高等教育發展道路的歷史考察——基于后發展理論的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6(05).
[24] 別敦榮,易夢春.高等教育普及化發展標準、進程預測與路徑選擇[J].教育研究,2021(02):63-79.
[25] 岑建君.疫情影響下的國際教育政策走向和未來發展[J].大學教育科學,2021(02):10-15.
[26] 余小波,劉瀟華,張亮亮.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保障的發展與評析[J].高等教育研究,2020(02):36-44.
[27] 白強.大學知識生產模式變革與學科建設創新[J].大學教育科學,2020(03):31-38.
[28] 葉雨婷.教育部高教司司長:進入普及化階段的高等教育有四大特征[EB/OL].(2020-12-03)[2021-04-08].https://new.qq.com/rain/a/20201203A0D7QV00.
[29] 李震聲.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評《結構主義視野下的博洛尼亞進程》[J].大學教育科學,2017(04):2.
Impact of COVID-19 and Strategic Adjustment: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in the Universalization Stag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LUO Hua-tao
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universaliz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ormal development, people hold many optimistic expectations on the scale,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higher education.COVID-19 has brought great uncertain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mainly in the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ocial trust and the prospect of university existence. The superposition of uncertainty makes the normal development slow, where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ertainty face great challenge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lies in the shortage of knowledge, resources, and system.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universalization, we should devote ourselves to the governance and structure re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regard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enter of new structure of world higher education, and establish a three-level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instantaneous regulation, short-term regulation and long-term regulation.
Key words: univers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OVID-19; uncertainty; shortage; prospect
(責任編輯 ?黃建新)
收稿日期:2021-04-08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我國超大規模大學的極化效應、擴散效應及其轉化機制研究”(72064012);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我國超大規模大學組織績效研究”(20XJA880004);國家民委民族研究項目“‘雙一流建設背景下地方民族高校轉型發展機制與對策研究”(2020-GMD-018)。
作者簡介:羅華陶(1972-),男,湖北利川人,教育學博士,湖北民族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高等教育理論、高等教育政策、區域高等教育研究;恩施,44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