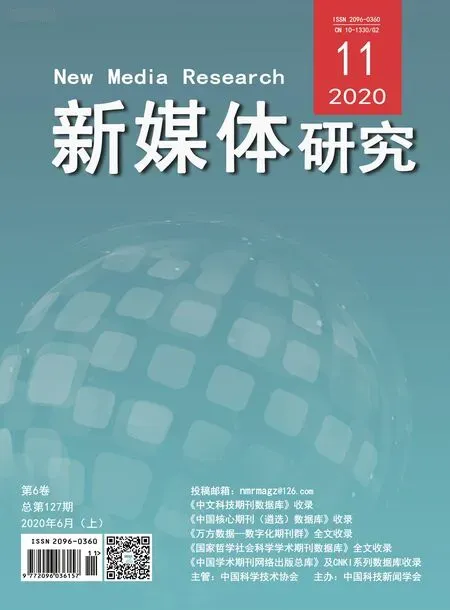技術與遮蔽:海德格爾哲學視域下的算法技術
時盛杰
關鍵詞 算法;海德格爾;技術;集置;遮蔽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21)11-0020-03
以算法為核心的新媒介技術極大改變了媒介傳播形態與社會傳播秩序。但是算法媒介卻又飽受爭議,人們在享受個性化、精確化信息推送服務的同時,也注意到了算法偏見、算法歧視、算法黑箱等負面效應。如何看待這一新技術成為了學界的熱點話題,本文從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的哲學思想出發,探究算法技術的本質、擴張與風險。
德國媒介理論家基特勒曾高度贊揚了海德格爾,認為“只是到了海德格爾時期,對技術媒介的哲學意識才第一次出現,數學與媒介的連接、媒介與本體論的連接也以更加精確的術語而得到闡明”[1]。海德格爾本人雖然并未留下專門的傳播學著作,但是其哲學思想卻給我們對算法技術的追問提供了啟示。
1 集置:算法技術的本質
海德格爾以現象學的視角審視現代技術的本質,他認為“技術之本質也完全不是什么技術因素”[2]。海德格爾并沒有將技術的本質歸結為某種實體性的要素,而是以 Ge-stell(英文為Enframing,學者譯為“集置”或“座架”)作為現代技術的本質。海德格爾認為“集置”是“那種促逼著的要求,那種把人聚集起來,使之去訂造作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者的要求”[3]。從詞源分析來看,Ge-這一詞根意為聚集,stell則源于德語stellen,表示擺置、擺放。
可見,海德格爾的 Ge-stell包括了三層含義:一是現代技術的根本性,即現代技術已經成為了存在者生存的框架,人們在按照技術的先在框架生活;二是現代技術的普遍性,即現代技術已經完全滲透進入此在的生活之中,人無法游離在技術的“集置”之外;三是現代技術的強制性,德語stellen有“對某人提出要求”之意,Ge-stell所要求的“擺置”與“聚集”帶有強制性,一切存在者都要按照技術的要求“擺放”與“聚集”。
“集置”的特點既在于徹底的實用主義,任何存在物都被降格為有用的對象;同時也讓存在者自身在這一對象化的過程中將自我也對象化了。換言之,就是海德格爾意識到了現代技術的“異化”——人并沒有成為技術的主人而是奴隸。
可以說,海德格爾的論斷是對當今算法技術的完美“預言”。算法如今廣泛運用于人們的工作生活場景之中,人們被“拋入”算法技術的先在框架之中。普通大眾并沒有權力編輯算法的程序與規則,只能被動地接受算法程序以做出行為。例如在生產勞動領域,各種CPI考核指標層出不窮,讓勞動者深陷其中。2020年9月,《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一文刷屏社交網絡,將外賣員與企業算法系統的矛盾公之于眾,呈現了算法技術的“集置”本質。
除此之外,算法技術“集置”本質還體現在社會傳播領域。算法傳播的個性化推薦產生的“信息繭房”已經在無形地塑造我們的日常觀念,甚至已經成為了“生活常識”的最主要來源。而常識往往是人們思考、認識事物的原點,人們在無形之中已經掉進了算法技術的陷阱。人們因為自始至終就生存于這樣的數字時代,所以無法做出區分判別,其看待技術的視角也是技術化的。同時算法的重要數據基礎都來源于用戶自身,用戶在享受算法帶來的技術便利的同時也在提供數據,實際上將自己對象化、降格化。
2 促逼:算法的擴張方式
算法技術的本質是“集置”(Ge-stell),但是算法技術并非是一種先驗存在物,而是科學技術的發展的高階段產物。海德格爾認為“在現代技術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種促逼”[2],算法技術正是通過“促逼”而入侵存在者的領域。
“促逼”一詞的德文為Herausfordern,意為“挑戰,挑釁,挑起,引起”。海德格爾用“促逼”一詞說明了現代技術的“迫近性”。他認為農民的耕種行為就不是一種促逼,因為他將種子交給自然并耐心等候。而現代技術貫徹著高效、快速、便捷的實用主義哲學,通過“促逼”擺置自然。“促逼”不僅是技術層面的對自然的壓榨,更是人存在狀態的轉變,“通過促逼著的擺置,人們所謂的現實便被解蔽為持存”[2]。“持存”特指那些被對象化、被榨取、被支配的事物。
作為現代新技術的算法,其“促逼”能力主要來源于兩個層面:一是技術層面的工具性促逼;二是社會層面的權力性促逼。
所謂的工具促逼,就是指算法技術憑借其定量化、系統化、精確化的特點擊敗了傳統技術,成為了當代技術中的“顯學”。技術時代的人們將世界看作一個與生俱來即可測量與精確認知的,由因果關系相互組合聯系的“計算復合體”。精確地認識真理,將哲學“科學化”是西方思想家的普遍傾向。算法的出現與運用無疑讓技術樂觀主義者看到了認識終極真理的希望。憑借著海量數據、機器學習,算法可以進行精確模擬、分析和預測,算法在理論上和實踐中的確在揭示終極真理的道路上擊敗了其他技術。
而社會層面的權力促逼,則是指算法技術在權力的主導下迅速擴張。有學者提出了“算法即權力”的主張,如英國學者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強調:“在一個媒體和代碼無處不在的社會,權力越來越存在于算法之中[4]。”首先,算法本身就是一套運算規則,能夠指定規則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加之計算機語言的高度復雜性,這決定了算法只能是部分人享有的“權力”而非人皆有之的“權利”。其次,算法長期被籠罩在數字神話的光環之下,具有高度的權威性,表現為一種“軟權力”。再者,算法的無處在讓人日益“透明化”,在無形之中形成了技術時代的“全景監獄”,讓人被動地被馴化。
算法技術通過工具性促逼和權力性促逼不斷擴張,實質是一種工具性的合目的論的擴張。海德格爾認識到了技術的“解蔽”并非是流失于不確定性,而是處處得到保障和控制。而控制、保障,正是人們使用算法技術的目的,使算法成為了合目的論的產物。在工具與權力的“促逼”之下,算法成為了“集置”,產生了新的技術秩序并規定著存在者的存在狀態。
3 遮蔽:算法技術的風險
技術是人類認識真理、把握規律、改造世界的重要中介,海德格爾認為技術是一種特殊的“解蔽”。海德格爾則將開放領域中的“無蔽”視為真理,“技術是一種解蔽方式”[3]。同時,他認為現代技術在進行強制“解蔽”的同時也造成了“遮蔽”。在現代技術的“集置”中,“人往往走向了一種可能性的邊緣……由此就鎖閉了另一種可能性”[2]。現代技術帶來的危險,就是“在一切正確的東西真實的東西自行隱匿了”[2]。簡言之,就是現代媒介技術形成了“被中介的真理”,真理被“遮蔽”了。
在這個“媒介即訊息”的時代,算法技術毫無疑問也在形成一種“遮蔽”,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層面:
第一,算法“遮蔽”了人們對于媒介的反思。“追問乃思之虔誠”[2],但是人們長期對技術萬能、技術中立的追求已經形成了“技術/數字神話”。人們不假思索地接受算法技術傳遞的信息,認為中立客觀的算法技術的輸出結果是“正確的”。技術規定著人們的思維方式,算法時代的人們往往以算法化的思維去看待算法,關心的只是算法的結果正確與否、算法的效率如何提升。這在海德格爾看來都是一種“遮蔽”,因為這種思維未能觸及到技術中立主義的真理觀根本——相合性。海德格爾認為追問技術本質應該在與技術領域由親緣關系但有本質不同的藝術領域進行,因為算法技術追求的是一種至高無上的確定性、必然性,而藝術則是追求可能性的代表。無限的可能性,才是人應有的存在狀態。
第二,算法“遮蔽”了真理。算法具有定量化、精確化優勢從而能夠揭示真理,這是符合常識的。但是海德格爾認為現代技術正在成為對真理的“遮蔽”,算法也不在例外。這主要由于海德格爾對傳統形而上學真理觀的顛覆。其一,對于真理與非真理的顛覆。傳統觀念認為真理的對立面是謬誤,人類認知真理的過程就是拋棄謬誤的過程。但是,海德格爾并不認為“非真理”就是謬誤,而是仍然處在晦暗之中、更為原始的神秘之地,他稱之為Gehemnis。而該詞的詞根heim在德語中是“家”的意思。在技術時代,人們把數學計算的正確結果視為真理,反之就是謬誤。這就使得算法技術正在淪為一種強制性、唯一的“解蔽”,這就“遮蔽”了其他的“解蔽”的可能性,甚至遮蔽了真理的原初的源泉。其二,對于相合性原則的顛覆。海德格爾反對傳統形而上學所認為的“真理是知識和它的對象的一致”[5]的相合性原則。他所問及的是“當我們問及某事物是否是真實的、什么是真實的、什么是真理等問題時,心中所想的東西”[6]。海德格爾注意到了技術時代的真理中介化現象,“真實”與“正確”不斷分離。海德格爾認為真理應該是開放無蔽領域的“真實”,而傳統真理觀只是一種經驗主義的“正確”。算法技術的輸出結果毫無疑問是“正確”,但并不一定真實。因為算法模型貫徹了設計者自身的意志和認識,必然在潛意識中忽略某些或大或小的因素,這就導致算法只是對真實的不完全性“擬態”,即中介化的真理。此外,真理的相合性是與“經驗”相符,但是算法技術的個性化推薦機制正在塑造一個極其多樣的信息環境,這使得每個人的客觀經驗都不一樣。現實生活中也從來不乏有將算法傳播的推薦內容作為“客觀標準”的現象,如此龐雜的“正確”實際上構成了對“真實”的擠壓。
第三,算法“遮蔽”了“存在”。存在問題是海德格爾哲學的核心問題,但是海德格爾認為存在是最普遍的、不可定義的、自明的概念,只能通過存在者去把握它。海德格爾認為,人的存在本性就是“去存在”,即人并非按照某種先在的模板去自我實現,人的本質就是成為自己,人始終是指向未來與可能性的存在。“去存在”人只有處在“本真狀態”才能使存在顯現。
海德格爾則將語言置于人的存在論地位,做出了“語言說話”的論斷,認為“語言是最切近人的本質的”[7]。海德格爾并不將語言看作純粹的交流媒介,而是存在得以顯現的場所,語言規定著人的本質。但是他也提出了人這一“此在”的自始就已“沉淪”,即害怕可能性的境域,混跡于蕓蕓眾生之中。此在以“雜然共在”的沉淪狀態來逃避它自己的存在,不斷把自己交付給“世界”,為常人所宰治[8]。算法用數據和計算營造了更加龐雜的“常人世界”,人越來越依賴于并傾向于以他人的話語進行表達。算法傳播形成的信息環境再次環境化,讓人們尋到了所謂“共同標準”,加劇了人的“雜然共在”。此時“語言說話”的主體就不再是人本身而是算法構建出的虛無縹緲的“常人”。算法技術增加了此在逃避的機會:逃避自我的存在,逃到大家那里去,從而使自己淪落為非本真的存在。
4 結論
從海德格爾哲學思想出發,算法作為現代技術的新發展,同樣未能擺脫“集置”的本質,它規定著某一先天存在的技術秩序,將人對象化并降格為有用的“物”。而算法能夠如此廣泛地運用并滲透入日常生活之中,其擴張方式則是依賴于技術與權力的“促逼”。而“促逼”的后果就是帶來了風險,算法在進行“解蔽”的同時也形成了“遮蔽”:算法的“數字神話”無形之中遮蔽著人們對于媒介的反思,算法也遮蔽了真理,同時也遮蔽了本應面向未來與可能性的人的本真狀態——“存在”。
但是,海德格爾其實并不是一個反技術主義者或復古主義者。他并不認為我們在批判技術的同時需要逃避它,也并不懷念著人類歷史上的某個“黃金時代”。海德格爾并不能給我們解決算法時代的諸多問題提供具體方法,但是他的反思與追問卻給我們提供了可能的救贖道路。
參考文獻
[1]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胡菊蘭.走向媒介本體論[J].江西社會科學,2010(4):249-254.
[2]馬丁·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M].孫周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3,12,16,25,26,37.
[3]海德格爾.存在的天命:海德格爾技術哲學文選[M].孫周興,編譯.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8:144,140.
[4]Lash,Scott.“Power after Hegemony:Cultural Studies in Mutation·”Theory,Culture & Society,2007,24(3):55-78.
[5]康德.純粹理性批判[M].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4.
[6]戴維·J,貢克爾,保羅·A·泰勒.海德格爾論媒介[M].吳江,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9:81.
[7]馬丁·海德格爾.在通向語言的途中[M].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1.
[8]紀忠慧.高價值言論的法理與哲理[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0,42(5):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