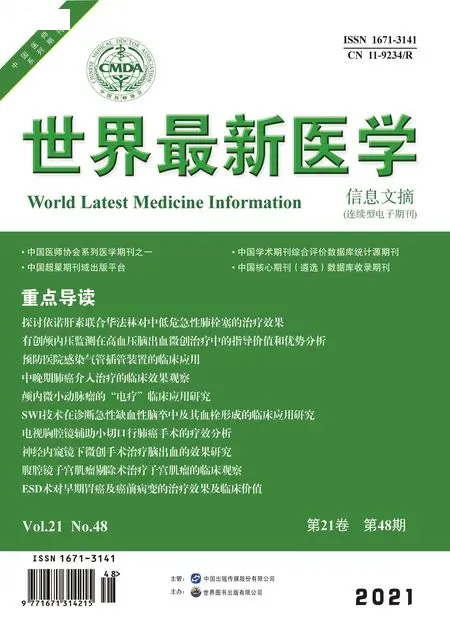觀察早發型與晚發型新生兒敗血癥臨床特點及病原學
郭映龍,劉雪嵐,陳佳佳
(揭陽市人民醫院,廣東 揭陽 522000)
0 引言
新生兒敗血癥具有較高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據調查發現,出生體質量越低的新生兒發病率越高,根據敗血癥的發病時間將患兒分為早發型敗血癥患兒和晚發型敗血癥患兒,臨床發病率分別為2%~3%、4%。然而,因為敗血癥的臨床表現不典型,患兒缺乏典型癥狀,臨床上容易出現漏診[1]。通過分析早發型敗血癥和晚發型敗血癥新生兒的臨床資料,對比兩型敗血癥的臨床表現、并發癥、實驗室檢查指標、病原菌分布及主要病原菌耐藥情況的差異,可以更好的為臨床早期診治及合理用藥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擇取揭陽市人民醫院75例確診為新生兒敗血癥的患兒,入組時間在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據發病時間將75例患兒分為早發型組(29例)和晚發型組(46例)。早發型組,男18例,女11例;平均胎齡35.77周。晚發型組,男34例,女12例;平均胎齡35.23周。兩組新生兒敗血癥的患兒的資料相比較,無顯著差異性,P>0.05。
1.2 方法。采用回顧性分析法,對75例新生兒敗血癥患兒的資料數據、并發癥、感染指數和病原學情況開展比較[2]。
1.3 觀察指標。①對比兩組臨床并發癥,包括DIC、感染性休克、顱內感染、多器官功能損害。②對比兩組感染指標數據,包含白細胞計數、血小板計數、C反應蛋白、降鈣素原。③對比兩組葡萄球菌耐藥性情況,包括青霉素、苯唑西林、紅霉素、克林霉素、慶大霉素、環丙沙星、復方新諾明[3]。④對比兩組腸桿菌耐藥性,包括阿莫西林/克拉維酸、頭孢呋辛、頭孢西丁、頭孢曲松、頭孢他啶、頭孢吡肟、左氧氟沙星、復方新諾明[4]。
1.4 統計學處理。數據利用統計學軟件SPSS 23.0進行處理,以(均數±標準差)表述計量資料,以(%)表示計數資料,組間差異性分別采用t檢驗與卡方檢驗。統計學意義存在,P<0.05。
2 結果
2.1 對比兩組新生兒敗血癥的患兒的組間臨床并發癥。早發型與晚發型新生兒敗血癥的患兒并發癥總率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對比兩組新生兒敗血癥的患兒的組間臨床并發癥[n(%)]
2.2 對比兩組新生兒敗血癥的患兒的感染指標數據。早發型與晚發型新生兒敗血癥的患兒的白細胞計數、血小板計數、C反應蛋白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降鈣素原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對比兩組新生兒敗血癥的患兒的感染指標數據(±s)

表2 對比兩組新生兒敗血癥的患兒的感染指標數據(±s)
2.3 對比兩組新生兒敗血癥的患兒的葡萄球菌耐藥性情況。早發型患兒出現2例葡萄糖球菌耐藥,晚發型患兒出現7例葡萄糖菌耐藥,早發型和晚發型葡萄球菌耐藥性情況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對比兩組新生兒敗血癥的患兒的葡萄球菌耐藥性情況[n(%)]
2.4 對比兩組新生兒敗血癥的患兒的腸桿菌耐藥性。早發型患兒出現9例腸桿菌耐藥,晚發型患兒出現18例腸桿菌耐藥,兩組患兒頭孢呋辛、頭孢西丁、頭孢曲松對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阿莫西林/克拉維酸、頭孢他啶、頭孢吡肟、左氧氟沙星、復方新諾明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對比兩組新生兒敗血癥的患兒的腸桿菌耐藥性[n(%)]
3 討論
新生兒敗血癥是細菌侵入血液循環,在血液中繁殖,生成大量的毒素,導致的全身感染,若癥狀嚴重,會威脅生命健康[5]。新生兒的體質量低,并且身體各個器官發育不完善,免疫系統不健全,容易提升疾病的風險。新生兒容易出現溶血,影響肝臟酶活性,影響肝臟對膽紅素的攝取,降低結合能力。在此次研究中發現,病原學特點中,病原菌對于青霉素的耐藥性較高,主要是因為抗生素使用不規范導致,臨床上為降低抗生素的敏感性,需要合理應用抗生素。早發型敗血癥患兒建議使用第三代頭孢菌素治療,結合血培養結果調整抗生素使用。晚發型敗血癥患兒,需要提升臨床重視程度,該類患兒具有較大的特異性,需要提升臨床警惕性,嚴密監測病情變化,做好感染控制,避免病情進展。
據本次研究結果顯示,早發型敗血癥與晚發型敗血癥患兒白細胞計數、血小板計數、C反應蛋白計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早發型敗血癥患兒降鈣素原高于晚發型患兒,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頭孢呋辛、頭孢西丁、頭孢曲松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綜上所述,早發型敗血癥患兒與晚發型敗血癥患兒的臨床特點和病原學分布具有差異,需要根據兩種類型的敗血癥特點,對患兒的初期病情進行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