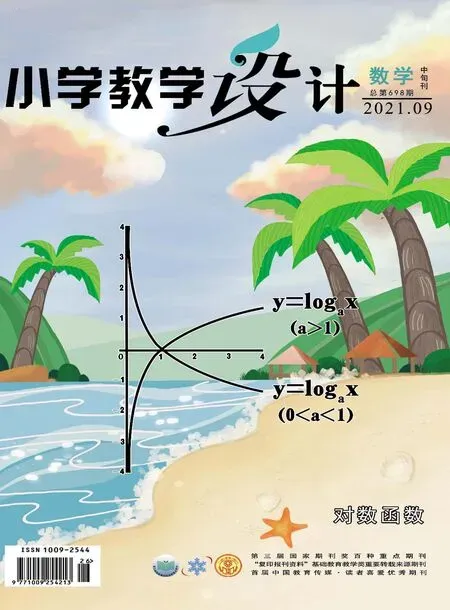三種顏色就是三種可能嗎
文|朱榮武
【問題凝視】
在四年級上冊“可能性”新知識學完后的練習中,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會出現這樣的錯誤:
問:袋子中裝有1個紅球、2個白球和3個黃球。從中任意摸出一個,摸出的可能結果有幾種?
答:3種,紅球、白球和黃球。
更有甚之,將這一問題推到成人之中,出錯的人也占大多數。
袋子中球的顏色只有三種,從中任意摸出一個,為什么摸出的可能結果不是三種呢?不是三種,那該是幾種呢?面對這樣的錯誤,教師該何去何從呢?
【成因透視】
一、生活經驗負遷移
生活中,顏色是區分不同事物或同類事物不同屬性的常用標準,學生對此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并應用嫻熟。比如黑色和白色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顏色、綠旗和綠旗是同一種顏色的旗子;再比如“紅燈停綠燈行”的規則中不同顏色代表的不同行為等。顏色不同即種類不同,這一認知學生確信無疑。因此,在上述問題情境中學生堅決認為“摸出的可能結果有3種”也在情理之中。同時,相關的學習活動也在無形中強化著學生的這一判斷視角。例如(如下圖),可能摸出的無外乎兩種顏色的球——紅球和黃球。

二、核心概念建構不準
義務教育階段涉及的概率內容都屬于古典概型,即在事件發生的結果有限且等可能的前提下,若所有可能出現的結果數為n,事件A實際發生的結果數為m,那么事件A發生的概率為。由此看定義概率必需兩個關鍵數據——所有可能出現的結果數n和事件發生的結果數m。《數學課程標準(2011年版)》對第二學段隨機現象發生的可能性雖未作“定量描述”的要求,但要求“感受隨機現象結果發生的可能性是有大小的,能對一些簡單的隨機現象發生的可能性做出定性描述”。這里,描述的前提仍是清楚地知曉“事件可能出現的結果數”,但相關的教學活動卻未能實現對這一核心概念的準確建構。比如例1后的“試一試”(如下圖),盡管教材有意引導學生認識可能發生的結果數為“2”——“這個紅球和那個紅球”,但由于情境內涵不充分,因此學生仍然是通過顏色來做出判斷——“因為只有一種顏色即紅色,所以摸出的一定是紅球”。學生雖然經歷了相關活動,但始終是在數學本質的邊緣游離,核心概念尚未建立。相反,這也從另一方面強化了學生依據“顏色”判斷種數的負面經驗。

【出路審視】
一、立足生活經驗提升數學理解,修正認識偏差
“所有的學習都涉及到原有經驗的遷移……用先前經驗去建構理解,學生也會誤解新信息……教師可以通過幫助學生使其思維可視化來糾正錯誤并鼓勵學生超越具體問題去思考,了解問題的各種變化,改變他們的原初概念。”因此,教學中要正視和尊重這些經驗,準確甄別、合理利用,恰當組織教學活動,引領學生在比較、反省、順應、重構等活動中獲得新的發展。“不同的顏色即是不同的種類,有幾種顏色就有幾種可能”,這些經驗在學生頭腦中根深蒂固、深信不疑。針對這一學情,一方面需要創造機會讓學生充分釋放“根據經驗表達交流”的過程;另一方面要基于上位知識的數學本質引領學生看到不一樣的“結局”,讓認識過程和認識結果上的“矛盾”引發學生的深思,并在“有意義接受”的過程中實現從生活概念向數學概念的蛻變,最終獲得數學理解——判斷可能的結果種數不是根據顏色種數而是根據球的個數。有幾個球,任意摸出一個球就有幾種可能。
二、多層建構古典概型感悟本質,重塑認知結構
古典概型本質上是一種定義概率,是在理想化的背景下來研究的,即如果事件可能出現的結果數為n,那么每個結果的可能性的大小都是。比如,袋中有5個球,從中任意摸出1個球,摸到的必然是這5個球中的1個,每個球被摸到的可能性就是。因此不管球的顏色有幾種,事件可能出現的結果數就是5,即球的個數對應的就是可能出現的結果數。鑒于學生“頑固”的生活經驗干擾,怎樣讓學生從依據“顏色種數”確定“可能出現的結果數”轉變到依據“物體個數”來確定“可能出現的結果數”,并認同其合理性進而接納這一“標準”便成為教學活動的關鍵。教學中可以采用由簡到繁的策略導引可視化思維,先研究簡單的“單色”古典概型,再研究稍復雜的“多色”古典概型,讓學生在多層次的判斷、表達、比較和抽象等思維活動中逐步突破“顏色干擾”,感悟古典概型的本質,掌握確定“事件可能出現的結果數”的方法,在“順應”的思維活動中形成新的認知結構。
【片斷重構】
片斷一:單色古典概型
1.激活經驗,暴露真實思維。
教師呈現裝有2個大小一樣的紅球的袋子,問:從中任意摸出一個球,可能摸出什么球?
生:摸出的一定是紅球。因為袋子中的球全是紅球。
生:是的。雖然袋子中有2個球,但都是紅顏色的,所以無論摸出哪個球都是紅球。
師:那你們覺得從袋子中任意摸出一個球,可能摸出的結果有幾種?
生:1種,紅球。
2.逼近本質,引發思維碰撞。
教師將袋中的2個紅球分別呈現出編號后,問:這兩個球和剛才的球比,有什么變化?
生:剛才的2個球沒有編號,現在2個球都有了編號。
生:球還是原來的那2個球,就是多了編號。
師:是的。這里球的顏色、大小等都沒變,就是多了編號,就好比每個球都有了自己的名字,這樣就好區分這兩個球了,分別是1號球、2號球。咦!現在從中任意摸出一個球,可能摸出的結果有幾種?
生:還是1種,紅球。
生:也可以說是2種。
師:現在出現了不同意見。同學們都來猜一猜:這位同學認為也可以說是2種,他可能是怎樣想的呢?
生:他是想可能摸出1號球,也可能摸出2號球,所以是2種。
生:我不同意!無論是摸出哪號球,都是紅球,結果還是1種。
生:我覺得從顏色上來看的話,是1種可能。但實際摸的話,可能摸到1號紅球,也可能摸到2號紅球……
師:大家說的好像都有道理,究竟可能摸出的結果有幾種呢?
(學生開始議論紛紛,但還是拿不定主意)
師:雖然這兩個球顏色大小都相同,但它們還是有區別的兩個球。任意摸出一個的話,可能是1號紅球,也可能是2號紅球,所以在數學上我們認為這時可能摸出的結果有2種。這時要從個數上來判斷而不是從顏色上來判斷。
片斷二:多色古典概型
1.遷移說理。
教師呈現裝有1個白球、2個黃球、3個紅球的袋子,6個球上分別隨機寫有①~⑥六個編號。問:從中任意摸出一個球,可能摸出的是幾號球?有幾種可能的結果?寫一寫。
生:有6種可能的結果,因為從1號球到6號球,每一號球都有可能被摸到。
師:現在將這些編號去掉。還是從中任意摸出一個球,有幾種可能的結果?
生:還是6種,因為6個球中每一個球都有可能被摸到。
師:為什么不是3種呢?
生:因為雖然是3種顏色,但一共有6個球,就應該是有6種可能。
生:同一種顏色的球有幾個算幾個。比如2個黃球雖然顏色相同,但還是有區別的2個球。
2.類比歸納。
(1)教師將袋子中的6個球分別變為白、黃、紅、藍、綠五種顏色和白、黃、紅、藍、綠、紫六種顏色,問:從中任意摸出一個球,有幾種可能的結果?
生:都是6種。因為雖然顏色的數量變了,但球的總個數沒變。
(2)教師呈現裝有2紅、2綠、3藍7支鉛筆的袋子,問:任意摸出一支,有幾種可能的結果?
生:7種。7支鉛筆每一支都有可能被摸到。
(3)教師呈現紅桃A、紅桃2、紅桃3、黑桃4四張牌,然后背面朝上打亂次序。問:從中任意摸出一張,有幾種可能的結果?
生:4種,分別是紅桃A、紅桃2、紅桃3、黑桃4。
3.抽象概括。
師:通過以上的學習,你有什么發現嗎?
生:有幾個物體,任意摸出一個就有幾種可能。
生:判斷可能摸出的種數不能看顏色,因為顏色和大小都相同的物體還是有區別的不同物體。
本例中,學生出錯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以顏色作為分類標準的先前經驗和對概率知識的未知。但細思之,學生此時已經具有了關于概率的直觀經驗和直覺感受,其對相關結果的判斷正是基于這種直覺和經驗進行理解、建構的“正常行為”,只不過這種直覺、經驗在當下有悖于數學知識現實而已。事實上,在學生漫長的數學學習歷程中,類似的“用先前經驗去建構理解而誤解新信息”的“正常行為”很多,比如學生根據乘法分配律模型“(a+b)×c=a×c+b×c”發現“(a+b)÷c=a÷c+b÷c”是對的,于是認為:因為“a×(b+c)=a×b+a×c”所以“a÷(b+c)=a÷b+a÷c”等。作為教師,一定要尊重和保護學生這種純真大膽的建構行為,并據此展開深度溯源,透視本質,尋求解決問題的出路,創造條件讓學生在深度理解的基礎上實現對已有經驗的改造和已有認知結構的重塑,在基于先前經驗的文化實踐過程中獲得知識、觀念、思想方法等全方位的熏陶。當然對教師而言,上例帶來的啟示是教師仍需要再學習,以彌補上位知識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