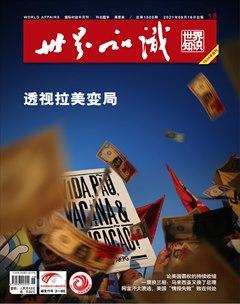拉美經濟:如何避免“被邊緣化”
張勇
受疫情沖擊,拉美遭遇12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疫情沖擊將顯著改變拉美地區經濟增長所面臨的內外部環境。展望后疫情時代,拉美國家將在致力于解決結構性脆弱的過程中尋求經濟復蘇和可持續發展之路。
疫情沖擊暴露結構脆弱性
歷史表明,經濟波動是拉美地區的顯著特征。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自2011年起,拉美再次陷入近十年的經濟下行周期。2020年的疫情沖擊更是加劇了周期衰退的程度。根據拉美經委會數據,2014~2019年,拉美經濟年均增長率僅為0.3%,創有史以來增長最弱的六年;2020年地區經濟衰退6.8%,也創下1900年以來經濟最差的紀錄。從世界范圍來看,拉美地區不僅是新興市場中遭受疫情沖擊最嚴重的地區,而且被世界經濟邊緣化的趨勢正在顯現,其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2011年的8.3%降至2020年的5.7%。
與國際金融危機相似,本次疫情沖擊主要通過對外部門(貿易和投資)、金融市場、大宗商品市場等多個渠道傳導并影響拉美經濟。在貿易投資渠道,拉美經委會數據顯示,2020年,拉美地區出口、進口和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分別下降10%、16%和34.7%。在金融市場渠道,影響主要體現為貨幣貶值和主權債務評級下降。2020年前十個月,拉美地區17國的貨幣平均貶值16.3%;2020年,拉美21國的主權評級被認定為實質性風險或投機等級。在大宗商品市場渠道,2020年初至2021年5月,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指數經歷“V”型走勢。在價格暴跌階段,貿易環境的惡化直接削弱了拉美能源資源出口國的出口收入和財政收入。
鑒于拉美國家經濟結構存在差異性,各國受不同渠道影響的程度有所不同。以資源能源出口為主的南美洲國家受到大宗商品價格暴跌的沖擊最大。以毗鄰美國市場以及客戶加工業為主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國家面臨貿易需求萎縮以及北美價值鏈中斷的雙重壓力。而以離岸金融業和旅游業為主的加勒比國家則遭受資金外流和旅游人數大幅縮減的雙重打擊。有數據顯示,2020年,南美洲、墨西哥和中美洲、加勒比地區經濟衰退分別為6.3%、8.1%和7.5%。與此同時,按照工業部門生產要素集中度分類,實體部門經濟顯著分化:勞動密集型部門表現最差,技術密集型部門居中,自然資源密集型部門則表現出較大的彈性。
疫情對拉美經濟造成的影響超出預期,主要歸因于該地區長期積累的結構脆弱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生產結構的脆弱性。拉美地區的出口以初級產品為主,受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影響很大;而且,參與全球價值鏈程度有限,無法享受國際分工紅利,對生產多元化不利。第二,財政和國際收支的脆弱性。拉美地區持續存在的“雙赤字”顯然增加了經濟風險。財政赤字的擴大容易引發主權債務危機,而經常賬戶長期赤字容易引發國際收支危機。第三,社會結構的脆弱性。地區的非正規就業、人口老齡化和社會不平等現象加劇了外部沖擊的程度。
疫情加劇經濟格局調整
全球經濟格局變革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已現端倪,而本次疫情沖擊更加劇了這種調整趨勢。就拉美地區而言,具有長期深遠影響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首先,全球價值鏈調整將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疫情沖擊對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的顯著影響是,全球生產網絡的“近岸生產”(nearshoring)趨勢加強。換言之,處于全球生產網絡的跨國公司更傾向于將供應商布局于更接近終端市場的位置。這種調整將加快拉美地區區域一體化進度,從而使其較深融入北美價值鏈。而拉美國家能否承接全球價值鏈的新布局,通常要受政局穩定及政府治理能力、勞動力市場競爭力、基礎設施完善度、技術準備度等多重因素影響。有鑒于此,拉美國家有必要從貿易一體化、生產一體化、基礎設施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四個方面入手,推進區域內經濟一體化程度。
其次,數字經濟興起有利于生產結構轉型。數字經濟不僅是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的新動力,而且在應對疫情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明顯。疫情期間,與數字平臺相關的活動持續快速增長,不同類型規模的公司越來越多地使用數字技術。鑒于拉美地區中小微企業數字化水平較低,拉美國家需要制定公共政策,鼓勵企業在供應鏈、加工、制造、運營以及分銷渠道中使用數字技術。與此同時,拉美國家也應在數字基礎設施、數據保護和數字安全、競爭和監管政策以及數字稅收方面加強區域內外合作。
最后,社會結構必須匹配經濟結構的變化。拉美發展歷史表明,社會結構轉型相對于經濟結構的滯后會快速放大危機所造成的沖擊程度,這種沖擊可能以抗議、暴亂等社會運動形式反作用于經濟和政治,從而導致更大的破壞力。本次疫情充分暴露了地區中等收入階層的脆弱性。拉美經委會數據顯示,2008~2019年十余年間,拉美社會結構出現收入分層固化、社會流動停滯現象,這也成為2019年底拉美地區出現新一輪社會抗議浪潮的導火索。而在疫情沖擊下,拉美地區社會階層出現明顯向下流動趨勢,中等收入階層占人口比例從2019年的41%降至2020年的37%,倒退至2008年的水平,這表明有更多的人陷入貧困。鑒于此,在中長期內,拉美國家必須更新發展戰略,促進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
后疫情時代增長動力來源
展望后疫情時代,拉美地區經濟增長仍受到內外環境因素的影響。因此,除了依賴大宗商品價格反彈、全球貿易投資需求恢復以及全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等外部因素改善外,拉美經濟增長的內部動力主要來自以下三個方面。
短期而言,政策空間決定需求側增長潛力。為抗擊疫情,拉美國家都實施了不同程度的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然而,限于財政的脆弱性和國內金融市場深化不足,兩者都面臨嚴峻的考驗。財政政策方面,拉美地區中央政府的債務總額占GDP的比例高達79%,這種高債務水平減少了財政政策運作的空間。貨幣政策方面,為應對持續走高的通脹預期,部分拉美國家提前加息,這與歐美發達國家實行的量化寬松政策形成反差,容易造成金融市場的波動。同時鑒于拉美國家國內金融深化不足,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容易受阻。因此,短期內,拉美地區需要增加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靈活性以刺激需求增量。
拉美地區以初級產品為主的生產結構暴露了其經濟的脆弱性。圖為2017年3月13日,在巴西圣保羅蒂普蘭碼頭,裝卸工人正在將大豆裝載到船上,準備運往中國。
中期而言,產業結構調整力度決定供給側質量。實踐表明,拉美地區初級產品專業化、去工業化和經濟非正規化增加了面對外部沖擊的脆弱性。農業和礦業的初級產品專業化使得拉美經濟易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影響,同時也阻礙了技術進步,影響了工業化進程;去工業化趨勢將影響拉美國家綜合競爭力的提高;非正規性就業的存在拖累了服務業現代化的步伐。鑒于此,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是提高增長質量的有效途徑。尤其是,再工業化會成為適應全球價值鏈調整、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關鍵環節。
長期而言,結構性改革決定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程度。拉美地區的發展問題不是要素積累問題,而是生產率水平低下且生產率增長乏力問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主要來自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兩個方面,而結構性改革恰好能夠滿足這兩個方面的要求。就具體措施而言,拉美地區國家可通過加強人力資本投資、促進技術、管理和組織的創新提高生產率;通過貿易投資便利化改善營商環境;通過完善反周期宏觀政策框架增加經濟韌性;通過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加速社會融合;通過提高行政效率、加強反腐機制完善政府治理能力,等等。簡言之,唯有切實推進結構性改革,拉美國家才能在長期內提高經濟潛在增長率。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員、巴西研究中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