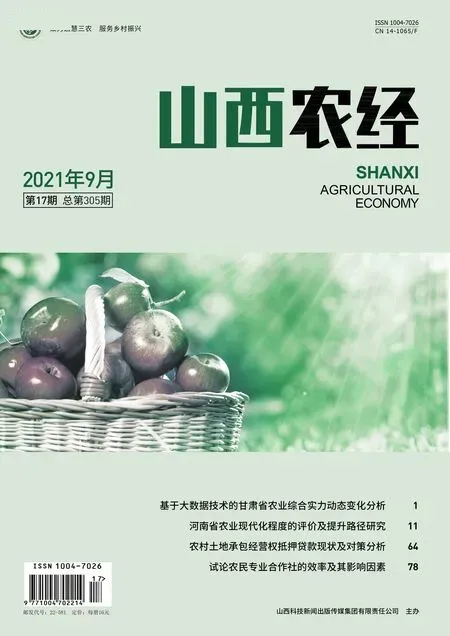日本“農業婦女項目”的實施狀況及對中國的啟示
□周瑞婷
(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暨哲學系 廣東 廣州 510275)
1 “農業婦女項目”的實施背景
“農業婦女項目”是2013 年在日本政府鼓勵下,由婦女農民和企業共同合作推出的新型商品和服務項目。該項目旨在促進日本婦女在農業、林業和漁業以及振興農村社區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以幫助廣大農業婦女成為日本“農業第六次產業化”的推動者[1]。
日本之所以推動這一項目,與現當代日本農業人口和產業發展動態息息相關。自古以來,日本就是以家庭作業為單位生產的小農社會。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20 多年間,日本仍有超過1/2 的人口居住在農村和從事農業生產,并且這些人口多為“兼業農民”。這些“兼業農民”在農忙之時從事農業生產,在農閑之時則“外出打工”。隨著日本經濟的復蘇并進入高增長期,村里的年輕人紛紛離開農村前往城市就業,導致農業逐漸后繼無人。
隨著城市人口的上升以及農村家居環境向城市化發展,城市周邊的農村成為了城市郊區住宅區。城市空間的擴張和交通路線的延展使更多農民不再愿意從事農業生產或當“兼業農民”,而傾向于長期留在城市工作[2]。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的農業普查和農業結構動態調查,進入21 世紀以來,日本農業人口急劇下降,并陷入老齡化的困境[3]。
此外,在日本農業史上,婦女是農業的主要推動者。隨著現代日本經濟社會和產業結構的變化,越來越多的農村男性轉向其他工作,這直接導致婦女在家庭農業中的負擔急劇增大。隨著社會生活和關系的現代化變遷,許多婦女不喜歡艱苦的農業工作,不愿意固守在農村保守的人際關系之中,這也使得婦女不愿嫁給農民、不愿待在農村。在日本的許多農村地區,嫁娶短缺和婚姻匱乏已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4]。婦女勞動力的匱乏和流失,對近年急速衰落和原本依靠婦女勞作的日本農業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
由表1 可以看出,農業已經成為日本的夕陽產業,而農業人口的急速萎縮加速這一夕陽產業走向衰亡。2015—2020 年,日本農業婦女人口隨著日本農業人口的急速下降而下降,而且農業婦女人口下降比例為27.9%,高于農業人口下降比例(22.4%)。

表1 日本農業勞動力統計
為此,在日本政府鼓勵下,農業婦女團體聯合有關企業從2013 年開始推出“農業婦女項目”,試圖通過社會資本的支持,借助互聯網時代新興技術和產業的力量,幫助農業婦女發揮作為日本農業發展推動者的力量,進而帶動日本農業經濟復興。
2 “農業婦女項目”的社會理念及其傳播
對負責“農業婦女項目”的決策者——農林水產省管理局農業、林業和漁業部以及社會有關企業而言,推行該項目需要有一個較大的社會生產、消費觀念和性別觀念的轉變。一般來說,日本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主要是男性,但事實上,女性農民約占農業人口的1/2。而且,隨著現代農業機械化、信息化的推進,婦女參與農業生產與管理,且對經濟收入及其增長的影響愈來愈大。另外,現代日本女性消費主體性的確立,以及前衛的消費觀念和強勁的消費能力(尤其是網購能力),理應在根本上決定女性在各行業、各產業的主體地位。
因此,從日本農林水產省的角度看,其所鼓勵推行的“農業婦女項目”,不僅是一項產業(農業)發展工程,也是一項關乎社會觀念轉變的文化工程[5]。從日本社會企業的角度看,其投入物力財力支持推行的“農業婦女項目”本質上是開拓新型的農業生產和經營模式,意在幫助婦女農民將其想法實現于生產和經營之中,進行前所未有的農業新產品開發和服務。如此一來,就需要在農業經濟行業完成三大轉變:第一,提高婦女農民在社會和農業界的地位,改變日本社會對農業工作者和女性的歧視;第二,改變婦女農民固守生產鏈的意識,幫助其促進自身經營和管理能力的發展;第三,將“農業”添加到年輕女性的職業選擇之中,改變年輕女性及全社會對農業的偏見[6]。
然而,對日本廣大婦女農民而言,以上內容實質上是來自于官方和資方自上而下的單向度指導。至于如何理解“農業婦女項目”的社會理念、怎么將“農業婦女項目”的社會理念傳播開來,還得由日本廣大婦女農民有組織地進行。為了在與官方、資方合作及協作的過程中掌握主導權,日本各地婦女農民代表組建成立了“農業婦女項目促進會”,以聯系和組織日本各地婦女農民,共享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積累的智慧,以及協商與官方、資方商討項目有關的政策、技術、投資和利益分配等問題。
“農業婦女項目促進會”成立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向社會廣泛傳播婦女農民關于開展“農業婦女項目”的社會理念,使更多人了解農業婦女對社會的貢獻。從2013 年11 月開始,“農業婦女項目促進會”奔赴各地開展各種婦女參與農業生產經營的推廣活動,截至2020 年已舉辦了8 期,主要向社會各界傳播農業婦女是“生產力”“智慧力”“市場力”三位一體的社會主體及力量的理念。
所謂“生產力”,就是要擴大農業婦女生產力的潛力,將農業生產、銷售、經營和服務的產業鏈及業務變成自主事務,將與農業相關的各項服務納入“農業婦女項目”成員的福利范圍,以保障農業婦女發展農業事務。所謂“智慧力”,就是要發揮農業婦女在商業化社會中的獨特智慧,讓婦女成為市場經濟的生產主體和消費主力,鼓勵婦女農民開動自己的智慧進行產品、服務、信息的開發,結合婦女消費者的喜好去改進現有產品,使現代商業社會從生產至消費都烙上女性的智慧印記。所謂“市場力”,就是要建立一個屬于婦女自己的新型農業產品市場圈子,從產品開發至改進都著眼于迎合婦女的市場需求,以強化婦女在現代市場經濟的話語權和主導權,從而提高農業婦女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
3 “農業婦女項目”的實施經驗
經過多年的推廣和實施,日本“農業婦女項目”形成了一定的具體實施經驗。2013 年以來,除了“農業婦女項目促進會”的努力之外,與農業相關的各類企業、教育機構等也陸續加入到“農業婦女項目”合作中來,在發揮農業婦女的智慧、開發新商品和服務、培育未來農業婦女有生力量、提高農業婦女的存在感和地位、培養農業婦女的自主意識、發展農業婦女經營能力、增加農業婦女權益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
第一,在全產業鏈上引導農業婦女與社會企業進行合作。“農業婦女項目促進會”的組建成立就是要成為婦女農民與社會企業進行合作的媒介,并主要為婦女農民提供組織、合作指導和效益爭取的服務。目前,響應并參與了“農業婦女項目”的大型財團及企業已達37 家。通過與社會企業的合作,婦女農民也得以解決資金、技術和銷售等環節的難題,從而實現“雙贏”。
第二,借助與社會企業合作所取得的各方面支持,為婦女農民爭取良好的生產工作條件,包括開發婦女農民輕松使用的農具和農械、制造適宜婦女農民進行生產及其他業務的工作服、改善婦女農民進行生產的工作場所、提供托兒服務等。除了提供物質層面的幫助和支持以外,在“農業婦女項目促進會”協調下,參與項目合作的社會企業對婦女農民身心健康也投入了相當的資源支持。
第三,推進各高校及教育機構參與進來,為廣大婦女農民進行生產和經營提供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培訓。2015 年至今,經“農業婦女項目促進會”斡旋而參與進來的有東京農業大學、蒲田女子高等學校、東京家政大學、山形大學等7 所高校及教育機構。這些高校和教育機構不僅為農業婦女進行農牧園藝技術培訓的生產技能教育、農業經濟經營和管理的知識教育,而且還為農業婦女提供到農場實習、進行農業演講的機會[7]。
第四,促進“農業女子項目”活動的擴大和發展,開展國際合作和交流,以開拓國外市場。“農業婦女項目促進會”對內要求加快發展成員數量并成立地方團體,從而能夠有充足的力量開展幫助婦女農民就業、生產和經營的活動。“農業婦女項目促進會”通過聯系和動員各地婦女農民形成有組織地對外宣傳和銷售行動,參與各種國際博覽會,例如“農業婦女項目促進會”曾多次在香港舉辦以女性為主題的農產品展覽會,從而為日本婦女農民的農產品開拓國外市場[8]。
第五,幫助農業婦女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以提高農業婦女的社會能見度及社會地位。值得關注的是,以“農業婦女項目促進會”為行動單位和組織,日本農業婦女積極參與了社會食品安全的運作和監督工作,將相當一部分工作投入到從農產品生產、食材挑選及加工等各個環節,以確保全社會的飲食與健康安全。由此,日本社會也逐漸意識到農業婦女所能發揮的積極作用,并開始改變以往對農業工作者尤其是農業婦女的文化和制度性歧視。
4 “農業婦女項目”實施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農業婦女項目”實施主體不明,導致權責模糊。政府作為項目的提倡者卻未能提供及時、適時的政策支持,企業資方作為項目的物力財力支持者卻以利潤為根本目的(農業婦女權益為次),農業婦女作為項目的實施對象卻未能實現全面參與和投入。
第二,“農業婦女項目”仍缺乏全國性的政策認同和全社會的友好支持。盡管“農業婦女項目”經過8 年的發展,但在農業已成為夕陽產業、農業人口急速萎縮的背景下,難以調動來自國家持久的政策支持,更缺乏來自全社會的有生力量輸入——女性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拒斥仍是日本社會文化的主流現象。
第三,“農業婦女項目促進會”的組織性質和基本運作有待規范化。例如在資方和農業婦女的收益分配上,“農業婦女項目促進會”所扮演的角色不明、立場搖擺不定。防止自身變成資方控制農業婦女的工具,以及在資方和農業婦女的收益分配談判中防止變成資方的代言人,已成為“農業婦女項目促進會”自我發展的棘手問題。
5 “農業婦女項目”對中國鄉村振興的啟示
與日本一樣,中國女性在農村家庭中承擔著重要角色,在農業生產中約占1/2 的勞動力比例,因此農村女性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戰略中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與日本農業婦女所面臨的問題相似,中國農村婦女也面臨著各種問題和挑戰,包括勞動技能不足、受教育水平低下、家庭和社會地位不高、權利保障不到位、身心健康問題突出等。這些問題直接制約中國農村婦女在鄉村振興中發揮應有的巨大能量。日本“農業婦女項目”的實施所針對和要解決的問題正是這些,因此中國可從其實施經驗中獲取有益的啟示。
第一,提高婦女在農業經濟發展和鄉村振興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國可借鑒日本“農業婦女項目”社會理念的宣傳經驗,通過宣傳教育,讓全社會意識到婦女是農業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和主體性力量,由此提高農村婦女的家庭和社會地位,讓農民作為一個光榮職業而存在,以此鼓勵和吸引年輕女性投入到農業經濟發展中來。
第二,營造有利于農村婦女全面發展的社會文化條件和政策環境。鑒于日本政府的政策短板,中國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制定和頒布支持農村婦女發展的政策,而后在政策的貫徹和護航下,落實各項有利于農村婦女發展農業事業的措施。其中,尤其應包括動員相關企業、高等院校、教育機構等參與到對農村婦女發展的支持中來,為農村婦女發展農業提供資金、技能、知識以及醫療衛生等服務和支持。
第三,提升農村婦女扎根廣大農村的自信心和義務感。農村婦女對廣大農村缺乏鄉土向往和扎根意愿,是中日兩國共同面臨的社會問題。但不同于日本,中國農村一直是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鄉村振興戰略已成為中國國家戰略,這讓中國有底氣去直面農村發展不充分和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中國政府的有力支持下,廣大農村從基層行政、產業基礎、文化教育到社會公益等各方面迎來了全面現代化的發展機遇,給廣大農村婦女扎根和發展鄉土提供了信心,這是日本所缺乏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組織及動員能力。“種養加銷全產業鏈、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規劃部署,為廣大農村婦女營造了大有作為的廣闊創業和就業天地。因此,如何讓廣大農村婦女意識到和參與到這一戰略部署和發展規劃中去,鞏固其扎根農村和發展農村的義務感,成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一項重要課題。
第四,提供農村婦女參與農業事業及從中獲得權益保障的政治和組織保護。要營建政府、企業、農村婦女三方良性互動的關系與機制,明確各方權責,明確堅持生產經營效益和農村婦女利益的協調統一,在堅持黨和政府的全面領導下,幫助農村婦女成立與發展合法的集體組織,組織起來應對市場和資方的不利局面,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在中日農村婦女參與農業及其他各項社會經濟建設的過程中,不可否認一直存在被“擠出”權益分配場域的現象,這本質上是農村婦女的地位被忽視,農村婦女的權益意愿沒有得到尊重,農村婦女的權益保障受到侵害。對中國而言,以上這些現象若得不到重視及解決,將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造成巨大制約。為廣大農村婦女提供參與農業事業并從中獲得權益保障的政治和組織保護,是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把依法維護農民權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重要思想的貫徹落實。為此,全社會要逐漸轉變以“利益最大化”為行動邏輯的觀念,逐漸樹立效率理性和公平理性相統一的社會價值理念,以深層次的精神文明建設為維護農村婦女權益保駕護航,從而提高廣大農村婦女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并轉化為推動鄉村振興的不懈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