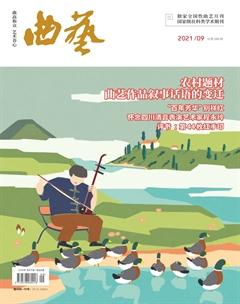四川揚(yáng)琴男腔的說、唱初探
周奕汐
筆者曾在重慶市曲藝團(tuán)有限責(zé)任公司工作3年,在團(tuán)期間,曾跟隨四川揚(yáng)琴國家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xiàng)目代表性傳承人陳再碧和重慶市市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xiàng)目代表性傳承人張紹鵬學(xué)習(xí)四川揚(yáng)琴老旦及男腔的演唱,并拜師于張紹鵬先生。其間,曾參與排練數(shù)十場、下鄉(xiāng)演出十余場、團(tuán)內(nèi)考核兩場,獲得了團(tuán)內(nèi)老師充分的肯定與鼓勵(lì)。在學(xué)習(xí)四川揚(yáng)琴男腔的過程中,筆者發(fā)現(xiàn)以下兩點(diǎn):第一,四川揚(yáng)琴的說、唱與四川方言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說唱與方言的關(guān)系);第二,說唱,這一詞充分顯示“說話”在四川揚(yáng)琴中的重要性(唱與說話的關(guān)系)。就此兩點(diǎn)關(guān)系,筆者通過自身學(xué)習(xí)的四川揚(yáng)琴選段《鳳求凰》《秋江》來展開探究,從而得出以下結(jié)論。
筆者曾以“四川揚(yáng)琴”為關(guān)鍵詞在中國知網(wǎng)上進(jìn)行查找,頁面顯示共有6頁、100余篇文章對“四川揚(yáng)琴”“揚(yáng)琴”進(jìn)行研究。有關(guān)“四川揚(yáng)琴”的論文70余篇。其中,在《四川揚(yáng)琴傳承人吳瑕口述史》(張強(qiáng))、《舞臺(tái)藝術(shù)的追夢人——夏銘鍾的情懷與擔(dān)當(dāng)》(王洲)、《時(shí)雨春風(fēng)嬌燕飛——記四川揚(yáng)琴國家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xiàng)目代表性傳承人劉時(shí)燕》(溫志航)、《新人吳瑕——青年四川揚(yáng)琴演員吳瑕訪談》(杜佳)中,主要以采訪的形式,對從藝者的曲藝歷程及成績做出了梳理與展示;《黃荊樹》 (秦淵)、《花香花鄉(xiāng)》(袁國虎)則是四川揚(yáng)琴的新曲目,并由點(diǎn)評人做出點(diǎn)評。
在有關(guān)曲藝家自身書寫的文章中,有“德派”傳承人劉時(shí)燕老師對四川揚(yáng)琴演唱的不同“潤腔”手法做出詳細(xì)說明(《四川揚(yáng)琴“德派”唱腔潤腔手法》),以及她自身對四川揚(yáng)琴的認(rèn)識(shí)(《我與四川揚(yáng)琴》)。一些文章,例如《淺析四川揚(yáng)琴音樂——大調(diào)一字腔》(張正)、《四川揚(yáng)琴大調(diào)一字腔分析研究》(王露),主要對“一字腔”進(jìn)行了分析。其他文章,便是針對四川揚(yáng)琴如何保護(hù)傳承、四川揚(yáng)琴如何進(jìn)行表演方式的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四川揚(yáng)琴演唱中一些技巧的藝術(shù)表現(xiàn)特色如何、四川揚(yáng)琴的發(fā)聲方法可以如何進(jìn)行改善等內(nèi)容進(jìn)行了研究。
一、四川揚(yáng)琴簡述及現(xiàn)狀
四川揚(yáng)琴又稱“四川琴書”,屬四川地方曲種。據(jù)傳,四川揚(yáng)琴約形成于清乾嘉年間,流傳于成都、重慶等城市。之所以名為“四川揚(yáng)琴”,是因此曲種以揚(yáng)琴為主要的伴奏樂器。舊時(shí),由揚(yáng)琴、京胡、三弦、碗碗琴、鼓板組成“五方”的陣勢,藝人也以生、旦、凈、末、丑分飾角色。現(xiàn)如今,成都的四川揚(yáng)琴“五方”樂器及分布為:揚(yáng)琴(居中)、漁鼓(左后)、檀板(右前)、三弦(左前)、二胡(右后)。在四川揚(yáng)琴的演出中,演員也可根據(jù)曲目需要,增減樂器。如在重慶市曲藝團(tuán)的四川揚(yáng)琴《鳳求凰》的表演中,就有阮、琵琶、鼓板、揚(yáng)琴、二胡、京胡作為伴奏樂器的組合;另外,在四川揚(yáng)琴《慈母心》中,也有二胡、鼓板、揚(yáng)琴、大阮、三弦等樂器組成的小樂隊(duì)組合,其中,揚(yáng)琴、鼓板為十分重要的,甚至可說是必不可少的樂器。
四川揚(yáng)琴講求“坐地傳情”,這是四川揚(yáng)琴這一曲種的特點(diǎn)之一。四川揚(yáng)琴的演員不穿角色服裝,因又要自操樂器,故只能通過面部的各樣表情塑造人物。“坐地傳情”的核心“傳情”,在于演員一般為坐唱,通過說白、唱腔、表演這三個(gè)主要手段,把故事內(nèi)容講出,把故事中人物的性格、情感表達(dá)出來。在筆者接觸到的現(xiàn)如今的四川揚(yáng)琴表演中,兩位主唱演員可根據(jù)情節(jié)內(nèi)容需要,進(jìn)行少量的走動(dòng)。
四川揚(yáng)琴的唱腔有大調(diào)、月調(diào)兩類,其中,大調(diào)為板腔體,月調(diào)為聯(lián)曲體。大調(diào)的戲劇性強(qiáng),適合表現(xiàn)較為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jié);月調(diào)的抒情性強(qiáng),適合表現(xiàn)較為婉約的故事內(nèi)容。
二、“說”之方言的“字正”
在“曲藝”這類藝術(shù)形式中,可以見到各地的文化形態(tài),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各地的方言。隨機(jī)打開“曲藝地圖”,可以聽到吳儂軟語的蘇州彈詞、河南話的河南墜子、北京話的京韻大鼓、粵語的粵曲、陜西話的陜北說書等方言曲種。毫不例外,四川揚(yáng)琴也同樣是以四川方言娓娓道來,吸引著無數(shù)觀眾。
(一)從《鳳求凰》說起
四川揚(yáng)琴《鳳求凰》是在四川揚(yáng)琴曲牌格律的基礎(chǔ)上而新編發(fā)展創(chuàng)作的曲目,它講述了漢代大才子司馬相如與大才女卓文君的愛情故事。四川揚(yáng)琴是為觀眾講述一個(gè)又一個(gè)故事,因此,相比民歌“自我感情”的抒發(fā),它的演唱篇幅普遍較長,四川揚(yáng)琴傳統(tǒng)曲目的篇幅時(shí)長可至1小時(shí)。但此篇曲目時(shí)長較短,只12分鐘左右。
《鳳求凰》開始處,便有一段司馬相如的說白:
臨邛山啊臨邛水,山水含笑迎我回,卓府相邀賓朋會(huì),帶酒留宿夜未歸。想我相如天涯漂泊,壯志未酬,久聞文君小姐才貌雙全,只恨無緣相見。哎!我何不去至琴臺(tái),彈上一曲,以解愁腸。
在曲藝中,念白一般指有韻的句子,說白則是人物的臺(tái)詞,有獨(dú)白和對白之分。在上段司馬相如的“白”中,第一句便是念白,后面為說白。筆者在學(xué)習(xí)此念白的過程中,師父十分強(qiáng)調(diào)此其中的“聲韻”。所謂“聲韻”,筆者在自己學(xué)習(xí)后所得出的理解是在把每個(gè)字的發(fā)音說到位的基礎(chǔ)上,還有一個(gè)說話音調(diào)的夸張,此夸張似是可以形成聲調(diào)的旋律。后面為說白,就更需要把人物感、人物所要表達(dá)的內(nèi)容表現(xiàn)到位。
那么,如何將念白的“聲韻”說到位呢?又如何將說白說明白呢?這便涉及四川方言的咬字發(fā)音。
從普通話的調(diào)值上看,第一句的拼音為:lín qióng sh n lín qióng shuǐ,sh n shuǐ h n xi o yíng wǒ huí,zhuó fǔ xi ng y o bīn péng huì,d i jiǔ liú sù yè wèi guī。用四川方音演唱時(shí),第一句的拼音為:lìn qiòng s n n lìn qiòng suì,s n suì h n xi o yìn euòhuì,zuò fù xi ng y o bīn pèng huǐ,d i jiù liù xǔ yě wěi guī。其中,紅色標(biāo)記處是四川方言中的不含翹舌音(但在發(fā)音時(shí),舌頭需稍微卷一些,否則全平舌影響發(fā)音聽感),藍(lán)色標(biāo)記處是不含后鼻音,橘色標(biāo)記處為改變了普通話的發(fā)音。在了解了四川方言的發(fā)音特點(diǎn)后,念白首先重要的一點(diǎn)是要將每個(gè)字說到位。且看第一句句首,臨邛山啊臨邛水(lìn qiòng s n n lìn qiòng suì),山水含笑迎我回(s n suì h n xi o yìn euò huì)。首先,要把“字頭說清”。正如此兩句中,“臨”字所發(fā)的“l(fā)”邊音要清晰,“邛”字所發(fā)的“q”、“山”字所發(fā)的的“s”、“笑”字所發(fā)的“x”等清輔音要讓它說清明,“啊”字所發(fā)的鼻音“n”要先進(jìn)入上顎,再把“n”說明白后歸向“”音。其次,要做到“字腹飽滿”。像“邛”“笑”中間的介母“i”發(fā)音時(shí),齒舌間要咬住,進(jìn)而再進(jìn)行“ong”“o”的收韻。最后,需要“字尾收韻”。在“臨邛山”“含”“迎”中,都有前后鼻音,這時(shí)要注意將前后鼻音“n”“ng”歸音進(jìn)鼻腔。在“笑”中,是以“o”來結(jié)尾,這時(shí)要注意把“o”說圓滿,口型也是從“”到“o”,最后收至“o”。筆者認(rèn)為,如此“字頭說清”“字腹飽滿”“字尾收韻”后,才是把字說明白了。這樣,觀眾也才能聽清。
接下來十分重要的一點(diǎn)是念白的“聲韻”。仍舊以第一句為例。臨邛山啊臨邛水(lìn qiòng s n n lìn qiòng suì),山水含笑迎我回(s n suì h n xi o yìn euò huì),卓府相邀賓朋會(huì)(zuò fù xi ng y o bīn pèng huǐ),帶酒留宿夜未歸(d i jiù liù xǔ yě wěi guī)。四川揚(yáng)琴演員說四川方言,那么,在念白時(shí),就得注意把地方語言的調(diào)值說明白;另外,還需要注重聲韻。例如,“臨邛水”三字在表1四川方言調(diào)值里都向下行走,在說時(shí),便是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行咬字、聲音、語氣等的夸張,它的整體感覺為向下落。在說“山”“相邀”“賓”“歸”等調(diào)值為44的平聲字時(shí),便可注意聲調(diào)向上的一個(gè)夸張,如此,既符合了它的調(diào)值走向,也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行了聲韻的處理。在說“笑”“帶”“夜”“未”等調(diào)值為214的字時(shí),便總能有一個(gè)小彎的處理,正像它的調(diào)值走向214一樣。在進(jìn)行第一句念白拆解分析后,可以發(fā)現(xiàn),正是因?yàn)槊烤湓挼恼{(diào)值富有變化,才有了一串連綿起伏、豐富多變的“念白”。
(二)從《秋江》說起
《秋江》為四川揚(yáng)琴傳統(tǒng)曲目,講述的是女主人公陳妙嫦,在秋江邊想乘坐艄翁的漁船追趕心上人潘郎的故事。在此,可注意一個(gè)演出時(shí)長現(xiàn)象。在劉時(shí)燕、徐述老師的演唱版本中,時(shí)長為20分鐘;在吳瑕、李曉軍老師的演唱版本中,時(shí)長為15余分鐘。筆者也曾與重慶市曲藝團(tuán)青年演員陳欣怡合作過此曲目,演唱時(shí)長為10分鐘左右。3個(gè)版本所展現(xiàn)的3個(gè)不同時(shí)長可以說明四川揚(yáng)琴的曲目在演出時(shí),可根據(jù)本團(tuán)情況以及受眾者情況進(jìn)行曲目篇幅的適當(dāng)調(diào)整。
在《秋江》中,角色無念白,也無大段的獨(dú)白,它是以人物“陳妙嫦”與“艄翁”的對話進(jìn)行說白中的“對白”。例如:
(老白) 哎呀,姑姑,我們秋江河下有個(gè)臭規(guī)。
(女白)莫非是鄉(xiāng)規(guī)。
(老白)老漢有個(gè)開船的歌兒要唱喲。
(女白)即使如此邊唱邊開。
(老白)要的嘛,要待老漢唱起來!
(取自《四川揚(yáng)琴曲目選(一)》)
在筆者演唱的《秋江》版本中,陳妙嫦上了艄翁的船后,他們對了這么兩句話。
(艄白)慢點(diǎn)!慢點(diǎn)!姑姑姐,好大的風(fēng)啊!要下雨了呵!
(陳白)雨來了……
(取自劉立三老師記譜詞)
此兩句話的第一句用四川方言道來為:m n di ner!m n di ner!gū gū jiè,h o d li fōng ò!y o xi yù l o ǒ!此時(shí),說“對白”同樣要注意將每個(gè)字的聲母、韻母說到位,將它們的字頭、字腹、字尾用唇齒舌咬住并至最后歸好韻。
在說白處,由于是人物直接的表達(dá),文字通俗平常。因此,加之語氣,說白處的節(jié)奏較念白會(huì)更緊湊一些,但同時(shí),還應(yīng)注意將聲韻說到位,這是十分重要的一點(diǎn)。
三、“唱”之“說”的味道
據(jù)一些老前輩介紹,“灌耳風(fēng)”主要是為了聽曲中的“味兒”。筆者也從自己師父(張紹鵬先生)那里得知,“灌耳風(fēng)”是在戲曲或曲藝教學(xué)時(shí),讓學(xué)習(xí)者經(jīng)常地反復(fù)聆聽該劇(曲)種的唱腔和曲調(diào),進(jìn)而體察其藝術(shù)風(fēng)格和韻味的一個(gè)漸進(jìn)的過程。筆者在學(xué)唱四川揚(yáng)琴時(shí),首先根據(jù)一位老師的錄音“灌耳風(fēng)”。在此過程中,筆者發(fā)現(xiàn),四川揚(yáng)琴的這位男老師的演唱不像學(xué)習(xí)民歌的男歌唱家那樣有許多顫音,也不像學(xué)習(xí)美聲的男歌唱家那樣使用那么多共鳴,四川揚(yáng)琴的這位男老師演唱,雖少顫音、共鳴,聽起來卻一點(diǎn)不減風(fēng)采,十分有他所唱出的獨(dú)有的味道。那么,他的味道從何而來呢?中國音樂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陳爽曾說過這么一句話,“說唱,說唱,要以說帶唱”。筆者再結(jié)合自己的學(xué)習(xí)、演唱?dú)v程,發(fā)現(xiàn)這句話里大有文章。
“你得讓觀眾聽清楚你在唱什么”,這是筆者學(xué)習(xí)時(shí)被多次告知的話。由此,筆者想到,“說話”和“唱歌”哪種方式能更好地使人聽清曲中表達(dá)呢?筆者想來應(yīng)是“說話”,也結(jié)合此,再聽四川揚(yáng)琴男腔名家徐述老師,筆者師父,老前輩劉立三老師,男腔演員李曉軍老師等四川揚(yáng)琴演員所唱曲目,發(fā)現(xiàn)他們即使在“唱”的部分,也的確像是在“說話”一樣。
(一)以《鳳求凰》看
(取自《中國曲藝音樂集成·四川卷(上)》)
(以下高音簡稱“高”,低音簡稱“低”)
在圖1中,司馬相如演唱的第一段里第一句“我也曾長望碧空月如水”中,旋律為“1(高)1(高)65|561(高)531(高)|0665|3(高)2(高)”,此時(shí)演員演唱,可試著不要以其旋律先帶字,而是先把字咬“正”,再以說的感覺將旋律帶出。
(取自《中國曲藝音樂集成·四川卷(上)》)
再如圖2中【垛快二流】處,“久慕小姐容貌美,文章出眾女中魁”的旋律為“01(高)|35|1(高)|765|03|56|2(高)3(高)|1(高)76|05|1(高)|53|56|076|51(高)|1(高)”,同樣,演唱時(shí)需先發(fā)字音,再將字盡量“說”在音高上。如此以“說”帶“唱”,觀眾既能聽清楚故事內(nèi)容,又能將四川揚(yáng)琴“唱”部分的韻味表現(xiàn)出來。
(二)以《秋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