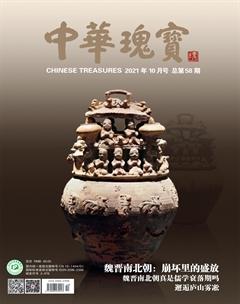分裂與融合的大時(shí)代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gè)大一統(tǒng)時(shí)代—秦漢瓦解之后,是長時(shí)間分裂和碎片化的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在這近四百年中,北方在艱難地融合胡漢之后,建立了完備高效的中央集權(quán)體制,最終擊敗了門閥政治統(tǒng)治下的南方,建立了第二個(gè)大一統(tǒng)時(shí)代—隋唐。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統(tǒng)一與分裂的交替是貫穿中國歷史的重要線索,如果說漢和唐是大一統(tǒng)盛世的象征,那么連接漢唐的魏晉南北朝則是分裂時(shí)代的典型,在傳統(tǒng)觀念中往往被認(rèn)為是一個(gè)“黑暗”時(shí)代。
如果將東漢中平六年(189年)董卓進(jìn)京作為東漢瓦解的標(biāo)志及魏晉南北朝實(shí)際上的開端,此后東漢名義上雖然仍維持了三十多年,但已天下大亂、群雄逐鹿。三國時(shí)的英雄人物曹操、劉備、孫堅(jiān)等都在此期間登上歷史舞臺(tái),互相廝殺。直至隋開皇九年(589年),隋文帝平陳,重建統(tǒng)一。整整四個(gè)世紀(jì)中,除了西晉曾有短暫的統(tǒng)一外,其他時(shí)候中國都處于四分五裂中。這一分裂期持續(xù)時(shí)間之長,在秦建立大一統(tǒng)帝國后,未曾有過。
此外,這一時(shí)期歷史的另一個(gè)特點(diǎn)是碎片化,尤其是東晉十六國時(shí)期,北方在一個(gè)多世紀(jì)的時(shí)間內(nèi),走馬燈般地出現(xiàn)了十六七個(gè)或短命或割據(jù)的政權(quán)。縱觀歷史,隋唐以降雖仍時(shí)有分裂,但之后的分裂與魏晉南北朝的分裂有本質(zhì)不同。如五代十國(從907年到960年)不過半個(gè)多世紀(jì),而且中原仍是統(tǒng)一的。至于之后遼、西夏與北宋的對(duì)峙,金與南宋的對(duì)峙等,至多只能被視為是南北朝的再現(xiàn),再未陷入到碎片化的分裂局面之中。如果我們要說中國歷史上統(tǒng)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恐怕只有穿越了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峽口,才能作如是說。
北方融合胡漢的艱難歷程
造成這一碎片化分裂局面的直接原因是西晉八王之亂后期,互相攻伐的諸王紛紛援引北方邊境的胡族加入內(nèi)戰(zhàn),如司馬穎倚匈奴劉淵部為助,司馬越與鮮卑合作。借此機(jī)會(huì)進(jìn)入中原的胡人貴族們很快發(fā)覺了西晉統(tǒng)治的孱弱與腐敗,不甘久居其下,而嘗試建立自己的政權(quán)。在消滅了西晉殘余力量后,新興胡族政權(quán)之間也攻戰(zhàn)不已。當(dāng)時(shí)先后在北方建立過政權(quán)的少數(shù)民族有匈奴、鮮卑、羯、氐、羌等,一般被稱為“五胡入華”。
如果說八王之亂只是西晉政權(quán)內(nèi)部的權(quán)力爭奪,各朝各代都不乏類似的情況,那么“五胡”的卷入不但擴(kuò)大了內(nèi)戰(zhàn)的范圍,加劇了戰(zhàn)爭的殘酷性,并且由此引發(fā)的民族遷徙與人口流動(dòng),徹底改變了中國北方的民族構(gòu)成。無可否認(rèn),連年戰(zhàn)爭造成的生產(chǎn)凋敝、物資匱乏,使得生存競爭更加激烈,在此過程中,胡漢、胡胡之間的民族沖突,乃至相互屠戮比比皆是,民族之間的矛盾趨于尖銳。為了駕馭對(duì)立的雙方,十六國政權(quán)多采取胡漢雙軌的統(tǒng)治方式,即根據(jù)胡人和漢人各自的特點(diǎn),設(shè)置不同的管理機(jī)構(gòu),分而治之。以前趙為例,“置左右司隸,各領(lǐng)戶二十余萬,萬戶置一內(nèi)史,凡內(nèi)史四十三”,統(tǒng)治漢人;至于轄下的胡族部眾,設(shè)置“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這種辦法的優(yōu)點(diǎn)在于適應(yīng)胡漢不同的生產(chǎn)和社會(huì)組織方式,減少矛盾與沖突,但本質(zhì)上仍是戰(zhàn)亂時(shí)的權(quán)宜之計(jì),分隔胡漢,而非融合胡漢。
盡管“五胡”政權(quán)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礎(chǔ)上,但由于其早年多有長期依附中原王朝的經(jīng)歷,其上層對(duì)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并不陌生,很快便能依樣畫瓢,建立起一套官僚體制。這一漢化過程并非一帆風(fēng)順,經(jīng)常觸發(fā)胡族政權(quán)內(nèi)部的矛盾,如石勒之子石弘熟習(xí)漢文化,但繼位不久就被其堂兄、戰(zhàn)功赫赫的大將石虎廢黜。十六國各政權(quán)皇位繼承過程中,代表漢化一方、相對(duì)文弱的繼承人被強(qiáng)悍的胡族部落將領(lǐng)推翻的事例比比皆是。每一次政變與對(duì)抗,又會(huì)激起新的胡漢沖突,乃至傾覆政權(quán)本身,這成為胡漢雙軌政權(quán)中的結(jié)構(gòu)性矛盾。
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在統(tǒng)一北方、局面穩(wěn)定后,進(jìn)行了融合胡漢的新嘗試。孝文帝以遷都洛陽為標(biāo)志推行漢化改革,命令鮮卑人改用漢姓,與漢族士人通婚,甚至放棄本民族的語言、服飾與風(fēng)俗習(xí)慣。這些激進(jìn)的改革措施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撕裂了鮮卑民族。留戍北邊六鎮(zhèn)的鮮卑兵士從早先的“國之肺腑”淪為“役同廝養(yǎng)”,失去了仕進(jìn)空間,積蓄已久的不滿最終引發(fā)了六鎮(zhèn)起兵,北魏也隨之滅亡。繼之而起的東魏北齊、西魏北周,統(tǒng)治核心分別來自六鎮(zhèn)中的懷朔與武川。北齊立國之初的舉措多受反漢化浪潮的影響,使胡漢矛盾有所激化。原本實(shí)力稍弱的西魏,為與北齊、梁抗衡,“維系其關(guān)隴轄境以內(nèi)之胡漢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為一家”,推行關(guān)隴本位政策,消弭胡漢界限,由弱變強(qiáng),至周武帝時(shí)一舉滅齊,重新統(tǒng)一了北方。完成了胡漢融合的北朝,汲取南北文化之長,煥發(fā)出巨大的活力,建立了更加完備高效的中央集權(quán)體制,不但憑借軍事上的優(yōu)勢完成了統(tǒng)一,也為開放包容、多元文化的盛唐奠定了基礎(chǔ)。
東晉南朝與士族政治的興衰
較之于戰(zhàn)亂不已的北方,南方形勢相對(duì)穩(wěn)定。晉元帝司馬睿最初僅有安東將軍、都督揚(yáng)州諸軍事的頭銜,論血緣不過是帝室疏屬,人望與正統(tǒng)上皆有欠缺,本來并不具備在江左運(yùn)轉(zhuǎn)皇權(quán)的條件,但北方淪陷使他因緣際會(huì)被推到歷史舞臺(tái)的中心。
由于司馬睿威望和實(shí)力不足,無法獨(dú)自撐起一個(gè)政權(quán),必須仰賴世家大族的支持,出身瑯琊王氏的王導(dǎo)扮演了這樣的角色。晉元帝即位時(shí),曾命王導(dǎo)共坐,一起接受百官朝賀,盡管王導(dǎo)一再推脫,但瑯琊王氏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時(shí)人稱“王與馬,共天下”,其實(shí)質(zhì)是士族與皇帝共同掌握權(quán)力,歷史學(xué)家田余慶稱其為“門閥政治”。東晉是中國歷史上皇權(quán)相對(duì)衰落的朝代,軍事上則依靠流民武裝,于是形成了皇帝垂拱、士族當(dāng)權(quán)、流民出力的獨(dú)特局面。
出身北府的劉裕成為門閥政治的掘墓人,代晉建宋。總體而言,南朝政治出現(xiàn)了向皇權(quán)政治復(fù)歸的趨勢。由于士族多以“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為行為準(zhǔn)則,逐漸喪失了行政能力,僅居于名義上的清望之位。南朝皇帝多用“寒人掌機(jī)要”,拔擢富有才干的寒微之士處理政務(wù),或出任典簽,監(jiān)視地方,成為擴(kuò)張皇權(quán)的工具。至梁、陳之際,又出現(xiàn)“郡邑巖穴之長,村屯塢壁之豪”乘時(shí)而起的局面,江南土豪也開始在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中占據(jù)一席之地,這些都搖動(dòng)了士族在政治上的優(yōu)勢。
一般把東晉南朝視為典型的士族社會(huì),按照歷史學(xué)家陳寅恪的定義,所謂士族“并不專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祿為其唯一之表征,而實(shí)以家學(xué)及禮法等標(biāo)異于其他諸姓”。由于士族的身份源于社會(huì)公認(rèn),而非皇帝任命,某種意義上形成了與皇權(quán)相抗衡的力量,出現(xiàn)“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現(xiàn)象。一方面士族倚仗門第,平流進(jìn)取,坐至公卿,輕松獲得高位;另一方面,依靠家學(xué)禮法,清談坐嘯,創(chuàng)造了精致的文化。但士族依靠相對(duì)封閉的通婚圈、交往圈來維系社會(huì)地位,出身寒微的人,不管本人到底才具如何,很難被士族社會(huì)接納,因此士族主導(dǎo)的東晉南朝,盡管產(chǎn)生了絢爛的文化,在文學(xué)、藝術(shù)、宗教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仍是一個(gè)缺乏社會(huì)流動(dòng)的時(shí)代。在此背景下,這一精致文化也走向形式化,變得空洞,變成了沒有現(xiàn)實(shí)關(guān)懷的清談。士族本身也日漸失去活力,不但對(duì)具體政務(wù)缺乏興趣,甚至“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連文化上的優(yōu)勢也日漸喪失。梁末侯景之亂時(shí),大量士族子弟因“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連逃難的能力都沒有,死于溝壑。東晉南朝雖然名義上承襲了西晉的正統(tǒng),具有文化上的優(yōu)勢,但也走到歷史的死胡同中,產(chǎn)生不了重建統(tǒng)一的力量。
從“東西”到“南北”
盡管魏晉南北朝最終由北方統(tǒng)一了南方,但東晉南朝以來對(duì)江南地區(qū)的開發(fā)仍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如我們現(xiàn)在都習(xí)慣稱自己為南方人或北方人,即便是居住在陜西、四川這些西部省份的人,也不會(huì)自稱為“西方人”。但以南、北作為中國地理、文化的天然劃分界線并非“自古以來”。漢代俗諺云“關(guān)西出將、關(guān)東出相”,實(shí)際上是以中原為本位,劃分“東”和“西”。再向前追溯,楚漢相爭、戰(zhàn)國時(shí)期秦與東方六國的對(duì)峙,甚至周滅商,都是東西方向的對(duì)抗,甚至八王之亂亦如是。因此在當(dāng)時(shí)人看來,中原才是決定天下走勢的核心區(qū)域,江南雖然腹地廣闊,不過是王朝的邊鄙。西晉末年,王衍為司馬越謀劃“狡兔三窟”之計(jì),選擇的三窟都在長江以北,最初并未考慮退步江南,哪怕已有孫吳立國的先例,偏安江南都未成為選項(xiàng)之一。
直到東晉初,晉元帝說過“寄人國土,心常懷慚”,學(xué)者們對(duì)這句話的背景有很多解讀,可以說司馬睿在心理上仍以北方為本位,江南不過是暫時(shí)的僑寓之所。這與兩百多年后,陳后主聽聞隋軍渡江,仍自詡“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沒。虜今來者必自敗”,前后迥異,折射出巨大的歷史變化。經(jīng)過了東晉南朝對(duì)江南腹地的拓殖開發(fā),至隋唐重建統(tǒng)一的時(shí)候,形勢已完全不同,經(jīng)濟(jì)史研究專家全漢昇對(duì)此曾有總結(jié):“我國第二次大一統(tǒng)帝國出現(xiàn)時(shí)的客觀形勢,和第一次大一統(tǒng)時(shí)有些不同。當(dāng)?shù)谝淮未笠唤y(tǒng)的時(shí)候,全國軍事政治和經(jīng)濟(jì)的重心全在北方,問題比較簡單。可是到了第二次大一統(tǒng)帝國出現(xiàn)的時(shí)候,軍事政治重心雖然仍在北方,經(jīng)濟(jì)重心卻已遷移到南方去了。”這一從“東西”到“南北”的變化直到現(xiàn)在仍影響著中國,這無疑也是魏晉南北朝留給我們的重要遺產(chǎn)。
仇鹿鳴,復(fù)旦大學(xué)歷史學(xué)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