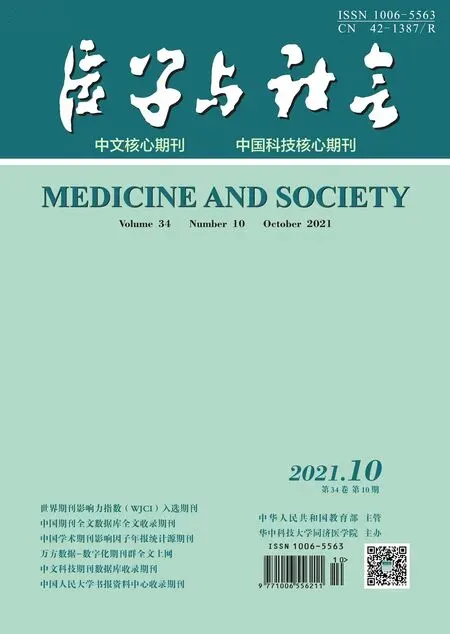中老年慢性病家庭災難性衛生支出水平及其影響因素
楊 菲 ,樊瓊玲,張雪蓮,曹雪梅,王家威,陶 寧,由淑萍
1新疆醫科大學護理學院,新疆烏魯木齊,830011;2新疆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新疆烏魯木齊,830011
現階段,慢性病已然成為我國公共衛生領域的一大難題[1]。慢性病導致的死亡人數居高不下,其導致的疾病負擔也處于較高水平。中老年人群作為慢性病的高發群體,長期被頻繁的治療以及昂貴的治療費用所困擾。沉重的經濟負擔不僅導致許多中老年慢性病家庭面臨與疾病有關的貧困處境,而且也使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受到質疑[2]。災難性衛生支出(catastrophic health care expenditure, CHE)反映的是家庭衛生支出(out-of-pocket payment, OOP)對整個家庭生活水平的影響,假設一個家庭的醫療衛生支出占家庭消費性支出比例超出一定的范圍,從而使這個家庭的經濟能力下降甚至出現難以維持生計的情況,就意味著這個家庭發生了CHE[3]。在老齡化加速背景下,我國中老年慢性病家庭CHE風險計量和相關影響因素的分析顯得尤為必要。基于此,本研究利用2015年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數據,測算我國中老年慢性病家庭發生CHE的水平,并對其發生CHE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以期為衛生政策制度如醫保政策的設計、改進提供參考。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研究采用CHARLS 2015年全國追訪數據,該數據庫由國家發展研究院和北京大學聯合開展,每2年進行一次,主要收集中國45歲及以上中老年人的生活、健康、就業、家庭等信息。采用CHARLS數據的原因有:①CHARLS提供的微觀數據足夠多,樣本量大也比較大,并且問卷涉及面廣,幾乎覆蓋了個人生活的所有方面,能夠提供CHE測算所需的體現家庭特征的相應數據;②CHARLS問卷設計參照國際標準,問卷設計科學合理,利用該問卷計算CHE相應的指標更加具有國際可比性和參考價值[4]。
經過對變量的篩選、轉化以及刪除一些對結果影響較大的缺失值后,本研究最終得到的樣本量為6483戶。其中城市2190戶,農村4293戶。中老年慢性病家庭是指家庭成員中有1個或1個以上中老年慢性病患者,經測算共有2418個慢性病家庭,其中城市837戶,農村1581戶。
1.2 研究方法
1.2.1災難性衛生支出界定。CHE 指一段時間內,OOP占家庭消費性支出的比例超過了一定的界定標準[5-6]。根據 WHO 的建議,一般采用1年內OOP超出整個家庭非食品性支出的40%及以上作為發生CHE的標準[7]。為了使得到的結果更加全面,本研究共選用了5個界定標準(20%、30%、40%、50%、60%)對樣本家庭的CHE發生情況進行計算而對 CHE 影響因素的分析則采用 40% 的閾值來判斷中老年慢性病家庭是否發生CHE。其計算公式如下:

(1)
其中,Ti表示家庭年現金衛生支出費用,xi表示家庭年消費性支出,f(x)表示家庭食品性消費支出,z表示設定閾值。
1.2.2 災難性衛生支出的測量。可通過CHE發生率和發生強度相關指標的計算來實現對CHE進行測量。家庭CHE發生率是指發生災難性衛生支出的家庭占全部家庭的比例。根據Ei即可求得CHE發生率。CHE的發生強度主要是通過平均差距和相對差距來體現,CHE平均差距=CHE差距之和/樣本家庭數。平均差距從側面反映出整個社會發生CHE的平均嚴重程度;相對差距與平均差距的計算類似,與之不同的是相對差距的分母為發生CHE的家庭數,而非全部樣本家庭,其反映了疾病對該類家庭的影響程度[8]。其具體公式為[3]:
(2)
(3)
(4)
其中,H表示CHE的發生率,O表示平均差距,MPO表示相對差距。
1.2.3 集中指數。集中指數可以反映與經濟水平相關的健康不公平程度,可以作為分析CHE對不同收入家庭造成的影響的一種方法[9]。其取值在-1到1之間,集中指數為0表示CHE在貧富家庭中的分布是均勻平等的;假設高收入的家庭更容易發生災難性衛生支出,集中指數則為正值,反之則為負值。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構成比對樣本家庭信息進行統計描述和分析,利用Stata 15.0計算CHE發生率、強度及集中指數,分析是否發生CHE(0-1變量)的影響因素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CHE發生強度(連續變量)的影響因素采用多重線性回歸模型。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樣本各年齡段居民的慢性病患病人數分別為45-54歲334人(占該年齡段的 29.5%)、55-64歲908人(占該年齡段的37.5%)、65歲以上1288人(占該年齡段的44%)。慢性病家庭中患有2種以上慢性病的占比達到39.01%,而家庭中有60歲以上老年人的占比達到了65.13%,這說明樣本人群的患病情況復雜,整體年齡偏大。
中老年慢性病家庭和非慢性病家庭過去1年的平均自付醫療衛生支出分別8522.6元和4934.0元;平均非食品消費支出分別為9911.6元和6428.1元;人均收入分別為5515.5元和5973.3元;住院率分別為43.05%和23.55%;被醫生建議應住院而實際未住院的發生率分別為20.51%和8.43%;家庭現金衛生支出占家庭非食品性支出的比例分別為85.98%和76.58%。
2.2 中老年家庭災難性衛生支出的發生情況
隨著CHE的界定閾值由20%上升至60%,樣本家庭的CHE 發生率呈現下降的趨勢。給定閾值水平40%下,中老年慢性病家庭中城鎮地區CHE發生率為16.94%,農村地區為17.53%,高于非慢病中老年家庭中對應的城鎮地區的10.19%和農村地區的12.29%。在所有樣本家庭中農村中老年慢性病家庭是CHE的發生率和發生強度最高的,其次是城市中老年慢性病家庭,而農村中老年非慢性病家庭、城市中老年非慢性病家庭的CHE發生率和發生強度則相對較低。除此之外,城市中老年慢性病家庭CHE的相對差距和平均差距(33.86%和4.26%)均高于非慢性病家庭(28.53%和4.10%)。另外,城市和農村中老年慢性病家庭CHE的集中指數分別為-0.1020和-0.1576,而相應的非慢性病家庭CHE的集中指數分別為-0.2765和-0.1488。在閾值標準由20%上升到60%的過程中,各組樣本家庭的集中指數顯示出逐漸接近-1的水平趨勢,這也從側面反映出CHE的界定標準越高,CHE的發生傾向于低收入家庭的情況就越明顯。見表1。

表1 中老年家庭災難性衛生支出發生率及發生強度
各閾值水平下CHE發生率的集中指數均為負值,說明CHE主要發生在低收入中老年家庭,這與國外學者Rahman的研究結果相似[10]。農村中老年慢性病家庭CHE集中指數的絕對值較城鎮中老年非慢性病家庭的值更大,表示CHE發生傾向于低收入家庭的不平等程度更大,這種低收入傾向的不平等使得農村中老年慢性病家庭CHE更多。
2.3 中老年慢性病家庭災難性衛生支出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以X1、X2、X3、X4、X5、X6、X7、X8、X9_1、X9_2、X9_3、X10_1、X10_2、X10_3、X11、X12作為回歸模型自變量,其中X1是性別變量,X2、X3、X6、X7屬于家庭特征變量,X4、X5、X11屬于經濟特征變量,X8、X9_1、X9_2、X9_3、X10_1、X10_2、X10_3屬于健康狀況特征變量,X12屬于醫療保險參保制度變量。以家庭是否發生CHE即Y1(0=否,1=是)為因變量進行二分類logistic回歸分析,以家庭CHE發生強度Y2(連續變量)進行回歸分析。表2表示以CHE閾值水平40%為標準,分別對農村和城鎮慢性病中老年家庭CHE發生率和發生強度影響因素回歸分析的結果。

表2 中老年慢性病家庭災難性衛生支出的影響
家庭是否發生CHE的回歸結果中,回歸系數為負值表示向不容易發生CHE方向變化,回歸系數為正值表示更容易向發生CHE方向變化;CHE發生強度的回歸結果中,負值表示其對發生強度具有負向影響,正值表示對發生強度具有正向影響。具體結論如下:①家庭成員數、是否得到親屬經濟幫助、門診和住院對農村家庭CHE發生率具有顯著影響;②性別、婚姻狀況、家庭成員數、家中是否有60歲以上老人、是否花時間照料孫子女/父母、門診和住院對城鎮家庭CHE發生率具有顯著影響;③性別、家庭成員數、是否得到親屬經濟幫助、是否向親屬提供經濟幫助、慢性病數量、衛生服務站門診、一級醫院門診、二級及以上醫院住院和家庭人均收入對農村家庭發生強度具有顯著影響;④婚姻狀況、慢性病數量、衛生服務站(診所)住院對城鎮家庭CHE發生強度具有顯著影響。
3 討論
3.1 中老年家庭災難性衛生支出存在不平等性
CHE發生率是衡量家庭CHE發生密度的重要指標[8]。結果顯示,2015年我國城鎮和農村中老年慢性病患者家庭CHE發生率均低于匡晶晶等針對CHARLS 2013年數據得出的研究結果(32.35%和37.41%)[11]。在CHE發生率各個界定標準下(20%、30%、40%、50%、60%),2015年我國中老年慢性病家庭的CHE發生率較2013年分別減少了21.47%、19.81%、17.90%、16.08%、15.32%,但相比于醫保制度健全且居民收入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如美國、葡萄牙、德國、瑞典等家庭CHE發生率(一般均低于1%)[7-8],我國的仍然處于較高水平。
我國仍有家庭承受較重的疾病經濟負擔,且這類家庭數量較多[12],我國社會醫療保障體系還不夠完善,無法滿足居民對衛生服務更高的需求,且居民醫療成本的也處于較高的水平[13]。中老年慢性病人群的CHE風險較高,表明醫療保障制度的功能發揮并不完善,當前我國醫保的覆蓋廣,但深度不夠,如報銷項目和范圍有限制等[14]。一方面,我國慢性病患者看病費用較高,而醫保報銷比例較低,遠遠無法滿足慢性病患者看病費用需求;另一方面,我國納入保障的慢性病病種數量不全,不同地區的政策差異較大,這也導致不同地區人群或同一地區不同人群間出現醫療保障不公平現象。此外,農村和城鎮慢性病家庭的CHE發生率均高于非慢性病家庭,且慢性病家庭的醫療需求明顯更多。同時,根據CHE發生的不平等性,政府應注重對低收入,特別是農村低收入中老年慢性病家庭在醫療保障制度上的傾向性,注重不同地區不同人群間的慢性病門診保障政策的融合發展,以增強該群體抵御CHE發生風險的能力。
3.2 影響中老年家庭災難性衛生支出發生概率和強度的因素多樣化
結果表明,我國中老年家庭CHE的發生率和發生強度顯著影響因素較多。①家庭規模越大,中老年慢性病家庭發生CHE的概率越小,同時農村家庭發生CHE的強度也變小。說明這種效應在農村更突出,農村家庭抵御CHE風險時對家庭規模的依賴程度比城市更高[2]。②向親屬等提供經濟幫助會顯著提升農村中老年慢性病家庭CHE發生的強度,而得到親屬等提供的經濟幫助會顯著降低CHE的強度,這表明農村中老年慢性病家庭更需要得到來自各界的經濟支持。③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中老年家庭慢性病老人到各級醫院門診就診和住院治療均會顯著增加CHE發生的概率,而農村慢病老人選擇到衛生服務站(診所)、一級醫院的門診就診、二級及以上醫院住院會顯著降低CHE的發生強度。這從側面說明在僅需門診治療的情況下,農村慢性病老人應提高對基層醫院門診的醫療服務利用度。④家庭人均收入與CHE發生概率、發生強度呈顯著負相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發生CHE的概率和強度也越小,從側面反映出低收入家庭可能更容易發生CHE。
而無論是否參加醫保,都不會顯著影響CHE的發生,其原因為:①未參保樣本偏少,在全民參保的大背景下,未參保的家庭極少,6354戶樣本家庭中僅有459戶家庭(約占樣本總量7.08%)未參加任何形式的醫療保險;②未參保家庭由于經濟條件有限或所處地區醫療水平不足,從而主動或被動放棄就醫,出現應住院而未住院的情況,醫療需求未能得到滿足,使該類人群CHE發生風險被低估;③側面暴露出當前我國醫療保障制度不夠完善。
綜上所述,我國中老年家庭的CHE水平整體較高,其中慢性病家庭的CHE發生率高于非慢性病家庭,且CHE更易發生在低收入家庭。政府在醫保籌資以及補償政策設計中,要注意對低收入人群標準的設定,注重保障醫保制度的公平性和傾向性。不斷完善我國基本醫療保障制度,進一步提高醫保覆蓋的深度,加大對中老年慢性病群體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的保障,降低CHE的發生率和發生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