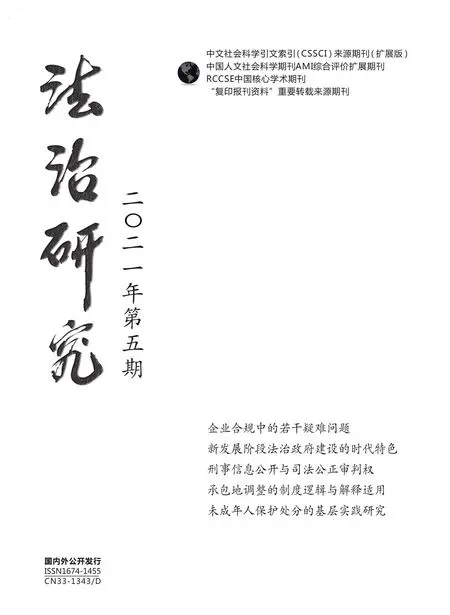未成年人保護處分的基層實踐研究*
徐劍鋒 崔倩如
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2018—2022 年檢察改革工作規劃》要求深化涉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探索建立罪錯未成年人臨界教育、家庭教育、分級處遇和保護處分制度。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構建起家庭、學校、社會、網絡、政府、司法等多重保護網,對于沒有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的罪錯未成年人,各級機關應落實好教育矯治、嚴加管束,建立起一整套“寬容但不能縱容”的未成年人保護處分制度。
一、未成年人保護處分制度概述
未成年人保護處分制度主要是對青少年采取的非刑法處置措施,體現了預防青少年犯罪功能,其內涵和特征也隨著社會發展逐步完善。
(一)內涵
未成年人保護處分制度,就是指針對未成年人的,兼具保護和處罰功能的教育方式,是一種代替刑法的措施,①參見陳敏男:《少年事件處理法之保護處分與刑法保安處分之比較研究》,臺灣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2002 年度碩士學位論文,第33 頁。是從青少年健康成長的角度出發所采取的必要保護。②參見[日]大谷實:《刑事政策學》,黎宏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158 頁。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少年法》所規定的保護觀察、移送教養院或養護設施、移送少年院③日本少年院是收容家庭裁判所判處保護處分少年的國立機構,主要開展如下課程:生活指導、職業訓練、學科教育、特殊教育及醫療處遇等。參見[日]宮澤浩一:《少年違法犯罪與違法犯罪少年的處遇》,西原春夫主編:《日本刑事法的形成與特色》,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第201-205 頁。等。保護處分源于保安處分理論和國家親權思想,兩者都主張將視閾擴展到有人身危險性的青少年,而不只是罪錯青少年,同時更加關注臨界預防。
(二)特征
保護處分的主要目的是實現特殊預防和臨界預防,在懲罰未成年人犯罪的基礎上,更加注重防止未然犯罪的可能性,即常說的教重于罰。在青少年步入犯罪深淵前進行干預和矯正。保護處分的作出機關通常為公檢法三家中專門負責未成年案件的部門,如法院的少年法庭,依據法律做出處分,④參見[日]安平政吉:《保安處分法的理論》,日本酒井書店1970 年版,第114 頁;林紀東:《刑事政策學》,國立編譯館1969年版,第311 頁。從而使之更具有公信力和強制力。其最重要的特點是優先于刑法適用。考慮到未成年人處遇個別化原則,一般會先使用保護處分,只有在萬不得已時才考慮施以刑罰。⑤《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第17 條第1 款第3 項明確規定:“除非判決少年犯有涉及對他人行使暴力的嚴重行為,或屢犯其他嚴重罪行,并且不能對其采取其他合適的對策,否則不得剝奪其人身自由。”可見,對犯罪未成年人判處刑罰,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罪行嚴重和無其他合適對策。保護處分具有先進性,隨著社會發展會注入新的內涵,如社區服務令就是隨著社區建制的發展而逐步產生的一種保護處分措施。
(三)意義
從統計數據來看,我國未成年人犯罪情況總體趨于穩定,數量較多。僅2019 一年檢察機關受理審查逮捕未成年人犯罪48275 人,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61295 人;14 歲至16 歲的低齡犯罪現象仍多有存在,2014 年至2019 年共有40966 名低齡未成年人涉嫌刑事犯罪;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除2017 年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均呈增長趨勢。⑥數據圖表來源:最高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14—2019)》,2020 年6 月發布。但2019 年上海市對361 名罪錯未成年人開展保護處分后,無一再犯。因此,探索未成年人保護處分制度勢在必行,提前分級處遇,預防青少年犯罪,有利于進一步降低未成年犯罪人數和再犯可能性。
二、我國和其他地區保護處分制度的實踐
國際上針對罪錯未成年人,適用刑罰的比例很低。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第19 條更是規定了“對少年不到萬不得已不能監禁”的原則。保護處分制度比較典型的有日本、英國、美國和我國臺灣地區。
(一)日本的保護處分制度

日本主要將保護處分制度的對象分為三類:即犯罪少年、觸法少年和虞犯少年,常統稱為“少年非行”。⑦根據日本《少年法》第3 條第1 款規定,交付家庭裁判所審判的少年包括三類:(1)犯罪的少年;(2)未滿14 歲的觸犯刑罰法令的少年;(3)虞犯少年。日本對少年犯罪的處分形式主要有六種:不予審判、不予處分、移送兒童福祉機關、移送檢察官、保護處分、救濟程序。其中,觸法少年指的是年齡不到14 周歲,雖然已經違法,但按照日本的刑法規定不負刑事責任的未成年人。虞犯少年⑧根據日本《少年法》第3 條第1 款規定,虞犯是指“有以下情形的,根據其性格及其環境,將來有可能犯罪以及觸犯刑罰法令的行為的少年:1.具有不服從保護人的正當監護之惡習的;2.沒有正當理由不靠近家庭的;3.與有犯罪性的人或不道德的人進行交往,或出入可疑場所的;4.具有傷害自己及他人品行行為之惡習的”。則是指當前并無違法犯罪行為,但認為其存在犯罪可能性的未成年人,具體如品行惡劣、不服管教、出入不正當場所、認識不當的朋友等情形。⑨參見康樹華:《當代中國犯罪主體》,群眾出版社2005 年第1 版,第11-13 頁。
日本保護處分制度的具體形式分為三種:⑩參見[日]藤吉和史:《少年犯罪和觸法行為者》,日本成文堂2005 年版,第133 頁。第一,保護觀察。即交由保護觀察所進行,將上述少年放置于各自的家庭環境或就業環境中,不影響其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對其進行監督指導或輔導援助。根據日本《犯罪者預防更生法》第39 條規定,該類監督人員稱為“保護觀察員”,是具有心理學等專業知識的公務人員,?參見張志泉:《矯正社會化的國外實踐及其啟示》,載《中國行政管理》2011 年第9 期。其主要職責分為兩類,一是督促孩子的父母履行好監護職責,二是對未成年人進行管束,一旦發現孩子有逾矩行為,情節較為嚴重,可以申請將該未成年人收容處分。第二,移送自立設施或養護設施。保護觀察針對的是一些有潛在犯罪可能性或已經有不良行為的少年,是一種開放性收容處分,有專人對這些未成年人進行指導,且生活在一起。而移送自立設施針對的是困境兒童,如缺少監護人的孩子、被虐待的孩子等,也有保育阿姨等與孩子們一起生活。第三,移送少年院。這是國家設立的機構,專門收容矯正未成年人,原則上封閉管理,在其中要接受相關學習和教育改造。細分的話又可以分為初級少年院、中級少年院、特別少年院和醫療少年院,分別收容教育12 至16 歲的正常青少年、16 至20 歲的正常青少年、16 至23 歲的虞犯少年和身心有缺陷的12 至26 歲的青少年。
日本保護處分制度的執行機構主要由矯治機構、兒童福利機構、保護機構和司法機構組成。而司法機構中專門處理未成年人犯罪的部門叫做家庭裁判所,負責除重罪少年外的一切案件,體現了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
(二)英美的保護處分制度
英國對未成年人體現出輕刑化特征。主要的保護處分內容有兩種:一是社區判決,即讓犯罪少年重新回歸日常社會,由社區統一管理,是一種非監禁的保護處分,其下又分為罰款、社區服務、有條件釋放、活動計劃、補償等多種法令。二是拘禁判決,也就是將犯罪少年放置于特定的機構予以管理,針對的是被法院判處監禁的未成年人。
美國的保護處分主要有四種:保護觀察、交付親屬或寄養家庭、原家庭外的安置和拘禁于公立訓練學校等方式。其中,最常用的是保護觀察,即通過家長對罪錯少年進行管教,只有在保護觀察效果不好時,才會考慮將未成年人予以拘禁。
(三)我國臺灣地區的保護處分制度
我國臺灣地區將少年的偏差行為分為觸法行為、虞犯行為?根據我國臺灣地區2007 年最新修訂的“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 條第2 項規定,虞犯主要指以下幾種情形:(1)經常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2)經常出入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3)經常逃學或逃家;(4)參加不良組織;(5)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刀械;(6)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的迷幻物品。、不良行為?根據我國臺灣地區1998 年11 月14 日研修的《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預防辦法》第3 條規定,一般不良行為分別是:(1)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2)出入妨害身心健康場所或其他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3)逃學或逃家;(4)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化學制劑或其他危險物品;(5)深夜游蕩;(6)對父母、尊長或教師態度傲慢,舉止粗暴;(7)于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8)以猥褻之言語、舉動或其他方法,調戲他人;(9)持有猥褻圖片、文字、錄影帶、光碟、出版品或其他物品;(10)加暴行于人或互相斗毆未至傷害;(11)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三類。對于情節輕微的不良行為,一般由警察當場進行教導,并通知其父母帶回家嚴加管教,如果是嚴重不良行為或者達到虞犯的程度,則將該未成年人直接移送少年及家事法庭,法庭配備相關專業人員如少年法庭法官、心理測評員和家庭調查員等,專業處理少年事件,對罪錯少年給予較為寬容的矯治處分。
我國臺灣地區最典型的處分措施為少年觀護制度,涵蓋了整個未成年人事件處理的審前、審中、審后三大階段,體系復雜,有專門的少年觀護官對未成年人進行觀察、監督和矯正。該制度兼具司法、行政、社會矯治、犯罪預防等價值功能。
一是審前觀護。主要包括審前調查、急速輔導、收容輔導與轉介輔導。急速輔導是在審前調查后,對無收容必要的未成年人進行的管教,輔導內容包含學業、工作、情緒、法律等,由少年調查官出具輔導報告,為法官提供參考。收容輔導就是針對收容于少年觀護所的未成年人進行監督教育的方式,除了少年調查官,還會有專業的醫生和鑒定人員運用科學方法進行鑒別,輔導內容與急速輔導雷同。轉介輔導是為了避免司法程序對未成年人造成創傷而設立的觀護方式,對于情節輕微罪錯少年,不再訴至法院,而從司法程序中轉介出來,交由相關的福利性機構進行短時間的輔導,如團輔、營隊和訪問活動。?參見施亦暉:《少年轉向制度的概念、嚴格、理論基礎》,載《兒童及少年審前轉向與安置輔導實務研討會》論文集,第6-28 頁。二是審中觀護。在法院開庭審理后,對少年觀護有不付保護處分、應付保護處分以及暫緩保護處分而裁定交付觀察三種處置。其中,最后一種交付觀察是指當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對未成年人該如何處分不置可否時,可征詢調查官的建議,裁定對該未成年人交付適當的機構和團體進行3 到6 個月的觀察期,從而激勵未成年人產生自我約束,類似檢察院的附條件不起訴幫教程序。三是審后觀護。又分為假日生活輔導、保護管束、留置觀察和親職教育輔導四種。假日輔導,指的就是在法官訓誡以后,交由少年保護官或其他機構,在未成年人的空余時間執行三到十次的道德、法律、學習等輔導和勞動服務。保護管束期限在3 年以下,適用于21 周歲以下少年,在此期間,未成年人要服從保護官的命令,保持良好作風、改變不良行為、不逃學、不抽煙、不賭博、不進入特定場所,并按時報告。留置觀察是指當未成年人違反規定,如無正當理由不接受輔導等,將被置于少年觀護所5 日的處分,是一種短暫的警惕性處分。親職教育輔導是指為加重未成年人父母的管束責任,法院可以讓父母接受8 到50 個小時的親職教育,如果法定代理人拒絕,法院將連續對父母處以罰款直到接受為止。
(四)我國的保護處分制度
目前,我國尚未正式建立起系統完備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未成年人保護處分制度,只有《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兩部法律將未成年人分為四類,分別是一般青少年、有不良行為的青少年、?《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8 條規定:本法所稱不良行為,是指未成年人實施的不利于其健康成長的下列行為:(一)吸煙、飲酒;(二)多次曠課、逃學;(三)無故夜不歸宿、離家出走;(四)沉迷網絡;(五)與社會上具有不良習性的人交往,組織或者參加實施不良行為的團伙;(六)進入法律法規規定未成年人不宜進入的場所;(七)參與賭博、變相賭博,或者參加封建迷信、邪教等活動;(八)閱覽、觀看或者收聽宣揚淫穢、色情、暴力、恐怖、極端等內容的讀物、音像制品或者網絡信息等;(九)其他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長的不良行為。有嚴重不良行為的青少年?《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8 條規定:本法所稱嚴重不良行為,是指未成年人實施的有刑法規定、因不滿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不予刑事處罰的行為,以及嚴重危害社會的下列行為:(一)結伙斗毆,追逐、攔截他人,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等尋釁滋事行為;(二)非法攜帶槍支、彈藥或者弩、匕首等國家規定的管制器具;(三)毆打、辱罵、恐嚇,或者故意傷害他人身體;(四)盜竊、哄搶、搶奪或者故意損毀公私財物;(五)傳播淫穢的讀物、音像制品或者信息等;(六)賣淫、嫖娼,或者進行淫穢表演;(七)吸食、注射毒品,或者向他人提供毒品;(八)參與賭博賭資較大;(九)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和已經觸犯法律的青少年。?對重新犯罪的預防,也就是已經觸犯法律的未成年人,不論是公安機關立案、檢察機關不起訴或是法庭判決其有罪,都應當在各個階段對觸犯法律的未成年人開展必要的教育感化。而從現行法律法規來看,當前可以適用于罪錯少年的各類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幾種:警告、罰款、拘留、強制醫療、專門學校教育,還有一些非刑罰的處理如訓誡、賠禮道歉、賠償損失和具結悔過等。而具體實踐中法官仍主要使用刑罰作為主要處置手段,這也導致了很多未成年人“交叉感染”和“二進宮”等問題,無法真正做到預防和矯正青少年犯罪的目的。因此,我國需要盡快建立起獨立完善的少年保護處分制度,真正實現臨界預防和分級處遇。
三、我國涉未罪保護處分制度中存在問題
我國類似保護處分制度的規定零散見于各類法律法規中,立法位階不夠清晰,行政色彩較為濃厚,缺乏立法的系統性、穩定性,故而沒有真正形成科學、系統、精準的保護處分體系。同時,懲罰性較強,標簽效應明顯,社區矯正專業化程度不夠等都是學者常提及的弊端。本文將著重通過對保護對象、工讀教育、司法機關和社會力量四方面的分析來探討臨界預防和保護處分中具體存在的問題。
(一)保護處分對象有待擴展,困境兒童及被害者成制度漏洞
筆者認為,兩部未成年人法規定的四類未成年人分類仍不夠完善,應進一步細化。
1.困境兒童未納入適用主體
實際辦案中,我們發現很多未成年人涉嫌刑事犯罪往往是被逼無奈,處于極度困境狀態,或是經濟拮據,或是沒有父母管束,或是由于父母管束太過嚴厲導致心理存在問題,而我國針對困境兒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明確規定:兒童系指18 歲以下的任何人,與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所界定的未成年人含義相同。我國目前存在“兒童”與“未成年人”并用的情況。總的來看,“兒童”一詞多在社會學與民政福利領域使用,“未成年人”一詞則多在法學與法律領域使用。除非特別說明,本文所稱兒童與未成年人的含義相同,但在不同語境下則尊重兩個概念的使用習慣。國家監護制度又不夠健全,導致困境兒童成為犯罪高發人群。困境兒童的本質特征是家庭無法庇護,根據國家親權理論需要國家介入管理,但我國目前對困境兒童的保護形勢仍較為嚴峻。
同時,困境兒童的信息該如何掌握也存在障礙,由誰來收集整合困境兒童的信息;該如何干預、如何幫扶;該做哪些輔導教育工作,由誰來做專業的干預工作;涉及多部門協調時由誰主導,從而避免責任稀釋,最大限度給予困境兒童以心理上和經濟上的支持;當困境兒童處于犯罪臨界狀態時,又由誰來監督,由誰來負責。以上都是具體實施過程中會產生的問題,需要建立有步驟的長效機制,才能將這些困境兒童納入保護處分和臨界預防的對象。
2.被害未成年人未納入適用主體
辦案中還發現,許多案件的犯罪分子系由被害人的身份轉化而來,很多人由于在幼年曾遭受迫害,長大后反而成為了施害者。如2019 年杭州市拱墅區人民檢察院辦理的譚某某、袁某某等人組織賣淫案,袁某某原先是被組織的賣淫女,之后其不僅自己繼續賣淫,還成為了“老鴇”,管理組織一批賣淫的未成年少女。還有一些在家庭暴力中遭受傷害的孩子,長大以后轉而毆打他們的孩子,如盛某某故意殺人案。?盛某某故意殺人案中,盛某某的父親長期與妻子存在矛盾,毆打妻子和兒子盛某某,最后將妻子殺死后自殺,盛某某幼年遭到父親毆打,并知道其父親殺死母親,其雖然正常考入浙江大學并結婚生子,但結婚后常家暴自己的妻子,并最終用刀砍傷兒子31處并試圖自殺。從心理學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強者認同,一個人被勒索了,他就會勒索其他的弱者;還有一方面是孩子在年幼時受到的傷害如果沒得到正確的引導,往往會引發一系列的心理問題。而現有的保護處分和分級管理中,缺少對此類潛在犯罪者的關注,對于案件中受到迫害的未成年人,我們通常出于保護和防止二次侵害的目的,不對他們作過多打擾,甚至信息不詳。
(二)保護處分措施與客觀需求不符,工讀教育辦學困難重重
我國零散在各部法律中的一些保護處分措施已經跟不上少年司法發展的客觀需求,具體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拘禁措施易交叉感染
公安機關在發現未成年人犯罪時,常常先行拘留7 日或延長30 日,之后報檢察院批準逮捕,這段期間對未成年人實行拘留,雖然一般采取單獨關押的措施,但實質也是一種變相的短期監禁,具有濃厚的少年監獄色彩,容易讓未成年人在看守所里受到不良影響,形成抱團效應,增加對社會的反叛,導致離開后走上更嚴重的犯罪道路,并可能產生標簽效應,不利于對青少年的挽救和特殊教育,也和全世界推行對罪錯未成年人實行非監禁化的處分原則相違背,因此應當慎用。
2.軟性措施致復發率高
軟性措施主要包括《預防青少年犯罪法》中規定的訓誡、道歉、賠償、責令具結悔過、不得進入特定場所、不得與特定人員交往、不得實施特定行為等,這些措施趨于表面化和短期化,很多未成年犯罪分子或者嚴重不良行為的少年為了逃脫法律的懲戒,愿意賠禮道歉并在短期內表現得“乖巧”,但很多未成年盜竊慣犯往往在之后又“重操舊業”,因為來錢快、對他們的懲罰力度小,他們往往在一段時間的幫教以后仍繼續去偷盜財物。另外,對于一些有不良行為的青少年,檢察機關還會對家長進行親職教育,要求家長嚴加管教,但成效不明顯,換言之,很多未成年人之所以會有這些行為,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監護人管束不力的結果,在法律后果發生以后,繼續交由家長進行管教,無疑是一種逃避司法責任的表現,另一個悖論是,如果家長平時能好好管束孩子,未成年人也就不會實施違法犯罪行為了。
3.工讀學校遇辦學困境
實踐證明,工讀教育對罪錯少年的挽救曾發揮過巨大作用,一方面可以讓已經輟學的未成年人有繼續接受教育的權利,另一方面也能通過半工半讀的方式培養孩子未來求生的技能,只要這些未成年人在社會上能獲得認同和肯定,有一技之長,能夠自食其力,重新回歸社會,其再次從事犯罪活動的幾率就會幾何式下降。但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的發展,現階段我國工讀學校的辦學面臨較為嚴峻的形勢:招生難、師資弱、經費少成為“三座大山”,?參見賈洛川:《未成年違法犯罪人員矯正制度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196-230 頁。政策投入傾斜力度小,在很多地區,由于缺乏基本的保障,工讀教育連維持日常的生存都十分困難,更難言進一步發展了。
(三)司法機關專業機構尚未完全設立,幫教責任難落實
一般認為,1984 年上海成立的首個少年法庭,是我國少年司法制度的雛形。現在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也要求公檢法設立相對獨立的未成年人案件辦理機構。但實踐中,只有檢察機關初步建成了貫穿四級的未成年人檢察組織體系,到2019 年底,四級檢察院共有1566 個院成立獨立的未成年人檢察機構和未檢檢察官辦案組,占檢察院總數的45.36%,最高檢、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人民檢察院均設置了獨立未檢部門。基層檢察院中,有1108個基層院有專門的未檢檢察官,有837 個院設置了未檢辦案組,有390 個已具備獨立的未檢機構。21同注前⑥。

全國基層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辦案組織情況
但公安機關內部沒有處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專門人員,缺少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板塊,法院也缺少統一的少年法庭,一般刑事案件均是由刑庭統一不公開開庭處理,而不分專人審理。公檢法和其他機構缺乏統一對接的部門進行未成年人信息保密處理,導致一些本應封存的犯罪記錄存在泄露可能性。
另一方面,在針對未成年人的幫教工作中,公檢法司四部門缺少統一合作,導致幫教流于形式。從目前四部門的具體情況來看:司法局自身力量有限;法院將主要精力放于審判和執行工作,沒有更多的時間參與庭外幫教;檢察機關雖然有專門的未檢部門,但干警人員數量配備較少;公安機關的基層民警自身工作千頭萬緒,難以將警力投入到未成年人工作中去。上述情況導致四部門無法形成合力。
(四)社會力量各管一段,信息采集難開展
《未成年人保護法》確立了保護未成年人的共同責任原則。22《未成年人保護法》第6 條規定:保護未成年人,是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政黨、人民團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城鄉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未成年人的監護人以及其他成年人的共同責任。但實踐中,學校老師、父母、社會各管一端,共同責任最終導致責任分配不清,誰都可以對未成年人工作進行指導,但誰都沒有將罪錯青少年的教育職責列為專門的業務,最終導致出了問題也不知道該向誰問責。從學校分析,老師的主要目標放在學生的升學上,無暇顧及幫教工作;從社區來看,各區雖然有團委、婦聯、教育局等機構負責青少年工作,但通常負責人均身兼數職,處理本職工作已經捉襟見肘,要去主抓不良青少年的幫扶教育工作基本不現實,導致社區幫教工作也被虛置。具體來說,雖然各基層政府已經陸續成立了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但實際上卻處于工作崗位基本系其他部門兼任,沒有固定工作流程,沒有固定工作部門、工作地點、工作人員的尷尬局面,亦沒有實施具體的保護措施。破解責任稀釋困境,需要細化具體分工,構建完善的職責保護機制。
未成年人信息采集工作也存在障礙。以困境兒童為例,雖然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第29 條和第43 條規定,學校、居委會、村委會要建立留守兒童、困境兒童的信息檔案。但從目前實踐來看,教育部門不太愿意提供數據,一方面出于保護孩子隱私的考慮,另一方面由于多頭索要數據,沒有統一平臺共享信息檔案,導致渠道不暢;而居委會、村委會上門調查情況又缺乏權威性和時效性,家長往往不愿意配合或調查不到真實的數據。具體操作層面而言,現今查詢困境兒童信息,可能要跑民政、婦聯、教育、關工委等部門,查詢行政違法前科的未成年人,可能要跑派出所,信息不全又沒有統一管理的數據庫,離實現數字化統籌還存在差距。
四、我國保護處分制度的改善路徑
要解決上述問題,還要從四方面著手,即明確保護處分對象、健全保護處分類型、細分司法主體、協調責任主體等,構建起七位一體的保護處分對象體系。
(一)明確保護處分對象
1.建立“七位一體”保護處分適用主體
第一,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即已經構成刑事犯罪的人員;第二,罪錯未成年人,就是14 周歲或16 周歲以下具有犯罪行為,但不負刑事責任的青少年;第三,臨界未成年人,是具有嚴重不良行為的青少年,針對一些接受過治安處罰的未成年人,要與派出所加強合作,增加與公安機關聯動,要求數據線索共享,發現未成年人涉嫌行政違法應及時將情況通報給檢察院,并進行跟蹤回訪,著重臨界預防;第四,未成年被害人,指的是性侵和故意傷害等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害人;第五,不良少年。尤其是在學校受過處分的孩子,可加強預防犯罪的針對性,并進行家庭周邊環境等社會治理;第六,困境兒童,如殘疾兒童、監護權喪失的、服刑在教子女和經濟困難、留守兒童等,進行數據排摸;第七,普通青少年,如外來務工子女,體現一般預防功能,進行定期法治宣講,法治進校園等活動,普及法律知識,避免很多年輕人由于不懂法不知法而觸犯法律。
2.突出對困境兒童的保護和數據收集
2016 年,國務院出臺了涉及留守和困境兒童的兩個《意見》,23即《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和《關于加強困境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明確了國家在保護困境兒童中的責任。242016 年6 月13 日發布的《關于加強困境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將困境兒童界定為:“因家庭貧困導致生活、就醫、就學等困難的兒童,因自身殘疾導致康復、照料、護理和社會融入等困難的兒童,以及因家庭監護缺失或監護不當遭受虐待、遺棄、意外傷害、不法侵害等導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或侵害的兒童”。而針對困境兒童數據收集難的問題,應當建立網格化幫教平臺,由專門主體整合數據,重點監測預防和研判,發現情況及時移交和干預,平臺通過各項數據匯總,如父母是否離異、家庭是否具備監管條件等及時預警,引入第三方專業機構綜合評估,并及時跟蹤回訪,納入網格化監管,以避免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惡性案件的發生。同時,對該類未成年人進行數據收集和管理時,一定要注重保護他們的隱私,做好數據保密工作。不然極易侵害未成年人應有的權益,也容易對孩子產生標簽效應。25參見盛長富、郝正天:《論保護處分及對我國的借鑒》,載《法律適用》2015 年第4 期。尤其對再次犯罪、被害人未成年人、困境兒童等的預防,要建立統一的數據庫,定期跟蹤回訪。
(二)健全保護處分類型
未成年人犯罪是“錯”,不是“惡”,我們需要對其引導矯治,而非單純的懲罰。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保護處分類型,豐富種類,增強非監禁的硬性措施,以幫助未成年人自我矯治,重新適應家庭和社會生活,并促使工讀學校向專業機構進一步轉型更新。
1.保護觀察
保護觀察是最重要的社區性保護處分措施,在日本和美國實施效果良好。26參見敷田稔、土屋真一、潘漢典:《日本少年司法制度》,載《環球法律評論》1980 年第3 期;呂征:《美國犯罪少年的刑罰替代措施》,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06 年第3 期。該措施旨在讓罪錯少年回歸到原先的家庭生活環境中予以矯治,使未成年人盡量減少與社會的隔離,減少對其原先學習和成長的影響。27參見[日]菊田幸一:《少年法概說》,日本有斐閣1980 年版,第189 頁。在罪錯青少年未成年前,需要設立專門的保護觀察員對該未成年人進行監督和教育,直到18 周歲終止。在此期間,保護觀察員可以根據相關法律要求未成年人遵守和履行何種義務,當觀察員覺得未成年人有嚴重不良行為時,可以向法院申請對其重新考慮監禁措施或送至專門學校進行統一管理。
2.非羈碼監管
杭州地區自主研發的非羈押人員數字監控系統,稱為“非羈碼”,可用于實時監控罪錯未成年人的行蹤。具體操作是以非羈押APP 為載體,通過外出提醒、違規預警、定時打卡、禁入地點監控等多項功能,對被監管的未成年人進行動態監管,一定程度上限制罪錯未成年人進入某些不宜進入的場所,結交不良朋友等。一旦發現未成年人違反相關規定,系統會及時預警并通知到對口的公安干警、檢察官和法官,由這些司法人員重新考量其行為和法律后果。
3.節假日輔導或安置
節假日輔導和安置是一種中間保護處分措施,指的是未成年人在平時工作學習時,仍放在家庭中完成,但到了節假日,則要到專門的機構中完成學習和輔導,很多國家和地區有類似的措施。28如美國的除本家庭外的安置、英國的出席教育中心令、德國的業余時間禁閉、俄羅斯的閑暇時間限制令、日本的移送福利性教養機構、我國臺灣地區的安置輔導、中國澳門的半收容等。其共同的特點是,節假日輔導不影響這些罪錯少年的正常學業,只在放假時對他們進行集中教育,把他們安置在較為封閉的收容機構進行學習教育和輔導。
4.移送專門學校
移送專門學校就是把犯罪的未成年人放到全封閉的收容機構進行一段時間的學習矯正。國際上很多國家和地區都采取了該種保護措施,但名稱不同,有的叫做少年院、感化院,有的叫做專門學校和訓練學校。新修訂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將該類學校重新定義為“專門學校”,并提出國家要對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加強專門學校教育,成立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未來,國務院和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要建立具體細則,形成一整套臨界預防管理模式,逐步向專業化職業化模式轉變,增加國家財政投入,匯集各方力量增加師資,完善教育內容。同時,專門學校也可以借鑒日本少年院進行功能分化,根據未成年人身心是否存在障礙、年齡差異等特征分為初等、中等、特別和醫療專門學校。
(三)細分保護處分司法主體
1.公安和法院應建立專門機構
公安機關尤其是派出所辦案人員,囿于基層治安案件數量龐大,人力有限,長期以來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人員和力量與普通案件存在完全重疊。應當在市級公安機關層面建立專門的未成年人公安部門,由女性警官參與其中,并聘請第三方專業人員,針對未成年人的心理和身體狀況進行評估。同時,對未成年人實施拘留要謹慎,盡量取保候審,但可以考慮使用非羈碼等方式限制未成年人進入特定場所。
我國法院審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機構長期以來附屬于普通法院,但也有部分地區試點少年法庭,如上海長寧的少年法庭,試點以后教育矯治了許多未成年犯罪人員,但由于缺少自上而下的少年審判機構,導致每逢改革節點該少年法庭就會面臨轉型沖擊。應當看到,建立專門的少年法庭,建立專業的隊伍,形成獨立的審判評價體系,是符合世界潮流和時代發展的,可以挽回更多罪錯少年。
2.發揮檢察機關主力軍作用
檢察機關是公檢法中唯一一個有專門未成年人案件辦理部門的機構,并有一系列針對未成年人的特別程序:如聘請第三方進行心理干預、附條件不起訴、6 個月的幫教考察期等,對罪錯未成年人起到了良好的教育矯治作用。根據《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7 條規定,檢察機關的專門人員應當經過專業培訓。現在各基層檢察院主要還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將專業性較強的心理輔導和幫教外包給心理咨詢室和社工團體,未來未檢工作人員要成為“多面手”,取得相關培訓資質,持證上崗進行專業的未檢輔導工作,掌握心理學、教育學和社會學等綜合性知識,準確把握未成年人的性格特征,培養起一批少年觀護員和調查員。同時,檢察機關還要加強與共青團、婦聯等社會團體的合作和聯系,構建起全方面的社會支持體系。
(四)協調保護處分責任主體
1.檢警協同前置節點
針對多頭共管導致的責任稀釋問題,可由檢察機關牽頭落實好監督職責,形成全社會齊抓共管的大格局。一方面,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積累了豐富的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實踐,能夠滿足涉罪未成年人多元矯正的需要。另一方面,檢察機關作為公安和法院之間的橋梁,發揮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能夠保證矯正措施銜接順暢。在基層檢察院實踐中,杭州多地檢察院和公安分局建立了檢警協同機制,不斷加強在涉未成年人刑事、治安案件中的配合與協作,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動建立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大格局。具體舉措包括在公安局建立起檢察官辦公室,依法開展涉未成年人刑事、治安案件的信息共享、偵查監督、幫教跟蹤、分級處遇等工作,并就以下五類未成年人信息建立共享機制:(一)涉罪未成年人,即已經構成犯罪的未成年人。(二)罪錯未成年人,即已經觸犯刑法但因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而不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未成年人。(三)臨界未成年人,即被行政處罰的未成年人。(四)未成年被害人,主要指刑事、治安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害人。(五)困境未成年人,即因父母服刑、重病等原因造成監護缺失的未成年人。同時,建立聯絡員制度,區公安分局由法制大隊派員擔任總聯絡員,各派出所法制員擔任具體聯絡員,將罪錯未成年人信息及時互通、同步共享。區檢察院對區公安分局作出的涉未案件撤案、不予立案、治安處罰等處理決定進行監督。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區檢察院應當視情、視時提前介入、引導偵查。
2.數字化處遇碼動態評估
檢察機關還應當監督保護處分制度的落實情況,加強對涉罪未成年人保護處分措施的司法化審查,能夠有效防止權力膨脹及濫用,以維護各方主體的合法權益。同時,可以充分利用公益訴訟對相關行政單位不履職的行為提出檢察建議,如校園周邊的食品安全等,從而不斷加強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工作。再者,應當牽頭建立數字化平臺,將罪錯未成年人的信息在平臺上集中統計,并根據涉罪、罪錯、臨界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行為輕重、危害行為后果、日常品行、家庭監護能力等進行綜合評定,根據情況編發紅色、橙色、黃色三類“處遇碼”,設定考察期,并定期根據觀護幫教情況重新評定,實現“處遇碼”動態管理,必要時可邀請心理專家等共同參與。考察期結束,經評定可以結束幫教的,轉為“綠碼”,若有必要繼續考察幫教,可視情延長考察期。數字化平臺同時向家長、婦聯、教育局、關工委等部門有權限地開放查詢端口,家長和相關部門全程參與、監督、反饋幫教效果,形成司法保護與家庭保護、社會保護有效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