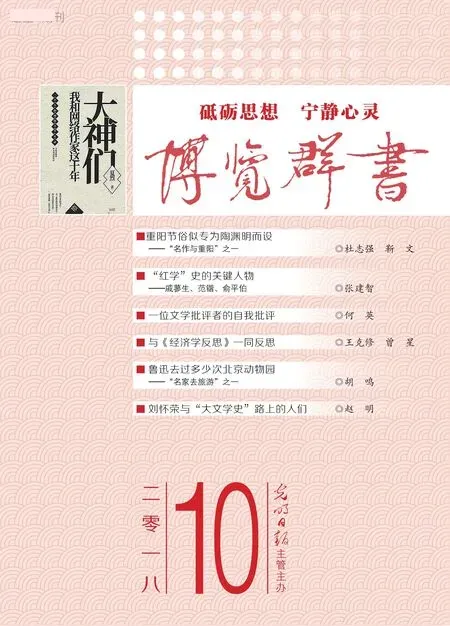向管仲問人性思想
張杰
管仲生活在春秋中期,那時雖然沒有像戰國時期孟子、荀子那樣嚴格意義上的人性理論,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人性思想。管仲的人性思想既是戰國時期人性理論的萌芽,同時又是他輔佐齊桓公所制定的改革內政、稱霸中原政策的理論依據。管仲的人性思想及其作用可分為以下三個部分。
管仲人性思想的內容
管仲生活的春秋時期,人性思想比較流行,這種人性思想與孟子、荀子的人性理論相比,多有不同。
管仲的人性以某些階層的生而即有的欲望、本能為內涵。在中國歷史上,“性”字由“生”字發展而來,“生”“性”多互用。根據《甲骨文字典》,“生”的本義為“象草木生出土上之形”,“性”則指生而即有的欲望、本能等。只不過,在人性理論中,“性”的涵義是指每個人生而即有的欲望、本能,而在管仲生活的春秋時期,“性”指某個人或某些階層生而即有的欲望、本能。《左傳·襄公十四年》載:“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失性”即“失生”,也就是指百姓失去基本的生存條件。《管子·牧民》載:“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惡憂勞”“惡貧賤”“惡危墜”“惡滅絕”卻是齊國百姓生而即有的欲望、本能。
管仲的人性指稱對象不是指所有人,而是指某個或某些階層。孟子、荀子的人性指稱對象是每一個人或者說所有人類。如《孟子·告子上》記載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人皆有之”,即是所有人都具備的。荀子同樣把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惡害等情欲作為每個人所生即有的人性。春秋時期人性的指稱對象則與此不同,它指某部分人或某個階層。《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載:“夫小人之性,釁于勇、嗇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小人之性”很顯然指一部分人的人性。《管子·形勢解》載:“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富貴尊顯”是君主生而即有的欲望。同篇又載:“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欲生而惡死”“欲利而惡害”是普通百姓生而即有的欲望、本能。《形勢解》雖然并非管仲所作,但卻是管仲后學的作品,這兩段話可以看作是管仲人性思想的繼承和發揮。
管仲的人性思想沒有類的規定性。在孔子之前的春秋時期,人們既沒有普遍意義的人性概念,更沒有在此基礎上對人性的善惡做出明確的善惡規定。當時人們往往把生而即有的欲望、本能作為人性的內容。欲望、本能可以變好,也可以變壞,沒有嚴格意義的善惡之分。《國語·周語上》載:“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厚其性”就是厚其生,保證百姓基本生存的意思。《管子·小匡》記載,齊桓公本人認為自己有三個缺點,即好田獵、好酒、好色。而這三個缺點是齊桓公生而即有的欲望或本能。《管子·侈靡》又進一步發揮了管仲的這種思想,認為飲食之欲、侈樂之樂是百姓的基本愿望。管仲及其后學以食、色、田獵、音樂等欲望、本能作為人性思想內容。這些內容本身沒有善惡之別,只在于統治者如何加以引導。正因為如此,管仲主張充分利用人性思想以改革內政、稱霸中原。
管仲的人性思想在輔佐齊桓公改革內政中的作用
管仲輔佐齊桓公改革內政的政策,始終貫穿著兩條主線,一條是滿足齊國百姓基本生活的人性需要,另一條是滿足齊國統治者安定齊國社稷的人性需要。
首先,是以滿足齊國百姓基本生活需要為指導的經濟改革。管仲為了富國強兵的需要,進行了一系列經濟改革。其改革措施包括四民分業定居、改革土地、稅收制度等等。這些改革措施都圍繞著滿足各階層的基本生活所需而制定的。現在就以四民分業定居制度為例來說明這一問題。
春秋時期,士農工商是支撐齊國社會的四大支柱。然而由于種種原因,這四大支柱在管仲生活的時期,都不能安心地生產、生活:農民“不服于公田”,士“不為君臣”,商人“不為官賈”,工匠“不為官工”。管仲輔佐齊桓公進行了四民分業定居制度改革,就是讓這四大階層安居樂業。四民分業定居就是把齊國的士農工商按各階層的實際需要各自集中在一起居住。根據《管子·小匡》的記載,齊國統治者安排士人聚居于臨淄城中的閑靜之地,讓他們閑暇之時研習孝、悌、義、敬等道德禮儀;安排農民居住在郊外的田野,讓他們農閑時置備生產工具,農忙時進行農業生產;安排工匠居住在官府附近,讓他們從事選定優質材料,分辨質量優劣,根據時令需要安排器物用度等活動;安排商人居住在市場附近,讓他們除從事經商活動之外,還進行觀察年景兇饑、了解國內市場、預判市場物價等活動。還有一點比較重要,就是士農工商四民的后代必須世襲其父輩的行業。由于長輩的言傳身教,四民的后代不但會自然學會各種專業技巧,而且還能夠在安心繼承各自的職業,他們不會見異思遷。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記載: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而生存無疑是人們喜好之事。四民分業定居制度無疑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了齊國社會絕大多數百姓基本的生存利益,這是管仲的改革措施能夠得到百姓的擁護的關鍵所在。
其次,以滿足齊桓公富國強兵、長治久安等欲望為指導的政治改革。《管子·大匡》記載,齊桓公在即位之初,就有“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的憂慮。為了徹底打消齊桓公這一憂慮,滿足他作為君主的長治久安的人性需要,管仲輔佐齊桓公進行了以宰相制度、參國五鄙制度、三選制度為代表的政治改革。本文以宰相制度為例來說明這一問題。
齊國的宰相制度始建于齊桓公。春秋時期,齊國的最高統治者雖為君主,但他的權力受到天子命卿國氏、高氏的嚴重制約。國、高兩氏的權力在和平時期僅次于齊國君主。在特殊時期,如內亂、諸子爭位之時,他們的權力直逼君主,有時甚至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君主的廢立。齊桓公在襄公內亂之后能夠順利即位,就是得到了天子命卿高傒的大力幫助。齊桓公即位之后,拜士人管仲為相,使他位居國氏、高氏之上,地位僅次于君主;讓他享有齊國的部分市租,使他“富擬于公室”;尊他為仲父,使他親近無比。齊桓公通過拜管仲為相,在齊國確立了宰相制度,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天子命卿對君主地位的威脅,這在當時對于提高齊桓公的權力、鞏固其統治非常有利。
管仲的人性思想在“攘夷狄而安諸夏”中的作用
如果說滿足齊國百姓和君主的人性需要是管仲輔佐齊桓公改革內政、富國強兵的理論指導,那么華夷之辨則是管仲輔佐齊桓公領導中原盟國攘夷狄、安諸夏的理論指導。
華夷之辨與攘夷狄。春秋時期,由于時代所限,華夷之辨非常流行。由于居住在中原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在生產、生活、語言、服飾、風俗習慣等各方面都與中原民族不同,中原人因而稱自己為華或華夏,稱少數民族為夷狄或戎狄。《國語·周語中》載:“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這說明至少在春秋早、中期,中原統治者認為戎狄等少數民族具有貪婪而不知謙讓的性格,因而并沒有把他們看作自己的同類或同盟。這就是所謂的華夷之辨。管仲生活在春秋時期,當然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左傳·閔公元年》載:“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在華夷之辨觀念的影響下,面對夷、狄等的入侵,管仲輔佐齊桓公率領中原盟國共同抵御外族入侵。這以存邢救衛最有代表性。根據《管子》《左傳》《國語》《史記》等記載,居住在北方的狄人入侵邢、衛兩盟國。當狄人伐邢時,齊桓公雖聽從管仲的建議聯合宋、曹救邢,但齊軍還沒有到達邢國之時,狄人已經攻下邢國,邢人大潰。諸侯盟軍在齊桓公的指揮下驅逐狄人并迎邢國國君至齊國,后又為邢人在夷儀筑城,并遷邢于夷儀。當狄人伐衛之時,衛國君主衛懿公無道,導致衛國都城被攻破,衛懿公被殺,衛國被滅,衛國遺民潰逃至黃河岸邊。齊桓公派軍隊接應他們過河,并在曹地立公子申為君,是為衛戴公,后又派軍隊在衛地楚丘為衛筑城,并封衛于楚丘。齊桓公存邢救衛之舉之所以得到齊國百姓以及中原盟國的支持,這與當時流行的華夷之辨密不可分。
華夷之辨與安諸夏。春秋時期,由于居住在中原的華夏民族在生產、生活、語言、服飾、風俗習慣等各方面都大致相同,以周天子為代表的統治者認為中原諸國是可以教化的文明盟國。管仲也有類似觀念。《左傳·閔公元年》記載,管仲也說,中原諸國互相親近,是不可以丟棄的。正是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作為春秋霸主的齊桓公對于中原盟國的內亂采取了安定的政策。這可從齊桓公幫助魯國平定慶父之亂中得到證明。
根據史書記載,公元前622年,正當齊桓公霸業鼎盛之際,魯國發生了內亂。魯國君主魯莊公去世之后,公子慶父在魯莊公夫人哀姜的支持下,連續弒殺了剛即位的公子般以及下任君主魯閔公。魯人又擁立魯僖公即位,慶父逃亡至莒國,后被迫自殺。但魯國的慶父之亂并沒有完全平息,支持魯國內亂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哀姜逃奔至邾國。在此情況下,齊桓公并沒有趁火打劫,而是先殺哀姜并歸尸于魯,后又派高傒率軍隊幫助魯國平定了內亂。對此,《管子·小匡》記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弒死,國絕無后。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公羊傳·閔公二年》則這樣稱贊此事:“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齊桓公安定以魯國為代表的諸夏之國的內亂,固然有稱霸中原的功利因素在內,但不可否認的是,其安諸夏系列舉動更是受到了華夷之辨的影響。
從人性的角度來看,管仲輔佐齊桓公改革內政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管仲的政治、經濟改革符合齊國君民的人性需求;管仲輔佐齊桓公尊王攘夷的外交政策之所以成功,同樣是符合齊國以及中原盟國的人性需求。管仲的人性思想有其局限性,其滿足君臣人性的需要顯得過于簡單,其華夷之辨的理念更成為一種糟粕,但在當時對齊國富國強兵、稱霸中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作者系山東理工大學《管子學刊》編輯部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