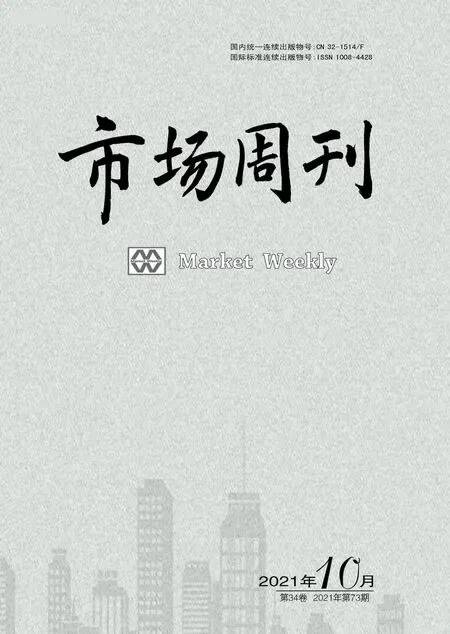企業金融化與系統性風險
徐田陽
(福建師范大學,福建 福州 350108)
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經濟運行呈現實業投資率下降與經濟金融化并行的特征,商品市場低迷而金融市場相對繁榮,伴隨著實體經濟投資收益率與金融投資收益率之差不斷擴大,實體企業積極參與金融市場活動,購買各類理財產品、信托產品、股票、基金、債券等金融資產,通過設立子公司或合營公司進行金融股權投資行為,實體企業金融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甚至呈現出過度金融化的問題。 王營和曹廷求認為近年來我國企業金融化演變過程存在以下兩個特征,在深度上呈現出由低金融化到過度金融化的發展趨勢,在廣度上表現為單個金融化到系統金融化的擴散傾向。
實體企業過度金融化意味著大部分資金在金融系統中內循環而并未流向實體經濟,過度繁榮的虛擬經濟將會催生出資產泡沫,進而可能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爆發。 另一方面,以實體企業影子銀行化為表現形式的金融化行為延長了資金鏈條,掩蓋了金融機構與實體企業之間以及實體企業與實體企業之間交錯變異的金融關聯性,成為金融 “脫實向虛”這一大社會現象的重要表現,而且游離于金融監管體系之外,擴大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蔓延邊界與程度,最終有可能放大來自各種負面沖擊的影響,為金融危機甚至是經濟危機埋下隱患。 面對 “經濟脫實向虛” “資金內循環” 等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 “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
二、文獻綜述
系統性風險并非獨立的風險,它具有全局性、傳染性、順周期性、負外部性、緩積急釋的非線性和非對稱性特征。 目前對系統性風險還沒有統一的定義,學者們主要基于傳染性和負外部性特征,從金融機構、金融系統、實體經濟三者之間的相互沖擊來定義系統性風險。
關于對金融系統性風險的研究,現有文獻主要分析了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信托業、多元金融等金融子行業對金融系統的沖擊,以及各金融子行業之間的風險溢出效應及其影響因素。 從研究結論看來,大部分文獻認為銀行業的風險溢出效應最大,并且機構層面的因素,如規模、杠桿率、期限錯配、融資融券等能夠影響到其系統性風險溢出效應。 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學者從泛金融部門角度研究金融系統性風險的溢出效應,比如翁志超和顏美玲測度了互聯網金融對銀行業的系統性風險溢出效應,孫翎等分析了我國房地產業對各類金融子行業的系統性風險溢出強度。
當前,已有不少學者認識到實體企業金融化將會增加金融系統性風險。 根據王永欽等的研究結果,過度金融化的非金融企業違反了融資優序理論,這些企業的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呈現正相關關系,并且企業存在向民間再放貸的行為,企業的金融資產負債特征與金融機構趨同。 李建軍和韓珣發現企業金融化表現出企業的影子銀行化,非金融企業通過直接充當信用中介和間接參與信用鏈條兩種方式參與影子銀行活動。 彭俞超等認為實體企業過度金融化將會顯著提高股價崩盤風險,在錯綜復雜的直接或間接關聯下,有可能導致整個股市的崩盤,最終引起系統性風險的爆發。隨著對系統性風險認識的加深,部分學者將注意力轉向實體經濟行業的風險傳染效應,比如楊子暉和王姝黛發現在行業下行風險的傳染過程中,部分實體行業風險溢出效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存在較強的解釋力。 翟永會通過實證檢驗了實體行業與銀行業之間存在顯著的系統性風險溢出效應,認為在系統性風險的管理中不僅應關注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還要注意到系統重要性實體行業和系統脆弱性實體行業的影響。 周亮從靜態和動態兩個方面,對我國9 個行業的系統性風險溢出效應進行了考察,結果發現,各行業間的系統性風險溢出效應均存在較強的相關性,并且材料行業積累的系統性風險最高。
綜上,現有文獻大多研究傳統金融機構或金融子行業的系統性風險及其溢出效應,而忽視了在實體企業過度金融化的背景下,企業行為表現出金融機構行為特征,這些過度金融化的企業實質上是類金融機構,它們加深了金融機構與實體企業之間以及實體企業與實體企業之間交錯變異的金融關聯性,并且更有可能成為系統性風險的傳染源,但現有研究并未考慮到金融化企業的系統性風險及其溢出效應。 另外,盡管實體行業與金融行業之間存在風險傳染效應已經不斷得到證實,但從微觀實體企業視角考察系統性風險傳染網絡和傳染路徑的研究依然較為匱乏。
三、理論分析
(一)企業金融化與系統性金融風險
對于單個企業,其金融化動機存在多樣性,蓄水池理論、投資替代理論、實體中介理論、實物期權理論、跨國公司避稅理論、股東價值最大化理論等從多個方面解釋了企業從事金融活動的原因。 一般認為基于預防性儲蓄的金融資產配置行為能夠改善現金流量波動、降低財務風險、緩解融資約束,進而促進企業的實業投資;而基于替代性投資的金融配置行為將對實體投資產生 “擠出效應” 、損害企業創新能力、降低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增加經濟的不穩定性。 近年來大部分學者的研究表明實體企業的 “投資替代” 效應大于 “蓄水池” 效應,即企業金融化的主要目的是投機套利而非預防性儲蓄。 因此,當企業基于投機動機涉足金融活動從而取得較大的利潤時,同行業、同地區、同社會關系的企業會模仿并學習其他企業的金融投資決策,從而導致金融化現象在實體企業中傳染擴散,造成實體企業 “脫實向虛” ,形成系統金融化局面。 由于實體企業和金融機構之間并不是獨立的,兩者之間存在著各種形式的業務關聯或投資者關聯,加之金融工具大多經過標準化設計,具有較高的同質性,當金融化實體企業或金融機構一方出現問題時,其通常會通過金融網絡和社會關系網絡對關聯部門甚至整個行業產生負面沖擊,這種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之間的正向反饋機制導致系統性風險在實體企業與金融機構之間傳染,而企業金融化行為無疑加劇了這種負面沖擊發生的概率與沖擊效應,使得來自實體企業部門的沖擊更容易演化成系統性風險。
具體來看,企業配置過多金融資產、發放委托貸款、投資金融股權等金融化活動將會使風險通過資金、預期、信貸等渠道傳導至銀行市場、股票市場、影子銀行市場等。 資金渠道指金融機構與實體企業之間以及實體企業與實體企業之間通過存貸關系、支付關系等形成的資產負債表關聯關系,一家企業的危機可能會通過此渠道引起其他企業的流動性危機或信用危機,造成信用風險逐輪外溢。 預期渠道指面對局部風險事件,投資者之間的恐慌情緒會相互傳染從而非理性地做出集中拋售或者贖回行為,導致風險快速擴散。 由于股票價格表現與企業經理和股東利益息息相關,企業經理為了個人私利,報喜不報憂,會通過粉飾報表、平滑利潤的手段,比如進行各種金融投資活動,達到向外界隱藏有關主營業務壞消息的目的,這種行為增加了股票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 隨著上市公司所掩蓋的負面消息越來越多,積累的風險越來越高,一旦超過某個限度,壞消息集中釋放,就可能導致股價崩盤風險的爆發。 為規避風險,投資者會賣出相同行業或相同投資者關聯的股票,恐慌情緒引起下一輪的股價暴跌。 信貸渠道指由資金渠道和預期渠道引起的流動性緊縮推動銀行和具有 “金融中介” 功能的實體企業收縮信用規模,引起企業融資成本上升、投入產出減少,導致資產負債表的惡化,然后不斷重復上一次的沖擊過程,使小沖擊最終演變成大波動。
(二)基于實體企業過度金融化的系統性風險形成機制
企業配置各類金融產品能夠降低自身風險,提高收益率,屬于分散化投資,是個體理性行為,但是實際上這種行為并沒有消除風險,只是將風險轉嫁給了集體(系統),將大概率損害個體收益的風險轉換為小概率危害群體的風險。 隨著過度金融化、系統金融化的到來,大多數企業包括金融機構都將風險轉嫁給了集體,這種獨特的風險分擔機制使系統性風險不斷積累,最終導致系統的崩潰。
相比金融機構,實體企業的資產管理能力和風險防控能力相對較弱,如果經濟遭受到較大的負面沖擊導致資產價格初步下降,特別是在經濟下行期間企業普遍預期不足,會拋售金融資產以防止資產出現較大貶值,并且這種行為是多數企業的選擇,集體的集中拋售造成資產價格的進一步下跌,此時恐慌情緒開始蔓延進而產生 “羊群效應” ,接著企業財務狀況惡化,此類風險通過上述資金、信貸、預期三個渠道造成銀行壞賬率提高、股價下跌,使得銀行系統性風險和股市系統性風險上升。
除了持有金融資產,實體企業金融化行為還表現為開展影子銀行業務,如委托貸款、民間借貸、購買銀行理財等。 相比中小企業(借款企業),上市公司(貸款企業) 信息不對稱程度低、抵押品豐富、銀企關系好,因此能夠以較低的利率獲取銀行貸款,并且通過合規或不合規的方式將從金融機構獲取的資金以較高的利率投向中小企業,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但卻提高了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加重了企業債務負擔。 中小企業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一次較大的外部沖擊可能會造成一大片中小企業違約,導致上市公司發生損失從而選擇退出影子銀行資金鏈條。 這將會造成兩個后果:一是融資約束加強再一次對中小企業產生影響,重復沖擊損失過程;二是由于影子銀行內的金融產品往往經過多重嵌套,并且杠桿率高企,資金突然退出可能引起某個資金鏈條斷裂,產生風險的連鎖反應,通過金融加速效應的作用在金融行業內傳導擴散。 系統性風險形成機制如圖1 所示。

圖1 系統性風險形成機制
四、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將高度金融化的類金融機構納入監管框架,分機構類型進行監管。 監管部門需要根據銀行、證券、金融化企業三類機構的內在差異性,有針對性的選取不同的監管目標、政策工具。
第二,繼續實行減稅降費等政策,大力支持實體經濟,同時應規范企業金融投資行為,加強企業金融風險防范意識,防止企業利用負債融資進行金融投機行為。
企業金融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實體經濟收益率偏低,過高的金融投資收益率對實體企業產生逆向激勵,即勞動不能致富,促使企業資金不斷投入虛擬經濟,結果是實體企業逐漸脫離主營業務,轉變成為類金融機構,成為非金融部門的系統性風險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