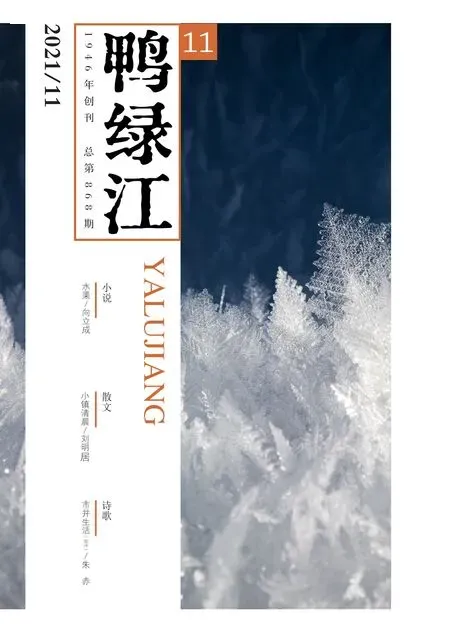青石
潘科羽
我們在水邊下車,過橋,又上山。步行的山路鋪著平整的石塊,因為常有人走,所以道路兩邊并不荒。松葉間墜下的陽光養不活太多低矮的植物,只有一些苔蘚類植物溫順地伏在黃土上,石板粘著青苔,呈現出恬淡的綠色。年深月久,石板與土地的連接就更為緊密、穩定,輕易不被撬動的。
翻過這座山,眼前豁然開朗,積水的梯田有序地排列在山野,秧苗滴綠,田埂蜿蜒,其間有疏水的大洞,幾塊石頭搭在上面,供人和牲畜通行。田埂盡頭便是農家的曬壩,媽說我們家有前后兩塊壩,給我指了個方向。果然,不遠的那一戶走出來一個老人,看到我們,很是親切地招手。媽說那是外公,我說我記得。
很久沒再來,人和房屋都已不同于我的印象。他們不年輕了,石砌泥筑的房屋也塌了一半,聽說很早的時候就已見破損,每逢大雨,瓦片缺漏之處就像水龍頭擰開一般,嘩嘩地往屋里沖水。家里有幾個大盆,專為雨天接水。然而物有定壽,補救也無大用,終于在前幾天的一場大雨后,老房子支撐不住似的發出一陣嘆息,前院的泥屋子垮了,還剩下另一半石砌的瓦房孤獨地挺著脊骨。
塌掉的是牲畜用的房屋,沒傷到人,這個季節也沒養什么牲畜。墻倒屋塌,卻似一聲警鐘,把家人之間有意避而不談的一串分歧敲到了明面上。我媽本想連著另外一半房屋都放棄,帶著外公一起到城里住,外公卻想把那一半修起來,即使身邊無人,他也愿意一個人守在這里。一個人守在這里做什么呢?我媽不理解,反復地勸,還是改不了老人的想法。
我印象中的外公原是隨和可親,會聽孩子話的,從來不知道他竟然有如此頑固的一面。我小時候因家長出差,在外公家住過一段時間。山里交通不便,物資也缺乏,去最近的集市要走五六里的山路,我貪吃,卻又不想走路,外公就用籮筐挑著我,打著手電走山路。天蒙蒙亮,頭頂還有幾顆星子,蟋蟀唧叫著在路邊的草叢中跳來跳去,我坐在籮筐里,那種感受很奇妙,我聽見外公踩石板上山時發出嗯哼的調子,音調獨特富有節奏,每哼一聲,他那強健的肌肉都會迸發一次力道將扁擔往上頂撐,難行的山路,被他走得輕捷又穩當。
我在籮筐里待到它再也裝不下我,這中間的一趟又一趟市集路,都是被他的縱容和溫柔抬過去的。原來順著孩子的人,一直只是一個很有力氣的孩子。他自顧自地重復著,好像眼睛耳朵都閉了起來,任別人說什么都不理會。
“我能吃飯能干活兒,我要誰管我?”
“大不了就是死,我還怕死嗎?”
……
聲音像是石磨盤拉出來的,因為急著講出,顯得欠考慮而缺底氣,可是他的意志卻如山巒一般穩重在這里。我好像又聽到那種哼聲,那是刻在骨骼里的固執。
時間讓很多東西老舊,也讓一些東西變新,它可以拉開一條鴻溝,使相望的雙方重新認識。聽說以前難行的山路現在建了車道,已經有專線往返村莊和市集。外公說是,車也坐過,但他還是更喜歡走。山里總也沒有什么大事,時間可以拉長了放緩了用,一腳一腳地走路也變成了一種樂趣。只是現在走路再也不需要他用盡全力,他也的確不年輕了。
媽也只好松了口,說現在比以前方便多了,反正通了車,有什么事我們也可以隨時回來。外公說:“嗯,方便。”多虧了這樣一個方便,老人的意愿最終得到了滿足,子女答應出資修繕舊宅,也不再提要強行帶他去城里的事。
老人立刻愉快起來,油鹽不進的頑固狀態一瞬間就被他收起,他又恢復到以前那溫純好說話的模樣。對新建房屋的事沒有太多意見,能遮風避雨就好。
我們陪他吃飯,商議了許多建房事務,又告訴他許多獨居需要注意的事,他心愿已了,十分聽話,樂呵呵地照單全收。我們走時,他站在屋外送我們。天色已晚,太陽快要落到山的背面。我走出好一段路,回頭一看他還在原地,幾乎要和石屋融為一體,笑容是深青色,在寂靜的余光覆蓋的山巒里漸漸黯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