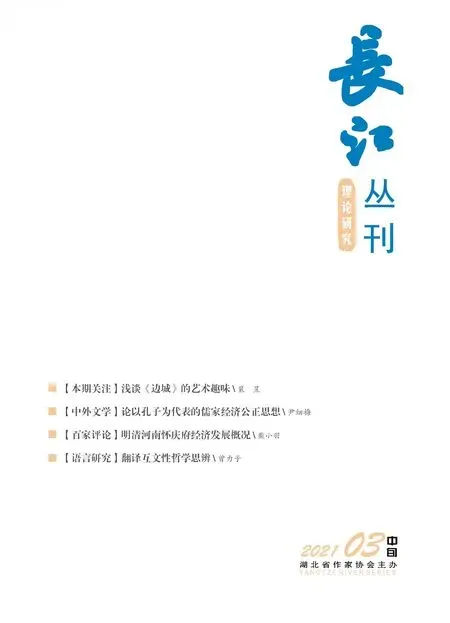翻譯互文性哲學思辨
■曾力子/邵陽學院
“翻譯是一種詮釋”為哲學家將翻譯置于詮釋學考究范疇所興觀點。中國古典譯論所述“文與道”、“言與意”一方面說明內容與形式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強調理解與表達之重要性,表達屬解釋說明一種方式。西方第一個將詮釋學作為理論引入的施萊爾馬赫將詮釋學規則分為“語義學”部分和“心理學”部分,可見文本與心理早已開始對話。理解在歷史發展長河中,人們對翻譯的解讀多樣且不斷變化,但終究未能脫離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轉化活動。文本作為一個存在客體在經譯者主體能動解讀之后可能會帶來完全不一樣的視域效果,正因為如此,翻譯被部分譯者認為是一種再創造,如林紓、嚴復的翻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原作。毋庸置疑,在對文本語言進行解釋時,作者與譯者之間的心靈碰撞產生的輻射電波對理解文本并轉換文本影響深遠,所有這些錯綜復雜的關系被視為一種互文。在這些翻譯哲學命題中,互文性誕生的時代背景,以文本為中心發散的次文本、文化、文體、主體等諸多要素的參與產生了哲學火花。
一、翻譯中的互文性
法國符號學家朱麗婭·克里斯蒂娃在譯介研究過程中獲得靈感,提出“互文性”概念,認定任何一個文本都是在它之前文本的遺跡與記憶的基礎上產生的,或者是吸收其他文本并轉換而成的。從一個文本到另一個文本的傳遞與過渡是一種轉換,無論發生語際還是語符,都離不開翻譯與創作。翻譯首先出現在語言之間,語言由數不清的符號組成,言語與符號指稱早已為譯者和觀眾所共知共享,即便非言語翻譯,其原則與規約也已預先支配,這些前提可視為認知互文要素。如互文性類型所述,互文本有隱性與顯性之分,預知文本即便只是架空投射在大腦,作為語言轉換的翻譯行為也必須恪守其內在指令。
普通意義上翻譯過程必須包括原文、譯者、譯文,兩個文本之間嫁接程度取決于譯者心理承負能力。從原文解碼到譯文編碼,整個過程中譯者首先會探析并解讀原文文本,直接文本顯然是眼前可觸摸可閱讀作者所著文本,然這只是語言符號顯示的狹義文本。譯者承載的文本概念在轉換過程中得以拓充,一方面他不僅要熟悉字面意義對應文本,還要走入作者心理,傳遞文本內容,實現作者意圖;另一方面,譯者需透視文本文化,嵌入自我意識,考慮讀者反應和譯本效果。個體在構建翻譯文本時集過往體驗、閱讀感受、文本互動、語言文化內涵于一體,充分發揮自我認知并重新書寫翻譯。這些無形卻寬泛概念引入文本之中拓寬了互文要義,翻譯目的、局限、個體意識、社會價值不斷涌現,隨著翻譯理論不斷革新并順應社會發展,翻譯行為也走向多級。正如羅蘭巴特所言閱讀即讀者與作者之間的一次對話那樣,
互文心理非常關鍵,翻譯過程中譯者承擔雙重身份—原作的讀者與譯作的作者,他將譯文讀者與原文作者串聯,使得互文要素從原作—譯者—譯作三重走向原作—譯者—譯作—讀者—批評者五重關系。顯然,參與要素主體性的延伸強化了互文內涵,也為互文在翻譯中的作用彰顯帶來了契機。
文化傳譯過程中抵制性翻譯引入的政治強權與殖民風暴將翻譯帶入了全新多元互文場中,語言文化、意識形態、政治關系、歷史傳統、心理重構融入翻譯使得互文要義形成龐大交錯集合。翻譯中的諸多技巧策略如直譯意譯、歸化異化在具體語境下的使用也是互文映射,其與互文性策略改寫、模仿、挪用等雖義之深淺有異,意之精髓一轍。勒弗維爾界定翻譯是為構建他者,譯者可以操控翻譯,提出翻譯首先要考慮的是“認知網格與文本網格的相互交織”,由此可見,翻譯是意識與文本的互聯,這種網格聯系與各種形式翹首相望的文本達成一致,系統交織雖不停留于現場文本,但包羅萬象的關系網絡正是互文性潛在文本痕跡,吻合多元互文無處不在之現實。
不僅如此,在真實文本中的翻譯互文性也隨處可見,尤以譯著文本為盛。林語堂列此類文本創造者之首,譯著作品豐富。除去《京華煙云》以小說體形式展示中國變革時代人物的生活命運,《生活的藝術》用悠閑筆調樹立傳統中國人愜意情調的美好生活,入木三分折射平民快樂哲學。《吾國與吾民》則以靜觀犀利語言描述了作品誕生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哲學等與中國人的性格、心靈、理想、思維等。雖然這些作品都是以英文的形式展現于外國讀者,但無論是文化負重還是語言承載都與中國歷史傳統與社會發展呼應互文。
二、互文性中的哲學
互文性雖以符號學衍生,基于巴赫金“對話”、“復調”與“狂歡”等文學理論,其發展與研究領域正向多極發散。互文之關鍵在于一種相互關系的自發或者有意識所為,其誕生背景,主要表現形式,內含反思均體現了哲學意味,力證為哲學闡釋。
(一)互文緣起進化順應哲學
普遍認為互文理論誕生于一種后結構主義與后現代解構模式下,它重文本與社會關系,去文本中心,破邏格斯中心,其靜態出身迎駕文本背后的動態發展過程。無可否認,互文的前提是文本,克里斯蒂娃所示“互文性”雖以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符號為藍本卻超越了前結構主義思想,承襲了巴赫金“對話”思想與“復調”之論。巴赫金用馬克思意識形態將語言作為具體語境和社會環境背景的一種實踐,凸顯了讀者或他者反應,尊重不同聲音,形成動態歷時傾向,鑄就了巴氏時空體。“話語是一種獨特的意識形態現象”,對話就是為了嫁接這種關系,以此得出“話語是說話者與聽話者相互關系的產物”。雖然巴氏沒有明確提出“互文性”這一概念,但是其詩學研究從形式走向社會,融入了歷史與現實的觀照,哲學萌態了然。
互文性為文本相互的指稱是不爭的事實,而這種推己及人的文本關聯完全符合哲學萬事都相互聯系之觀點。羅蘭·巴特提出作者之死,讀者中心,讀者在閱讀中所傳遞的意識、話語期待、文本反饋對文學及話語批評分析帶來了福音,自我與他我的消長關系授予其觀點哲學光環,將互文概念泛化。
隨后熱奈特將互文性概念進行系統理論建構,著眼文本整體,提出“跨文本性”并將其分為五種類型:文本間性,副文本性,元文本性,承文本性,廣義文本性。這一劃分將引用、評論、派生、模仿、類屬等手段具體運用于互文研究中,對之后業內學者對互文類型分析產生導向作用。
互文產生的解構時代背景與不斷發展演變歷程既是對哲學唯物史觀的順從,是辯證觀的明證,承認文本之間聯系并聯接主體個人意識也是能動觀的演變,理論辯證推進思維方式為理論的后續研究提供了開放空間,尊重實踐—理論—實踐的辯證循環。
(二)互文類屬形式表現哲學
互文理論作為文本理論最初用以服務文學批評,此后被不斷運用到語篇分析、語用解讀與翻譯研究,尤以翻譯為最。互文的類型之分也眾說紛紜,各有說辭。創始人克里斯蒂娃將互文性分為水平互文和垂直互文,之后強弱互文,主動與被動互文,表層互文與深層互文,廣義與狹義,自與他,隱與顯等相對概念互文名稱相繼出現。這些互文分類分別體現了語言哲學的歷時與共時觀,表現形式程度差異觀,文本語段與認知心理雜糅觀。
具體常見互文方法包括改寫(adaptation),引用(citation),用典(allusion),戲仿(parody),糅雜(pastiche)。改寫主要發生在文體變化與多媒體涌現時代,如將文言文轉換成現代文,詩歌體轉化為章回體,或者將文本小說改編成電影、話劇等。內容相同而外在形式多樣,可以理解為多個形式表象反應同一個內容實體之間的辯證關系。引用分為直接引用與間接引用,直接引用一般都有引號或文中標注,一目了然,而間接引用則需讀者有一定的文化轉借能力和豐富的詮釋經驗。用典是借用國家特有文學故事和史實,讓雙語讀者產生簡明具體、委曲含蓄效果。引用與用典兩種互文手法都是基于歷史文本,從過去傳遞到現實,引用不一定是典故,只求順應文本再度書寫所需,典故卻代表著本民族的某種精魂,以典譯典,尋求雙語之間最貼切的效果對應。萬物都可追蹤溯源,尋求本源之舉正是唯物辯證之法,引用與用典即為正視并證實起源的互文方法。根據美國傳統詞典釋義,戲仿是“模仿作者獨特風格的文學或藝術作品,或為喜劇嘲笑效果而創作的作品”。以已有文本為綱進行意識性仿擬是尊重事實與主觀能動性極致發揮的結合,也是客觀事物變化發展的具體表現。糅雜將個體融合,整體參合個體,讀一個文本,盡可尋萬千子集,互文意蘊表現了整合觀。
(三)翻譯互文過程內化哲學
通過互文緣起、發展、分類、表現形式等多方考究,互文作為文本理論輻射跨學科研究優勢非一般理論所及,其用于翻譯研究內涵運作與哲學關聯千絲萬縷。無論是中國古典譯論還是西方翻譯理論,都折射著哲學光環。中國古代樸素哲學對言意之鑒定彌漫著互文氣息。老子有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為“道法如若可言,只是平常道法;名號若可定,只是平常名號”。由此可推“能指與所指只存在于一般意義,不存在于永恒確定之中”。西方互文性歷史可以追溯到哲學家柏拉圖。沃通與斯蒂爾將柏拉圖與蘇格拉底對話作為互文研究首選材料。柏拉圖與學生亞里士多德都提及摹仿,注重普遍聯系之真理,互文意味較為明顯。相互關系更是是一種互文、補充、取代甚至原創時更兼翻譯效能。
文本本身具有實踐性與產出性,引入互文性理解賦予文本更多不同的聲音,而這個聲音就是讀者闡釋的結果。王寧認為“翻譯是作為一種以語言為主要媒介的跨媒介闡釋”,這是他關注新媒體時代特征的感言。從語言到其他媒介的轉換,翻譯文本的種類與范疇發生了改變,個體闡釋必要性尤能凸顯。哲學闡釋從現象到批判,文本主體與譯者主體間性的關系與權重也悄然變化。從主體間性到文本間性實則為闡釋視角差異,并未脫離互文要義,前者謂主體互文,重認知內隱,后者為客體互文,重真實外化。譯者承擔的任務是在文本內外關系中進行文本對接、語言轉換、知識轉移、經驗傳遞等活動,做到合情合理解釋,不折不扣翻譯。海德格爾闡釋的無盡循環論為首尾呼應互文本、翻譯中的復譯等論調鋪墊了哲學根基。理解是闡釋的前奏,闡釋是理解的結果,從個體思維認知到闡釋共享,使意識走向存在,局部邁向整體。
維根斯坦提出“語言游戲”之概念,認為“翻譯是一種語言游戲”。語言游戲實則重“用”,而“意義即為使用”,意義成了語言哲學的核心,且為翻譯互文理解焦點。要獲取真實準確意義,在互文性觀照下,文本之外顯性或隱形實體作用于語言要素,帶來主體人相應思維與行為,轉換為翻譯文本,切合了人對文本意義的認知。翻譯承擔的語碼轉換具象為某種符號,本質為意義譯語重構。劉宓慶對意義的哲學解讀分為指稱論(Reference theory)、觀念論(Ideational theory)、語用論(Use theory)、指號論(Signs theory)。中國古代意義指稱“名與實”、“物與象”代表古老樸素哲學,暗示概念內涵與外延的多面性,實體性與整體性在翻譯解讀意義時被提升至特定語境與時空交錯之中,帶來了指稱的定與不定,為互文翻譯無定法提供了哲學依據。觀念論意義重譯者感覺與認知,一切意義都是心理過程的映射與聯想。互文翻譯譯者走入作者心理過程便是意向探尋過程,同時也凝結自我翻譯心得體會給譯語讀者,意向觀念依次互文傳遞,完成意義功能:譯有所意。語用論與指號論被越來越多地運用到言語行為與隱喻翻譯中,前者關注語言用途,話語雙方心領神會與預測行為在一定范圍內是可控的,是主體文本與客體文本相互交涉互為所為,后者則強化符號的相似性,引發了翻譯的隱喻研究,客體文本互文在修辭格中穿梭,意義得以幡然。
操縱學派主要代表人物勒弗維爾指出所有的翻譯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對原文有目的的操縱,由此強化了譯者主體權力。隨著解釋在不同階段不斷循環,以話語建構的權力之爭也在翻譯研究中形成了新的鏡象。權力話語是福柯社會哲學理論中最凸顯的成分,他眼中的權力不是恒定不變的物的概念,而是一種關系。福柯對“話語與權力”的思考本身體現一套不同于西方主體哲學的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批評話語分析的跨學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福柯權力話語觀點,話語成構社會關系與行為,使得翻譯的社會學意義更加凸顯。在多元文化交互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環境之下,翻譯互文哲學意義也將走向另一個高度。
三、結語
互文即關系,本文從語言與哲學,語言與翻譯,翻譯與互文,互文與哲學等關系梳理中樹立哲學思辨之理念。無可否認,現代語言翻譯理論源于哲學沉淀與實踐循環,文本引領翻譯重言語,重理解,重意義。隨著大腦認知科學發展,認知詩學成為一種交接背景、圖式、原型范疇、心理掃描、文本世界等于一體的綜合研究趨勢。世界普遍聯系但矛盾主體不斷彰顯的辯證哲學在互文性翻譯理解中占據鰲頭,翻譯中互文的無處不在,互文中關系的交錯不已,關系中主客體疊疊不休也給現代哲學帶來全新理論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