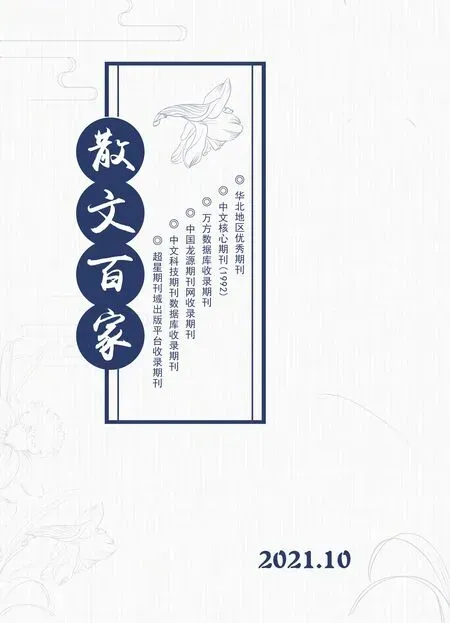論書法抒情觀的文化淵流及其歷史建構
季旭東 蔡志偉
蘇州三元美術館;南開大學藝術與美學研究院
中國的詩、歌、舞與書畫素有抒情傳統,皆重于通過藝術媒介表達、顯現主體的情感與心性。較之詩、歌、舞,書畫藝術的抒情觀念相對晚出。然而,當抒情觀念被引入書畫藝術并獲得理論自覺以后,其就成為了書畫創作與鑒賞活動的重要美學面向之一。僅就書法藝術而言,“心”“意”“情性”的抒發不僅具有極高審美價值,而且具有美學本體意義。本文旨在考察書法藝術中抒情觀念的文化淵流與歷史建構。
一、先秦之“樂”:文藝抒情傳統的思想文化淵流
中國文藝的抒情傳統,淵流于先秦之“樂”——詩、歌、舞。
在禮樂背景下,儒家強調樂教(詩教)在個體人格完善與社會禮法構建中的重要作用,所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在儒家看來,“樂”之所以能在人格構建與社會風化中起到如此功效,其因在于“樂”發之于人心、貫之于人情——“樂”的抒情性。
孔子對于詩樂有過諸多論述,其認為《詩》有著“興”“觀”“群”“怨”的功能,即能夠“對人的精神從總體上產生一種感發、激勵、凈化、升華的作用。”這實則是從審美欣賞角度側面揭示了詩樂的抒情本質。關于詩樂的抒情本質,“詩大序”曾有一番正面論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序·卷上·大序》)這里認為,“樂”的三種形態——詩、歌、舞皆以“志”“情”為根底,乃是主體文化生命狀態的外在顯現。
對于“樂”的抒情本質,荀子展開了進一步論述: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荀子·樂論》)
這里明確提出,“樂”與“情”有著直接聯系,亦即是將抒情視為“樂”的本質。在其看來,“樂”中之“情”源自主體生命的內部涌動。當這樣一種生命律動獲得動靜相宜的藝術形式時,便能夠將內心的種種波瀾加以顯現,并且取得澄汰心志、節制感情的凈化作用,完成“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的社會功能。
這種思想在《樂記》中得到了系統性的闡發: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樂記·樂本》)
由于樂音起于人心與外物相接時所產生的“情”,故而當其獲得一種合乎倫理規范的藝術形式之際,就能將外在于人的道德規范內化為人的自覺追求,所謂“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樂記·樂化》)。值得注意的是,《樂記》在荀子分別“情”與“性”的基礎上,進一步說明了“樂”中之“性”,即“人產生情感的能力”。如果說“情”展現的是人心之殊相,那么“性”則對應著人心的共相。概而言之,儒家以道德倫理為中心論述了“樂”的抒情本質,其將“樂”視為一種源出“心”、顯現“情”“性”、且合乎于倫理規范的審美實踐與藝術形態。
道家對于“樂”似乎頗有微詞,老子有言:“五音令人耳聾。”(《老子·十二章》)然則須知,這種反對意見主要批判的是將“樂”作為社會生活的多余矯飾。事實上,道家不僅同樣注重“樂”之于人的重要意義,而且還為“樂”之“情”開拓出了一種超越維度。《莊子》中有這樣一則寓言:
南郭子綦隱機而坐,仰天而噓,苔焉似喪其耦……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不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子游曰:“夫天籟者,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莊子·齊物論》)
從這則寓言中可以見之,與儒家樂教面向道德社會的完善建構有所不同,莊子將“樂”視為與“道”相通的媒介之一。造成這種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儒、道兩家對于“樂”之本質——“情”的理解存在差異。
一般認為,莊子是“無情”論者,所謂“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莊子·德充符》)然而,莊子所謂的“無情”并非是對于“情”的根本舍棄,而是要求割舍非“自然”意義層面的“情”。對于何謂“無情”,莊子有過明確闡發:“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莊子·德充符》)由此可見,莊子所謂的“無情”就是“因自然而不益生”,遵循或者返回人心的本然狀態,而不主張人心在與外物相接時出現各種變化,所謂“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莊子·養生主》)這與儒家所說的“情”“感于物而動”截然相反。
同時,莊子所謂的“無情”又與儒家所謂的“性”具有一定相似性,荀子即認為:“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荀子·正名》)但是,不同于儒家將“性”視為“情”的原初態與推動力,莊子的“無情”恰恰是要否定、超越“情”。正是由于否定并超越了作為殊相“情”,故而“無情”就顯示出一種與天地萬物相往還的“大哉”境界,所謂“謷乎大哉,獨成其天。”(《莊子·德充符》)如是可說,莊子所謂的“無情”實為一種面向“道”、具有超越性質的“大情”;道家之“樂”并不著眼于如何凈化“情”,而是要將“大情”鼓動,使人由此進入超越境界之中,這是道家對于“樂”之抒情本質的獨特闡發。
在詩樂抒情問題上,屈騷與儒、道兩家皆異。如果說儒家之“樂”是情感有節制的抒發,那么屈騷則是情感極強烈的噴涌;如果說道家之“樂”旨在超越有限的“情”而去感悟無限的天地境界,那么屈騷則利用宗教式的迷狂實現了人與萬物的通靈。李澤厚先生曾經寫道:“《離騷》把最為生動鮮艷、只有在原始神話中才能出現的那種無羈而多義的浪漫想象,與最熾熱深沉、只有在理性覺醒時刻才能有的個體人格和情操,最完滿的融化成了有機整體。由是,它開創了中國抒情詩的真正光輝的起點和無可比擬的典范。”“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緒、無羈的想象在這里表現得更為自由和充分。”更加值得品味的是,屈騷之“情”與儒家的中和之“情”以及道家的超越之“情”,在性質上有著根本不同,其構建了一種悲情主義——“這些不勝枚舉的‘情’字毫無掩飾地披露了屈原的好、惡,喜、怒、哀、樂,其情感的基調是哀傷、沉抑和悲憤的。”
先秦時期,儒家、道家與屈騷對于“樂”之“情”的闡發與表達,共同構成了中國文藝抒情傳統的文化淵流。正是在這一傳統中,書法藝術逐步形成了抒情藝術與抒情模式。
二、“書為心畫”“任情恣性”“心手達情”:書法藝術抒情意識的萌生與確立
書法藝術的抒情意識萌生于西漢時期,其標志是揚雄的“書為心畫”說:
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面相之,辭相適,捈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法言·問神》)
應當看到,在揚雄這里,“書”已不僅是記載言論的表意文字,而被視作一種既能記載言論、又能傳達情感的藝術化媒介。若以《易傳》有關“言”“象”“意”三者關系的闡發作為參照坐標,揚雄所謂的“書”已超出了“書不盡言”之“書”的范疇,而進入了“立象以盡意”之“象”的領域。正是在“象”的意義上,在“象”與“意”的連通意義上,揚雄才有所謂“書為心畫”的說法;也正是這種“聲”之“畫”、而非“聲”之“形”才能實現一種“動情”效果。
然而不得不說,在書法藝術并未真正自覺的西漢時期,揚雄的“書為心畫”說雖然已經點明了書法藝術的抒情功能——“動情”,但是尚未將“情”作為書法藝術的美學本體加以看待。這種觀念的出現與確立,不僅與書法藝術的自身發展相關,更加與個體意識的自覺程度相關。
東漢是個體意識逐步自覺的時期,也是“情”被確立為書法藝術美學本體的時期。就某種程度而言,“情”的自覺是個體意識逐步自覺的關鍵標志,這在漢末魏初劉劭的《人物志》中表現得十分明晰,如其云:“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剛柔明暢貞固之征,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夫色見于貌,所謂征神。征神見貌,則情發于目。”(《人物志·九征》)在這種對于“情”的高度關注中,“情”也隨之被視為書法藝術的美學本體所在,其標志是蔡邕的“任情恣性”說:
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后書之;若迫于事,雖中山兔毫不能佳也。(《筆論》)
這里,蔡邕將“任情恣性”作為進行書法藝術創作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說,他將書法藝術視作一種個體在內心虛靜狀態下情感的自由流露與自在顯現。蔡邕的“任情恣性”說既受到了道家“滌除玄覽”“心齋”“坐忘”等思想觀念的影響與啟發,也將屈騷所綻放、洋溢出的無羈恣肆之風包容其中。盡管這兩種抒情傳統有著不同的精神旨趣,但是在個體生命顯現層面卻具有一致性。
魏晉南北朝時期,“情”是哲學、美學的中心概念之一。王弼認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西晉文紀·卷五》)宣稱理想人格是“神”與“情”統一。在其看來,“神”“能體沖和以通無”,與宇宙本體發生關聯;“情”則使人“哀樂以應物”,與天地萬物產生情感共鳴;理想人格的完善塑造,有賴于“神”與“情”的相互交融。受此影響,“神”“情”成為當時人格審美的重要概念,并被進一步引入自然審美領域。至此以后,“情”深入到了審美意識之中,成為審美創造、審美欣賞的重要范疇,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劉勰“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之說(《文心雕龍·神思》),這可看作是對魏晉乃至自古以來文藝活動抒情傳統的一次高度概括。
在這種重“情”的思想、審美氛圍中,書法藝術對于“情”的重視便是題中之意。在魏晉南北朝書論中,諸如“心”“意”“心意”“思”“胸中”范疇等都與“情”的內涵基本一致,皆表達了書法藝術乃是因情而動、緣情乃發的抒情藝術:
心存委曲,每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傳衛爍《筆陣圖》)
起筆下筆,忖度尋思,引說綜由,永傳古今。(傳王羲之《筆勢論十二章并序》)
敏思藏于胸中,巧態發于毫铦。(庾肩吾《書品》)
手隨意適,筆與手會,故蓋得諧稱。(陶景弘《與梁武帝論書啟》)
手從心麾,毫以手從。(王僧虔《書賦》)
就所引材料來看,書法藝術中“情”的抒發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情”的醞釀,所謂“心存委曲”“敏思藏于胸中”,這是對于感情的把握與斟酌;其次是依據“情”來凝想書法意象,所謂“各象其形”“忖度尋思”。(傳)王羲之所謂“凡書貴乎沉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結思成矣”(《書論》),就是對此的詳細闡發。在這一階段中,書家將前一階段中涌動的情感加以明確化,將蓬勃的情思轉化為對于如何表現這種情思的冷靜思考,從而構建起“情”與書法形式之間的橋梁,引導“情”作以符合藝術秩序的表達。最后是在“手”與“心”(“意”)的協調運作下,將此前凝想的書法意象表達出來,所謂“手隨意適,筆與手會”“手從心麾,毫以手從”。在這一階段中,由于統合“情”與書法形式的書法意象已經構建完成,故而“心”“手”“筆”就形成了一種在直覺觸引下的高度連貫態勢。王僧虔的一段表述極有代表性“必使心忘于筆,手忘于書,心手達情,書不忘想,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即彰。”(《筆意贊》)不難見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情”已經被視為是整個書法藝術創作的美學本體所在,書法藝術被認為始于斯、也終于斯。
綜上所述,伴隨著書法藝術的發展與個體意識的自覺,書法藝術的抒情意識在兩漢至魏晉南北朝之際逐步萌生并獲確立。
三、“心正氣和”“本乎天地之心”“可驚可愕,一寓于書”:三種書法抒情模式
如前所述,儒家的中和之“情”,道家的超越之“情”以及屈騷的激揚之“情”,三者共同構成了中國文藝抒情傳統的文化淵流。書法藝術的抒情意識雖然受到三者作為一種整體的共同影響,但是也相應形成了三種各有側重的抒情模式,或近于中和之“情”、或近于超越之“情”,或近于激揚之“情”。對于這三種書法抒情模式的理論闡發,主要經由唐代虞世南、孫過庭、韓愈三人完成。
虞世南提出的“心正氣和”,偏于儒家中和之“情”的抒情傳統:
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于妙。心神不正,書則攲斜;志氣不和,字則顛仆。其道同魯廟之器,虛則攲,滿則覆,中則正,正者沖和之謂也。(《筆髓論·契妙》)
文中所及“收視反聽”“絕慮凝神”之語,雖然顯示出道家思想色彩,但是其功能指向卻是達到儒家所追求的“正”與“和”。在虞世南看來,書法藝術創作必須以一種心神“正”“和”的狀態進行,也就是有節制地進行情感抒發,這與儒家對于“樂”之“情”的論述一脈相承。而這種情緒的藝術形態化產物,則是一種符合儒家“沖和”之美的書法風格面貌。
孫過庭提出“本乎天地之心”,偏于道家超越之“情”的抒情傳統。他曾指出,雖然每個人都有“情性”,也都能將“情性”在書法藝術中進行風格化表達,但是并非所有的“情性”、所有的書法風格面貌都具備較高審美價值,所謂“偏玩所乖”是也。孫過庭提倡從“情性”的偏狹性中走出來,以“天地之心”作為書法風格的真正基石:
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書譜》)
這里所謂的“本乎天地之心”,一則指向莊子所謂的“無情”,是對種種“情”之殊相的否定,是對人心自然狀態的回歸。就此而言,孫過庭的“情性”實則著重于“性”而非“情”。值得注意的是,孫過庭雖然否定“情”的偏狹性,而提倡以“性”的自然狀態為書法風格的依托,但是其并不反對在“天地之心”的高度表現“情”的多樣性,其將王羲之樹立為此間典范——“寫《樂毅》則情多怫郁,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志慘。”二則指向道家所謂的“自然”。葉朗先生曾指出:“孫過庭把書法藝術的意象比作奔雷、墜石、鴻飛、獸駭、鸞舞、蛇驚、泉注、山安等等,并不是為了說明書法意象在形態上要和自然物相似,而是為了說明書法意象應該表現自然物的本體和生命。按照老、莊的哲學,造化自然的本體和生命是‘道’,是‘氣’。”由此看來,孫過庭的“情性觀”代表著一種以道家超越之“情”為根底的抒情精神,其強調將“情”作為一種“本乎天地之心”的本然之“性”來理解,從而實現一種“風規自遠”并且“同自然之妙有”的書法風格面貌。
韓愈提出的“可驚可愕,一寓于書”,偏于屈騷激揚之“情”的抒情傳統:
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斗,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后世。(《送高閑上人序》)
作為古文運動的推動者,韓愈的儒學背景不言自明。在這段表述中能夠看到儒家樂論“感于物而后動”的思想影響。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韓愈在此描寫的書法創作情緒絕非儒家追求的中和之“情”,而是在屈騷中方才具有的那種沉抑、悲憤、甚至有些迷狂的激揚之“情”。對于這種書法創作情緒的大肆渲染與高度推崇,與其“不平則鳴”的文藝主張有著深刻聯系,在古代書法美學理論中獨樹一幟,與此相對的書法風格面貌乃是“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
綜上所述,虞世南提出的“心正氣和”、孫過庭提出“本乎天地之心”、韓愈提出的“可驚可愕,一寓于書”,可以分別視為與儒家、道家、屈騷“樂”之“情”相對應的三種書法抒情模式。
四、結語
先秦時期,儒家、道家與屈騷對于“樂”之“情”的闡發與表達,形成了三種基調不同的抒情文化原型——中和、超越、激揚,并作為一個整體共同構筑了中國文藝抒情傳統的文化淵流。隨著書法藝術的發展與個體意識的自覺,“情”在漢晉時期逐步成為書法美學的核心概念,被確立為書法藝術的美學本體而貫穿于書法創作活動始終。至唐代之時,書法藝術的抒情觀念獲得了進一步的細化發展,形成了三種各有偏重的書法抒情模式,分別體現出儒家、道家、屈騷抒情傳統的文化思想影響。毫無疑問,書法藝術的抒情觀念是中國文藝抒情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觀照個體文化生命是中國文化與藝術審美的核心要義之一,其集中體現于在對與“心”“性”“情”的思索、探究與表達之中。應當看到,中國文藝的抒情傳統并不止于一種單純的情感抒發,而是包含著“心”“性”“情”三者,呈現為一種由“情”經“性”到“心”并可反向循環的動態螺旋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