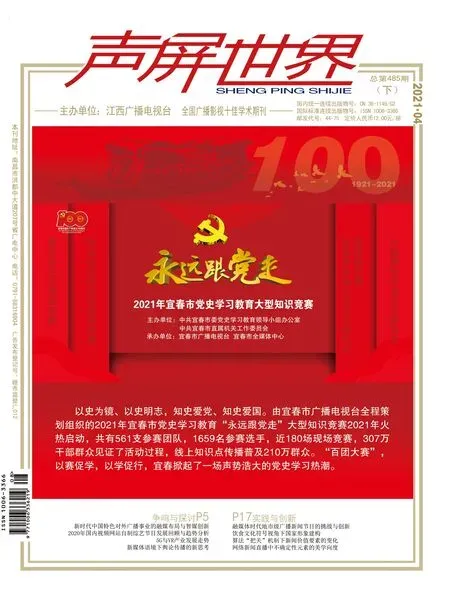淺析自媒體“洗稿”現狀及成因——以微信公眾號為例
□ 付俊妮
研究緣起
在自媒體風起云涌的時代,人們已經習慣用是否擁有“10W+”的閱讀量去衡量一篇作品的好壞,而不是看它的內容。為了保證作品成為“爆款”賺取流量,一些自媒體人動起了歪念頭。他們采用篡改、刪減、打散重組等手段把原創作品改頭換面,但其實是新瓶裝舊酒,最有價值的思想部分還是沒變,這就是所謂的“洗稿”。
在微信公眾號泛濫的時代,“洗稿”已經成為了自媒體行業內部公開的秘密。從幾十萬粉絲的大號到不起眼的小號,數不清的自媒體平臺都加入到了這場“洗不清”的戰斗中來。因此本文以微信公眾號為例,闡述自媒體“洗稿”現狀并分析自媒體“洗稿”成因。
“洗稿”概念界定
“洗稿”目前在學術界還未有一個權威的認定。魏永征指出:“‘洗稿’一詞源于我國香港地區新聞界,是業界默認的普遍操作。它指的是某個新聞事件發生后,沒有到現場采訪的記者從廣播電視或網上的報道獲取已經發生的事實,然后寫成文稿發表。有時同行之間還會互相交換采訪文稿,各人根據別人報道的事實撰稿在報紙上發表。”
任渝婉認為:“將別人發表的稿子進行改動,如重組語序,改變表達方式,在短時間內將文章改頭換面完成一篇新聞稿,這種行為被稱為‘洗稿’。”
微信公眾平臺的“洗稿”行為主要表現為挪用原作品的構思和創意等,把原作品用類似的語言改寫一遍,但本質內容和中心思想是一樣的。
微信公眾號“洗稿”現狀
“洗稿”已形成灰色產業鏈。為了獲得平臺給予的流量分成,自媒體“洗稿”現象已經泛濫成災。有人在洗稿,有人在買稿,還有人在做中間商,“洗稿”已經形成了一條灰色產業鏈。位于這條產業鏈底層的是一批偽原創兼職寫手,他們通過貼吧、QQ群等方式領取回報低的“洗稿”任務。這些“洗稿”任務的描述通常都很簡潔,包括洗哪種稿子、字數和原創度的需求以及薪酬。而位于這條產業鏈底層之上的,是管理這些寫手的團隊或公司,他們會出一些洗稿軟件、原創度檢測軟件和傳授“洗稿”技巧的教學視頻等。這些共同形成了一個流水線工廠,日復一日地生產出偽原創稿件。
治理“洗稿”困難重重。現有的法律在“洗稿”治理上存在盲區。依照我國現有的著作權保護法,“洗稿”行為在法律上也很難界定,對“洗稿”與否沒有固定的判斷標準。“洗稿”后的作品很難發現和原創作品之間的關系。
微信公眾平臺針對“洗稿”現象,成立了“洗稿投訴合議小組”。“洗稿投訴合議機制”將機器算法和人工審核進行結合,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作用。但是在判定被投訴方“洗稿”后,懲罰措施顯得很輕,只是將“洗稿”文章刪除,沒有更加強硬的懲罰措施。另外,杜絕“洗稿”現象需要多方合作,只有平臺發力是不夠的。
以微信公眾號為例淺析自媒體“洗稿”成因
自媒體“洗稿”外因。一、商業壓力。微信公眾號經過數年發展,已經擁有龐大的創作群體,包含政府、組織、公司、個人等,粉絲數量也持續增長。伴隨著龐大的公號數量,發稿量持續增長,競爭壓力愈來愈大。只有閱讀量多的“爆款文章”才能從中脫穎而出,為賬號主人贏得豐厚的流量分成和廣告收益。一些公號自身不具備寫出“爆款文章”的能力,陷入“無米下鍋”的窘境。在這場激烈的角逐中,他們選擇“走捷徑”,通過“洗稿”炮制“偽原創”生存下來。
二、法律法規不健全。隨著自媒體時代的來臨,出現了許多超出傳統范疇的新事物,使現有的法律法規體系陷入困境。現階段使用的《著作權法》修改周期漫長,并沒有針對新情形提出新對策。
在具體司法實踐中,現有著作權保護中運用到的“思想表達二分法”原則在解決“洗稿”問題時顯得無力。在有關著作權的案件中,需要判斷清楚被告使用的是原告的思想還是表達,但是思想和表達的劃分十分模糊。“洗稿”者正是打著只使用了“思想”的幌子進行“洗稿”漂白。“思想二分法”存在的漏洞被“洗稿”者利用,成了他們洗白的工具。
“思想表達二分法”是判斷侵權的原則,三步法是具體的實踐方法。在實際司法案例中,法院主要運用“抽象——過濾——比較”三步法來認定侵權。三步法在司法實踐中被用來判定是思想還是表達。三步法第一步是抽離掉作品中屬于思想的內容,第二步將兩部作品中相同但又屬于公共領域的內容過濾掉,第三步是判斷兩部作品剩下的內容是否實質性相似。但是“洗稿”作品往往把多篇文章雜糅起來使用,相似點可能只有一小段內容,這導致了實質性相似確定起來很困難。
三、原創作者維權困難。“洗稿”問題隨著自媒體時代的降臨愈演愈烈,“洗稿”者考慮到原創作者要維權起來困難重重,便變本加厲。原創者維權困難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原創作者維權周期長,以微信公眾號為例,維權者需要向“洗稿投訴合議小組”投訴,微信平臺邀請“合議小組”中的成員加入,收回結果要有十份以上,合議才有效。合議過程中,大于或等于70%的合議組成員認定被投訴方“洗稿”,被投訴方“洗稿”行為才算成立。整個合議流程所需時間很長,最后的維權結果也有可能以失敗告終。二是原創者舉證困難,自媒體作者在打官司時要提供的是電子憑據,而電子憑據具有“易刪除”的特性,很難被保留。以微信公眾號為例,在原創作者與“洗稿”者私下交流時,“洗稿者”可能會暗中刪除掉“洗稿”文章。此時,除非是原創者預先留下憑證,否則這場風波會不了了之。
自媒體“洗稿”內因。一、逐利愿望。商業逐利至上的社會大環境下,“洗稿”者通過“洗稿”來實現盈利。“洗稿”者背后的盈利邏輯是侵權行為成本低于交易成本。以微信公眾號為例,即使被告的稿件最終被判定為是“洗稿”作品,對“洗稿”者的懲罰也只是把“洗稿”文章刪除,并沒有經濟上的處罰措施。而如果自媒體要獨立完成一篇稿件的創作時,需要投入較多的人力物力,稿件被創作出來后,也有可能不能吸引讀者流量。相比之下,“洗稿”的成本就顯得很低廉,風險也很小。
二、“無米下鍋”的窘境。微信公眾號的準入門檻很低,申請個人微信公眾號,只需要簡單幾步就可以完成,而且注冊微信公眾號是不需要任何費用的。許多微信公眾號的主體在寫作文章方面可能完全處于“小白”狀態,他們沒有能力創作出優質的稿件。創作出一篇優質稿件是需要耗費很多的時間和人力的,如果自媒體作者沒有深厚的知識功底,很容易陷入“稿荒”的困境,因此就連一些自媒體大號也打起了“洗稿”的算盤。
三、版權意識薄弱。一方面,網絡的匿名性導致了一些自媒體作者道德意識的弱化。自媒體作者的真實身份往往被隱藏起來,這樣他們剽竊作品時的愧疚感降低。郭慶光在《傳播學教程》中指出匿名性原理的概念:“集合行為使個體湮沒在人群中,沒有人能夠知道他的姓名和身份,處于一種沒有社會約束力的匿名狀態中,這種狀態使他社會責任感和自我控制力降低減弱。”“洗稿”已經形成了一條灰色產業鏈,許多“洗稿”者正是在法不責眾的心理效應下對“洗稿”趨之若鶩。
四、受眾的媒介素養不夠高。自媒體時代時常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一篇內容優質的文章,閱讀量和點贊量寥寥無幾,而一篇看似粗制的文章,卻贏得了“10W+”的瀏覽量。大多數受眾在接受公眾號帶給他的信息時,更關注的是這些信息是否對他有用、是否讓他產生了一種情感。而這些信息背后的創作渠道,他們不是那么關心。認真寫作的人慘淡收場,用不當技巧吸引眼球的人卻混得風生水起,這種巨大的心理落差導致了一部分自媒體作者加入了“洗稿”隊伍。
結語
“洗稿”現象是伴隨著自媒體時代而產生的,大到坐擁百萬粉絲的公號,小到鮮有人知的小號都加入了“洗稿”隊伍。對于“洗稿”原因的分析不可以片面地只進行主觀分析,要結合大的社會背景進行分析。對于“洗稿”的治理,不能簡單苛求自媒體作者自身應保持原創精神,還應采取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平臺管理的措施做強有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