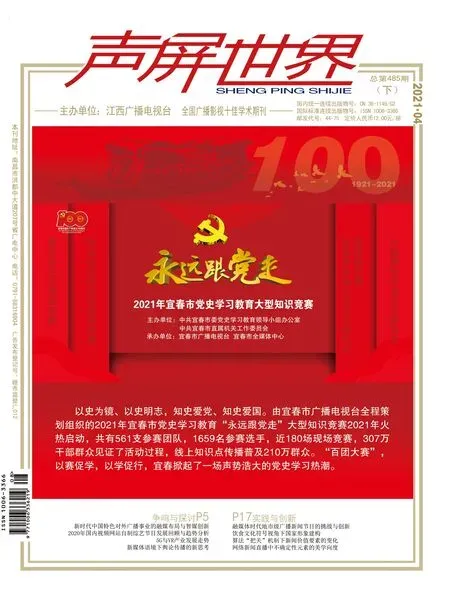“她綜藝”的女性價值傳達與現實困境——評《乘風破浪的姐姐》
□ 艾芳怡
新世紀以來,隨著女性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的提升、互聯網娛樂的蓬勃發展驅動女性注意力和消費方式的轉變,以女性為綜藝主角,圍繞女性的生活、工作、情感、社交等話題展開討論,以折射當下社會女性價值觀的“她綜藝”應勢而生。2020年芒果TV自制“她綜藝”《乘風破浪的姐姐》(以下簡稱《姐姐》)是在女性意識崛起的社會背景下,汲取“她綜藝”的實踐經驗創作的成果。節目聚焦30位1990年之前出生的“姐姐輩”女藝人的女團追夢歷程,以“三十而驪”為口號,以“破齡成團”為宣言對抗著傳統的男性話語和固化的市場思維。本文將梳理潛藏在節目中的女性話語內涵和價值傳達機制以及女性敘事的阻力,為“她綜藝”的創作帶來更深入的思考。
女性主體的自我認知與成長
重構女性主體是后現代女性主義的重要觀點,后現代女性主義認為女性的主體性是女性走向解放的關鍵,展現女性主體性對于“她綜藝”的價值建構具有結構性意義。如果說以《創造101》為代表的女團養成綜藝的本質是資本方借力娛樂工業體系以謀求粉絲經濟的紅利,潛在地表達了女性的成長價值,那么《姐姐》則是理念先行,是以女團選秀模式為依托對女性意識的自覺集中展示。
“鏡中我”深化自我認知。庫利認為,他人對自己的評價、態度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鏡子”,個人通過這面“鏡子”認識和把握自己。節目中的“30+”女藝人雖然都是在演藝圈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但由于演員、歌手、舞者、主持人等職業的分化而鮮有交集。節目以女團的形式將她們聚合在同一環境,為她們設立共同的任務,在團隊訓練、集體生活和舞臺競爭中展示個性之間的碰撞,在相互學習和經驗交流中看到自身的閃光點和不足,從而在更加深刻認識和把握自己的基礎上促使個人能力得到恰當發揮。作為女性,她們對于同性的評價無疑傾向于以女性視角為基礎,此種帶有女性共情色彩的評價往往更加中肯,也更有利于被評價的女性主體獲得清晰的自我認知。自我認知是一個能動的、創造性的過程,姐姐們在與社會、她人的聯系上,在“乘風破浪”中持續挖掘自身潛力,重新認識自我,形成新的意志和行為主體,凸顯了女性不斷實現自我完善和發展的主體性價值。
“蝶變”彰顯女性價值。成長不受年齡限制,“30+”的女性同樣能夠在突破自我中抵達成長。節目召集的30位“30+”女藝人,絕大多數并非女團出身,對于一些唱跳表演零基礎的姐姐,在短時間內配合隊友展現出一個完美的舞臺,并滿足觀眾對“女團”的審美絕非易事。然而,沒有什么比挑戰自我更能凸顯女性的成長。節目通過介入式采訪和直接電影式的鏡頭,記錄了她們的生理、心理體驗,展現了她們“自為存在”式地追求在舞臺上乃至人格上的成長的獨立姿態。早在第二次公演就被淘汰,而在第五次公演的復活賽中重返舞臺的阿朵,從不爭不搶到主動競爭隊長表露自己的野心,“教科書級”的拉票,阿朵以行動表明自己不再只充當參與者而是要當勝利者。多年以來背負著《快樂大本營》“小透明”標簽的吳昕,也在這個節目里發出了屬于自己的光芒。姐姐們所表現出的勤奮、進取的精神,彰顯了中年女性的自信與魅力,同時也激勵著觀眾確立自我的主體價值。
推動女性媒介話語體系的構建
勞拉·穆爾維在《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中指出,女性銀幕形象是男性審視下的呈現,而非女性自我闡釋的產物。后現代女性主義認為,在男性話語體系的支配下,女性的本質特征及生存經驗是由男性言說的,性別差異與偏見的存在,勢必造成對女性本質特征和生存經驗的歪曲。因此,實現女性的全面發展和真正解放,構建女性自身的話語體系尤為重要。
解除枷鎖,走出邊緣。女性的年齡,似乎一直是整個社會無時無刻不在“介意”的要素和“審視”女性個體價值的尺度。演藝界的“潛規則”是社會意識的投影。潛在的年齡標尺下,女藝人主動選擇的余地愈發有限。因此,只有打破年齡的束縛,給予各個年齡段的女性平等的選擇權和話語權,才能廣泛地構建屬于整個女性群體的話語體系。“三十而勵”,《姐姐》設定了一個重要的前提——年齡。從構成群體的年齡層次上看,30位女藝人介于30歲至52歲的年齡跨度之間,被邊緣化的中年女藝人重新獲得了多元個性展示及自我表達的平臺,有助于解構以往傳統媒體塑造的刻板的中年女性形象。“成團之夜”對中國女排精神以及來自各行各業和不同年齡段的榜樣姐姐的致敬,更是超越了節目原有框架下的價值表達,對女性年齡及價值的肯定從特定的女藝人上升到了普遍意義上的女性群體。因此在形式上,節目直觀地構建了一個提升女性話語權利的媒介環境。
撕掉標簽,真誠表達。《姐姐》在節目形式上呈現的女性媒介話語權在年齡層次上的拓展,最終指向節目敘事中女性話語內涵的豐富表達。
其一,女性價值與年齡無關,姐姐也要乘風破浪。在男性中心文化影響下,“年齡”不僅束縛著女性話語的自由表達,而且成為誘發中年女性人生焦慮的重要因素。《姐姐》則直面女性年齡議題,賦予年齡積極意義。50歲的鐘麗緹在節目中談到:“只要夢想沒有停止,不管你是10歲、30歲還是60歲,都要一直往前走。年齡只是一個數字。”52歲的伊能靜為了展現更加完美的舞臺,在長期患有低血糖的狀態下凌晨四點還在堅持訓練,直呼“不要因為我的年紀放過我”。她們用話語和行動以誠懇的態度為女性群體發聲,鼓勵女性敢于撕掉男性中心文化規制的年齡標簽,以“無懼年齡”的精神追求價值目標的實現。
其二,拒絕“被定義”的人生,每位女性都有無限可能。女性特征往往在男性中心文化的塑造中被“標簽化”,比如性格不夠溫柔或者不愛穿裙子的女性被認為沒有“女人味”,不行使生育權的女性則過著“不完整的人生”等。這些帶有強制意味的設定,往往成為女性自由發展的桎梏。實際上,女性特征是由女性自己來言說和界定的,恰如楊瀾在第四次公演中表示“每個女人都應該由自己來定義女人味”。主題曲《無價之姐》正呼應了節目對女性“自信歸位”的呼喚,體現出作詞人對女性意識的自覺掌握和宣揚。“保持獨有鋒芒”“什么人生,什么夢想,我自己造”“我是我的無價之寶”,《無價之姐》旨在說明女性無論外表還是內在都要勇于堅持自我、認同自我、釋放真我,女性價值無需定義。從某種意義上說,李宇春作為傳統審美標準的抵抗者和個人審美的堅守者,由她為節目主題曲作詞并演唱,本身就是一種女性意識的潛在表達。同時,節目要求演員、主持人、制片人像女團成員一樣在舞臺上表演唱跳,也正是在看見女性價值的多樣性中挖掘她們的無限潛能。
反思:女性敘事在博弈與妥協中的弱化
“她綜藝”在本質上是一類文化產品,在“泛娛樂化”時代和資本主導的娛樂市場環境中,既承載著觀眾在屏幕上尋求審美愉悅和娛樂的愿望,又先天攜帶著商品屬性,企求獲得更廣闊的利潤空間。因此,《姐姐》雖努力承擔著社會議題、追求著藝術價值,但受眾的審美偏好、娛樂市場的商業邏輯也在影響著節目的女性價值傳達。
窠臼:“文化工業”表征復現。《姐姐》作為一檔立意深遠的競爭性節目,其賽制應與節目理念一脈相通,然而決定選手去留的卻是“觀眾喜愛度”,其中潛藏的娛樂工業法則值得細究。“觀眾喜愛度”即現場觀眾根據個人喜好為姐姐們投票,只有占據喜愛度排行前排的姐姐才能暫時避免被淘汰。觀眾喜愛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與她們的名氣相匹配的,在名氣的加持下現場的觀眾評審在投票時就很難無視她們之前獲得的成績,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排名結果帶有濃重的“論資排輩”的意味。像寧靜、張雨綺、伊能靜這些“咖位”大、話題度高的姐姐,有節目組和觀眾“撐腰”,幾乎未曾面臨淘汰的邊緣。而最“優先”被淘汰的選手基本上都有兩個特點:不夠紅,話題少。拋開舞臺專業素養,不談女性人格差異,僅僅以人氣熱度高低來決定姐姐們是否有資格繼續留在舞臺上“乘風破浪”,甚至可以說,留下熱度高的選手以賺取更高可以變現的流量,節目賽制使得自身已經陷入普通女團選秀節目的市場規律。
除了名氣,舞臺感染力也是影響“觀眾喜愛度”的重要因素。毋庸置疑的是,對于現場觀眾來說,唱跳結合的快節奏歌曲要比純聲樂的慢歌更具有感染力,這也是在前兩次公演的比賽結果中得到印證的事實。因此,創造更“燃”的兼具視聽刺激的舞臺,成了姐姐們獲得觀眾喜愛的“安全牌”。在缺乏視聽刺激的歌曲每每遭受組隊“輪空”的尷尬后,在第四次公演中純聲樂慢歌已經無跡可尋了。一邊是音樂總監趙兆堅持自己的藝術品味,一邊是“孟佳組”想要迎合觀眾口味。節目在個性與大眾之間搖擺不定,姐姐們在自我矛盾中與“觀眾喜愛度”這一指標不斷地做出妥協,反映出商業邏輯與節目女性敘事的沖突。
展望:“她綜藝”女性敘事的改進。“定義不一樣的女團”,節目的初心是對女團傳統形象的反叛和對女性所承載的社會成見的反抗。然而,對固化思維和現存規則的顛覆并非一蹴而就。觀眾已然形成的審美偏好、商業模式對女性敘事的征用、資本逐利的本性,都在阻礙著“她綜藝”新銳的女性價值觀的傳達。《姐姐》在與資本博弈中妥協,造成的女性敘事弱化的局面,也為“她綜藝”的創作帶來了深刻的啟示:“她綜藝”在促進女性媒介形象改觀的過程中,應該對男性中心話語降噪,減少商業利益干擾,在傳達當代女性價值、塑造更多立體鮮活的女性形象中推動觀眾審美偏好的改變,不斷在自我的“否定之否定”中實現女性敘事的邏輯自洽。
結語
現象級“她綜藝”《姐姐》以其獨到的性別敘事為“她綜藝”創作樹立了理念標桿、開拓了廣闊道路,為社會議題與娛樂文化的初步結合打下的良好基礎。雖然在資本競相逐利的娛樂市場中,節目還未逃離積聚女性敘事力量的同時又被商業邏輯弱化的命運,但節目仍將繼續激勵更多富有多元價值的女性形象的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