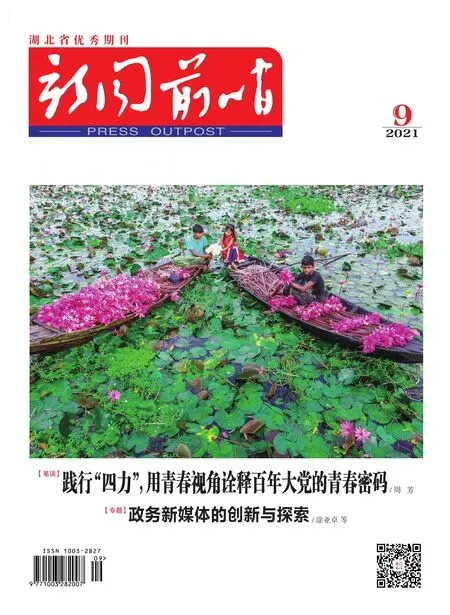從青年亞文化角度探析網絡綜藝的全新表達
——以《說唱新世代》為例
◎江安航 胡亦琳 姜洪偉
一、研究現狀
對于青年亞文化和網絡綜藝節目(以下簡稱“網綜”)的研究時間跨度較短,近十年來逐漸出現針對這兩方面的期刊和論文。筆者采用網上搜索、查閱字典等方式對青年亞文化和網綜的相關詞匯進行了查閱。通過萬方數據庫查閱文獻匯集材料,發現以往該領域的研究主要從以下三個角度出發。
首先,從青年個體成長的角度。作為當下最流行的網絡節目樣式之一,以青少年為主要受眾群體的網綜節目,組成了青年亞文化中重要的一環。柳靜在《綜藝節目的文化分析》中提到:“受青少年生理和心理的影響,青年亞文化呈現出對傳統和精英文化的抵抗及非主流的文化特色,在綜藝節目中則表現出青春感性沖動和青春偶像崇拜的特點。”
其次,從青年亞文化的角度。網綜對于青年亞文化的影響是復雜的,學者們有的將網綜視為一場“狂歡”,深入剖析了“狂歡”現象的特征和影響;有的從傳播學和語言學的角度分析了網綜的受眾的心理。
第三,從商業化角度。“‘消費’是一種青年亞文化行為的基本功能和社會意義,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消費主義的普及,亞文化群體與商業機構之間通過“消費”體現了多種互動關系。”多位學者對于網綜背后的產業鏈和營銷策略進行了分析。
總之,我國對于青年亞文化和網綜的相關研究有前輩做鋪墊,但其中針對《說唱新世代》的研究并不多,本文將緊緊結合這一部網綜展開分析。
二、《說唱新世代》及青年亞文化概況
(一)《說唱新世代》流量和口碑雙豐收
《說唱新世代》是嗶哩嗶哩(簡稱“B站”)出品的首檔說唱音樂類節目,該節目在B站獲得了良好的回饋和口碑,在眾多說唱類節目中脫穎而出,收獲了豆瓣9.2分的好評。節目宗旨是“萬物皆可說唱”,匯聚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說唱歌手,齊聚“說唱基地”。他們將通過層層公演考核,以音樂創作和競演表現,決出代表新世代發聲的“世代表達者”。
(二)青年亞文化的定義及背景
青年亞文化一般指社會階層結構框架里不斷出現的那些帶有一定“反常”色彩或挑戰性的青年新興社群或新潮生活方式。在平臺和對象上與網絡亞文化有相似之處。它的亞文化屬性使其不同于以主流文化為基礎的廣大青年文化。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民規模達9.04億。而在我國網民的年齡結構中,10-39歲的網民占60%以上。這些年輕人的開放性、分散化、互動性等特點,使青年亞文化在網絡環境中更好地成長。同時,各類移動終端的繁榮發展為亞文化的生長提供了優良的發展條件。
三、青年亞文化視域下《說唱新世代》的主要表現形式
(一)從內容、年齡段、表達形式的角度闡述青年亞文化的多元性
1.不同年齡段呈現了青年亞文化的不同特征
青年群體的年齡段可進行細分,不同年齡段的青年群體呈現出的亞文化態勢不同。這一點在《說唱新世代》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85后”選手的個人作品飽含對人生的釋然與和解,他們為人處世也更加世故和老練;而“95后”選手的作品中則展現出更多對社會現象和所處環境的思考;不少“00后”選手選擇通過作品傳遞他們對當下人生階段的思考。這種代際差異讓我們也看到了亞文化傳播方式的多元化態勢,在這種亞文化環境中,青年的思想和行為必然更加多元化、個性化。
2.《說唱新世代》節目中選手表達思想的形式多元
在《說唱新世代》這樣一檔藝術性、娛樂性較強的綜藝節目中,選手表達思想的形式也十分多元。例如,同樣是反映社會問題,Subs的《畫》中描繪了一幅烏托邦的美好景象,情感真摯感人;而螺絲刀組合的作品《叫爸爸》的歌詞中,用戲謔的語氣描繪出了生活中處處想走捷徑的人的心理,從反面諷刺、抨擊了這種不勞而獲的行為。
另外,節目的賽制也給予了選手充分的展現機會。《說唱新世代》以展現出選手們最真實的一面為宗旨,設計了對抗性的規則,既鼓勵選手按照給定的主題即興創作,也充分給予了展現以前的作品的機會。
(二)青年亞文化的標出性促成商業化收編
“標出性”由布拉格學派的俄國語言學家特魯別茨柯伊提出,本意在于突出非常規項。應用在人文社科領域時,主流文化即為常規項,亞文化即為非常規項。讓受眾關注和了解亞文化的過程即為“標出”。
對于青年亞文化進行“標出”的過程展示了青年亞文化與主流文化的不同之處,將其邊緣化和非正常化了,但往往正是這樣的標出現象,將“聚光燈”照在青年亞文化上,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積極效果。
嘻哈文化以《中國有嘻哈》、《說唱新世代》等綜藝節目為代表,在資本的推動和受眾市場娛樂的導向下,使一部分受眾的視線轉向亞文化音樂,即對嘻哈文化進行“標出”。《說唱新世代》節目播出之后,平臺緊接著對選手們的官方賬號進行了宣傳,并推出了后續綜藝《造浪》《造浪》是嗶哩嗶哩出品的首檔說唱廠牌音樂旅行節目,嘉賓為《說唱新世代》排名前八的選手,節目播出后反響優良。《說唱新世代》的記憶點不僅在相關視頻彈幕中大量出現,甚至會出現在與嘻哈無關的視頻中出現,形成了獨特的“貸人”文化。
當一個處于標出項的青年亞文化經過了某個綜藝節目的聚焦和重構之后,將會逐漸向主流文化靠攏,被主流文化收編。在網絡綜藝領域,節目制作方會針對亞文化靠攏的過程,構建一個逐漸成熟的商業化產業鏈。為了賺取更大的市場份額,將不斷有節目制作者通過該產業鏈策劃下一次亞文化的標出,形成循環。
四、青年說唱愛好者群體認同的構建的新表征
(一)“抵抗性”方式改變
20世紀70年代時,嘻哈音樂誕生在美國紐約的黑人貧民區,當時貧富差巨大,種族歧視嚴重,該地區社會動蕩,矛盾和沖突層出不窮,嘻哈音樂創作的初衷是為了表達和發泄情緒,主題多為批判社會和紙醉金迷,帶有青春期特有的抵抗和叛逆的色彩,由此形成嘻哈文化原本的“抵抗性”。
不難發現,《說唱新世代》中很少出現言辭鋒利、充滿攻擊性的音樂,甚至一些歌手在訪談中坦言,來到這個節目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為了競爭,而是為了交朋友或者宣傳作品的,總決賽季軍沙一汀表示“我是來玩的,我只想認識想要認識的人和喜歡我的人。”選手萬賽文也說:“即使把我先淘汰了,只要我能把自己的作品留下來,也是一件好事,音樂被大家聽到就好。”節目中唯一一位在采訪時向其他選手“宣戰”的選手被觀眾戲稱為“稀有物種”,但他在節目后期也坦言自己被“感化了”,交到了很多朋友。
青年亞文化的抵抗性不再呈現為激進的正面沖突,而是將其表達需求融合到語言、動作、旋律以及節奏等符號之中,將選手對個人經歷、社會現象的思考用藝術的形式表達出來,給抵抗性賦予了溫和的特質,賦予了話題的厚度和深度。
例如,選手Subs的作品《我不想死在20歲》創造于大專院校畢業后對未來感到迷茫之時。歌詞并不攻擊任何人,只是蘊含了青年人對于人生和未來的思考,真實地表現出了他在結束學業后對未來的無措感,想要逃避現實,但掙扎后還是擔起了責任,勇敢追夢的經歷。在歌曲解析訪談中,他說:“我想讓別人感受到我的‘喪’,也想讓別人感受到我的力量。”
(二)“邊緣性”向中心逐漸靠近
被“標出”的亞文化群體向主流文化群體靠近,是雙方相互作用的,亞文化群體需要靠近主流文化的機會,而主流文化則通過吸收亞文化變得更多樣繁榮。青年亞文化為了宣揚自身,需要向受眾展現自身文化魅力的機會,尋求更多關注。例如嘻哈文化中音樂創作者們需要流量和平臺,《說唱新世代》在B站獨家播出,B站作為“亞文化的烏托邦”如今已成為國內最大的原創音樂社區之一,包含大量音樂創作者和受眾,可以為說唱愛好者提供平臺。此外,與騰訊、愛奇藝、優酷等視頻網站不同的是,靠推廣“二次元文化”起家的B站本就是青年群體的聚集地,其用戶對于亞文化更加包容,該群體借助這個平臺張揚自己的文化,向主流文化靠近。主流文化需要滿足更多、更廣人群的個性化需求,因此需要不斷尋求創新,與亞文化進行一定的融合。
結語
無論是亞文化還是主流文化,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魅力,吸引著一部分人愿意為之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創造出專屬于一個時代的經典和輝煌,反映出其中的深層社會原因。嘻哈文化正是如此,在《說唱新世代》節目中,制作者以“萬物皆可說唱”的觀念為指導,呈現了青年亞文化的多樣性、標出性,該文化的抵抗性發生了改變,嘻哈音樂作品的風格不再是單一的、鋒利的、紙醉金迷的,它反映了社會問題和對人生和世界的思考,賦予了亞文化積極的厚度和深度,促進亞文化向主流文化改變。
注釋:
[1]柳靜:《綜藝節目的文化分析》,山東師范大學2011年學位論文
[2]董中鋒:《新媒體背景下娛樂節目狂歡現象研究——以〈奇葩說〉為例》,華中師范大學2016年學位論文
[3]唐文楊:《從傳播學看網絡節目〈奇葩說〉的文化表達》,暨南大學2016年學位論文
[4]張寧、唐嘉儀:《商業邏輯與青年亞文化生產:網綜節目的批判話語分析》,《新媒體研究》2019年第2期
[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20)[EB/OL],http://www.cac.gov.cn/2020-04/27/c_158953547037858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