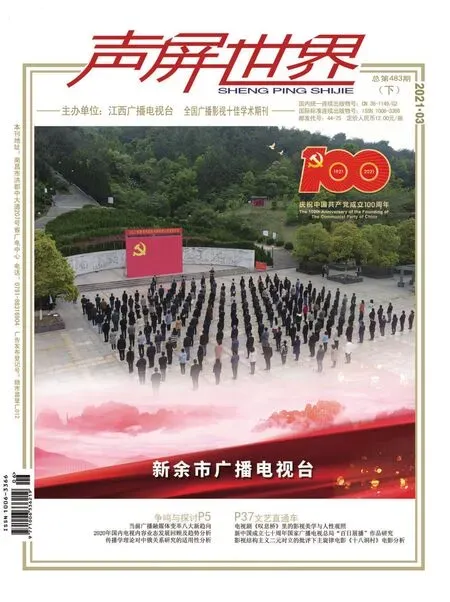科幻電影中的賽博格形象研究
□ 賈廣宇
賽博格概念的界定與拓展
機械移植提高人體機能的科學設想。“賽博格”一詞的誕生,是取自“控制論(Cybernetic)”和“有機體(Organism)”兩詞的前半段組合而成的新名詞“cyborg”。最早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當時美國航空航天局的兩位科學家克萊因斯·克林斯與內森·克萊恩,希望通過藥物、機械等技術手段幫助宇航員提高人體機能,從而增強宇航員在外太空的生存能力,這個設想也成為了賽博格的概念雛形。后來隨著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賽博格的定義也隨之被擴大,出現在了醫學、人類學等領域當中。在現代醫學當中,醫生面對軀體患有生理缺陷的患者,也會使用例如助聽器、心臟支架或是義肢等機械裝置來幫助患者彌補生理功能上的缺陷,實現人體與機械的結合。馬歇爾·麥克盧漢曾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這一概念,在如今的電子傳播時代,手機、電視等電子媒介成為了人們視覺和聽覺向外延伸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這些電子設備成為了安裝在身體上的“隱形機械”,不知不覺中,“賽博格”的概念已經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
人類邊界逾越背后的社會象征。除了起初“賽博格”人機結合的狹義概念外,后人類主義也推動了賽博格向著哲學問題的變遷。后人類主義思想作為對人文主義的批判,是對于“以人為中心”思想的反思和對于人與自然、社會之間關系的重新解讀,人們可以在唐娜·哈拉維、布魯諾·拉圖爾、凱瑟琳·海勒等著名學者的理論中找到后人類主義思想的影子。隨著現代科技的快速發展,人們也開始去思考人類與科技之間的微妙關系,這使得關于賽博格的研究擺脫了原先的狹義科學概念,進入到了文化研究的領域范疇,賽博格概念中關于人體的重構與后人類主義思想中對人本質的反思產生了共鳴。在美國女權主義學者唐娜·哈拉維的筆下,賽博格的出現意味著人類與動物、有機體與機械以及物質與非物質三條人類界限的模糊,在邊界模糊的背后賽博格也象征著對于性別、種族、階段等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的消解,當人人都成為賽博格,關于這些二元論的區分也就失去了意義,從而實現真正含義上的男女平等社會。因此,哈拉維也將賽博格視為一種政治神話,并且發出“我愿意做賽博格,而非女神”的呼聲。正是由于賽博格的概念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進入到了文化領域范疇,關于賽博格的研究也越來越成為科技將如何左右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對人類的身體性將產生怎樣影響的一種未來寓言。
科幻作品中人類反思的創作對象。受西方工業革命影響,科幻小說誕生于那個機器開始改變世界的年代,文學作為社會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自然會與社會表征產生呼應;當下科學技術正在重塑人類的生活方式,當科技進化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又會怎樣改變人們的社會?科幻小說帶著這樣的思考,進入到了當時人們的視野中。起初作為一種科學設想,賽博格在20世紀中葉才被提出,但在先前的科幻小說中人們發現賽博格的形象已然存在。在瑪麗·雪萊所著的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中作者描寫了一個被科學家用尸體殘肢拼湊而成的巨大怪物,書中人造人的科學設想也成為了賽博格的一種縮影。而后來科技社會衍生出的賽博朋克文化則更加完善了對賽博格的設想,在威廉·吉普森的經典賽博朋克小說《神經漫游者》中,作者向讀者展現了一個光怪陸離的虛擬空間,主人公凱斯大腦與世界網絡相連接的信息盜賊形象也開創了人腦與電腦結合的賽博格新形式。在科技文明高度發達的賽博朋克世界中,人體改造后的賽博格成為了社會的主要群體,可是科技高速發展帶來的資本主義極端化,賽博格的社會是否會變得畸形?作為人與科技最直接的互動產物,賽博格是人類對于科技發展反思最直觀的體現,自然也就成為了許多科幻小說的創作主體。
科幻電影中不同類型的賽博格
被孤立的社會“邊緣者”。當機器人可以模仿人類行為,人們會抱著怎樣的態度去對待它?是欣喜它的分擔,還是恐懼它的代替,亦或是憎恨它的霸占?在科幻電影《剪刀手愛德華》中,身居古堡的老科學家創造了一個機器人并取名為愛德華,但愛德華就如同《弗蘭肯斯坦》中的怪物,兩者都缺失人類身體表征的完整性。怪物試圖幫助人類,卻因非人的外表受到社會的拋棄,最終對人類心生仇恨;愛德華心地單純,卻苦于身體和心智的殘缺愛而不得,最終自我封閉,兩者皆是社會邊緣的賽博格存在。這樣的角色下卻蘊含著另外一層思考,人工智能是否真的會產生意識?意識的產生是否又代表人類生命的產生?如今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機器人已經進入了我們的生活,關于AI主持人的新聞就引發了許多人的職業危機感。電腦正在一點點代替人腦,如果機器人已經開始頂替人類去工作,那么將來有一天機器人是否會代替人類去生活?正如唐娜·哈拉維在《賽博格宣言》中所說:“我們的機器令人不安地生氣勃勃,而我們自己則令人恐懼地萎靡遲鈍。”這是人工智能帶給人類難以擺脫的憂思,但它也在不斷地警醒著人類,與其去擔憂人類是否會被終結,不如加強自身對于科學規律性地把握,避免科技發展的失控。
尋求自我身份認同的“失憶者”。當身體成為軀殼變得可以隨意更換,當意識和記憶可以被轉移和制造,賽博格該如何去定義自己的身份。押井守導演的動畫電影《攻殼機動隊》憑借著其對于人本身深刻的哲學性思考被很多觀眾奉為賽博朋克電影的神作。在《攻殼機動隊》的世界中,人類可以拋棄自身孱弱的肉體將其更換為機械,甚至可以憑借高度發達的科技實現大腦電子化。電影主人公草薙素子便是實現全身義體化的賽博格形象。素子在奉命調查“傀儡師”案件時發現罪犯存在記憶被篡改的現象,這讓素子內心產生了深深的自我懷疑。她作為全身義體化的賽博格,機械義體讓DNA失去了說服力,記憶如今又可以被篡改,到底如何才能讓自己確定“我”就是“我”呢?押井守在影片最后也并沒有表明答案,而是讓素子放下了對“自我”的執念,選擇與本是人工智能程序卻擁有自我意識的傀儡師合體,意識超越了肉體的限制,成為一種高級形態的存在,但人們已無法再將合體后的素子稱之為“人”。因此,關于何為人的討論人們不能將身體與意識分裂開來,正因為擁有著人類的身體,人們的大腦才能獲得關于人類的感知,即使記憶被篡改,可人們依然能夠通過自己的行為去重新定義自我身份,如同電影《銀翼殺手2049》中的K。K作為人類生產的復制人,本以為自己是被復制人生下的孩子,代表著奇跡的發生,可最后K發現自己的記憶是被別人篡改的,他的存在是為了掩護真正的復制人孩子,這讓K的內心幾乎崩潰。K身為賽博格擁有的一直是別人的記憶,但是在真相大白后他沒有放棄自己“人”的身份,而是通過救下戴克讓他們父女相見的行動重新尋回自己存在的意義。
父權社會的“挑戰者”。前文中曾提到在唐納·哈拉維的筆下,賽博格概念的背后代表的對于男性—女性、心智—身體等二元對立解構的消解,承載著烏托邦式的社會功能,從而幫助女性跨越出當前的身份認同困境,沖擊西方的父權社會秩序。影片《阿麗塔:戰斗天使》塑造了一個正義、善良的女性賽博格形象——阿麗塔。在阿麗塔的世界中,無論是鋼鐵城食物鏈頂端的維克托,還是天空之城撒冷的集權者諾瓦,權力的掌管者無一例外都是男性角色,這似乎也是哈拉維所批判的西方父權社會的縮影。父權制度下的女性一直處于卑微和服從的地位,這也刺激了女性意識的覺醒以及反抗,阿麗塔雖然身材嬌小,但是在面對這些男性對手時毫無懼色,將他們一一擊敗。電影中阿麗塔在愛與冒險中不斷成長,一點點地接近挑戰男性反派所掌握的權力至高點,如同唐納哈拉維等女權主義學家所代表的女權運動一般,不斷地在沖擊著男權思想。隨著當代女性獨立意識的覺醒和社會地位的提高,女性也在逐漸地從父權制社會下解脫。或許在賽博格的社會,如唐納哈拉維所說:“賽博性別是一種進行全面報復的局部可能性,”性別之分在全民義體化的賽博格社會也就變得毫無意義了。
結語
當科技逐漸嵌入人們的生活,科幻作品中關于未來的設想正在由假成真,對于人類和科技的互動寓言也轉化為了現實思考。凱瑟琳·海勒曾在《我們如何成為后人類》中指出人類必須與其他生命形式共享這個星球甚至人類自身,或許在不久的將來人們都會以賽博格的形式存在于這個世界上。盡管賽博格的出現并非意味著人類的終結,但會對人類文明產生怎樣的沖擊,科技是否會成為人類命運的主宰,這值得人們不斷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