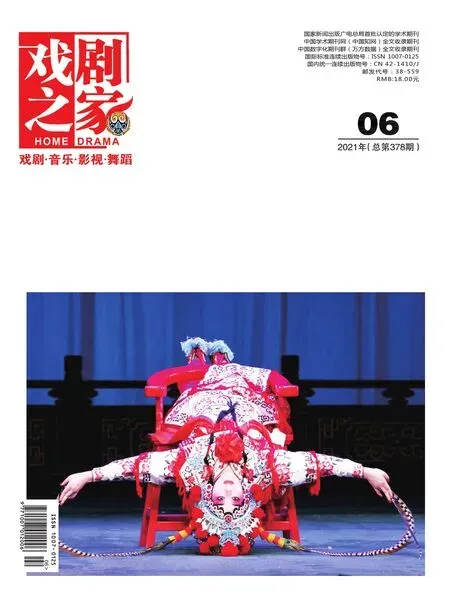淺談田漢的戲曲觀
(中國戲曲學院 北京 100073)
戲曲藝術作為中國傳統藝術,它的表現形式和文化基礎決定了傳統戲曲在封建時期結束后面臨的尷尬境況。文言文向白話文逐漸過渡,老套的傳統故事也不再能滿足新時代的精神需求,更勿論風俗習慣的改變讓原生劇種難以為繼。即使如此,也有很多有識之士致力于對舊戲進行改革,他們相信舊戲并非一無是處,其中代表人物有以實踐為主的歐陽予倩、梅蘭芳等,而面對這樣一項繁重而艱巨的任務,片面的改革都只是治標不治本。學術界之所以認同田漢先生是中國戲曲改革運動的先驅者,是因為他對戲曲的認知很全面,主張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要在尊重傳統的前提下談革新,在實踐與理論的平衡中創造中出一套既有根基又能夠吸收新力量的理論體系。
田漢先生的思想不僅僅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而且受到了西方文學藝術觀念的浸染,因此他對待戲曲的態度是客觀的,這種客觀態度隨著歷史的進程逐漸成熟。
一、不同時期田漢先生對戲曲理論的認識
清末民初,思潮涌動,改良派和革命派嘗試接觸“西學”,開始重視文藝作品在輿論和反映社會現實上的作用。當時學術界涌現出一批響應改良運動的團體和個人,內容主要以新編歷史劇和表現現實生活的新戲為主,但是隨著政局的消沉,新戲也逐漸流于形式,最終不了了之。
田漢對于戲曲創作理念的真正覺醒應該是在五四運動時期。五四時期是戲曲改良的低谷時期,當時的主流思想傾向是批判戲曲中的封建思想以及在文藝方面的落后,這一思想的主導力量都是受西方教育影響較深的知識分子,他們對于傳統戲曲只是紙上談兵,并沒有實際的了解,再加上一味地推崇西方文化甚至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戲曲的存在,這樣的思潮對戲曲界產生了極其嚴重的消極影響。但同時也出現了大量的表演藝術家,以梅蘭芳、程硯秋為代表,他們先后到國外進行演出,將傳統戲曲發展為以名角為中心的表現形式,雖然提高了戲曲的藝術審美,但是對于劇目題材內容的忽視導致了劇本創作的低迷。
這個時期,田漢正在日本留學,開始接受西方的文藝理論和民主思想。在嘗試了缺乏現實性的失敗后,他意識到,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差異,單純地引入西方理論而不進行本土化改造是會造成排異反應的。與胡適等人不同,田漢對傳統戲曲抱有深厚的感情。田漢的藝術觀念與全盤否定戲曲的觀點不同,他在承認傳統戲曲存在封建落后的部分的同時,主張保留傳統戲曲的特色,在此基礎上與西方文明的新型戲劇或是話劇不顧一切地靠攏。
在這兩個時期(即田漢先生產生戲曲藝術觀念的初期),由于當時中國傳統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沖擊,所以田漢的戲曲藝術觀念主要立足于中西方戲劇藝術的差異,從舞臺實踐的實體化角度提出廣泛建議,在中國傳統戲曲和外國戲劇的先進文明之間做出平衡。
在新國劇運動時期,戲曲形式上的改變基本定型,大體的程式已經得到了業內的廣泛認可。這時候田漢研究的重點就在于戲曲內涵的革新,改革重點從中西對比變成了古今對照。田漢對于傳統戲曲的主要批判在于舊戲當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田漢主張戲曲藝術應該貼近生活,貼近現實,真正成為平民藝術。
田漢的“新國劇運動”的戲曲改革初衷,在抗日戰爭時期得到了繼承和發揚。由于戰爭,百姓流離失所,戲曲舞臺也隨之四海漂泊。此時風花雪月的傳統劇目已經不能滿足受苦百姓的精神需求,因而從受眾層面根本性地改變了戲曲表現形式。戲曲是傳達創作者或其想要代表的階層的思想和聲音的藝術載體,因此在這樣一個全民抗戰的前所未有的時代,創作者更應該結合抗戰現實,為窮苦大眾發聲,達到振聾發聵的效果。
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強調要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田漢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戲曲改革更是大刀闊斧。新中國成立后,田漢的戲曲理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即舊劇的“民族性”和傳統劇目當中的鬼神元素。新中國成立后,強調各個民族和平統一,帶有明顯民族爭端色彩的劇目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但是田漢認為只要把握好其中的度,這些民族氣節是可以并入愛國主義精神當中的。對于傳統劇目當中的封建迷信,田漢并沒有全盤否定,而是傾向于對帶有神怪色彩的戲進行細致的劃分。對于借助鬼神和自然來寄托對未來的希冀的藝術表現形式,田漢給予了肯定,他認為這種表現形式與其說是迷信封建,不如說是百姓受迫于無力改變的黑暗社會而做出的微不足道的掙扎,因此這些不能被看作是舊時代的糟粕而被輕易丟棄。
二、田漢先生的主要理論觀點
從田漢先生在不同歷史時期對于戲曲理論的認識,可以歸納總結出他的三個最主要的理論觀點:
首先是戲劇當中的民族精神。在抗日戰爭時期,這一條基本可以作為田漢戲曲理論觀點的核心。眾所周知,抗日戰爭是一場民族解放戰爭,藝術作品要起到振奮民心、鼓舞士氣的作用。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田漢提出這樣的觀點是大勢所趨,這在當時形成了他戲曲創作的理論基礎。
其次是關于歷史劇的現實作用。根據記載,田漢在抗戰時期的主要創作主題是新編歷史劇,常常借古喻今、宣傳抗日救國的思想,借助歷史題材,與現實斗爭緊密連接在一起,盡最大可能地鼓舞人民的抗戰熱情。歷史劇有別于歷史,并不能完完整整地將華夏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悉數呈現在舞臺上,即便是膾炙人口的歷史故事也不一定就會適合戲曲舞臺。在保證戲曲表現形式的可行性以外,還要考慮到思想內容是否符合時代的需求以及舞臺表演的觀賞性。此外,田漢還提出,要注重歷史劇的歷史主義態度。在抗戰時期,舞臺藝術確實大多被應用在了宣揚價值觀和鼓舞士氣上,即便是田漢也創作了不少這樣的作品,但是在戰爭結束后這些斷章取義、含沙射影的作品就顯得不尊重歷史了,田漢先生認為這樣曲解歷史對歷史教育會產生不利的影響。改編歷史是有限度和底線的,田漢無論是在特殊時期進行的歷史劇創作還是在解放后提出的完整戲曲理論,都一直遵守著這樣的信條,即對傳統的繼承和革新、對舊劇的深化與創造。
最后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田漢在創作的過程當中,提出了戲劇創作的大眾化和通俗化的問題,在內容上有所創新的同時,也融入了各種藝術形式,對所有的舞臺藝術都一視同仁,由此達到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在當時的背景下,戲曲改革順應時代的需求,為了宣傳教育利用戲曲為抗戰服務,是抗日救亡時期戲曲改革工作的重心。
三、戲曲改革的變化
在抗戰勝利后,戲曲改革的大方向也產生了根本的變化。
首先田漢明確了一點,即戲曲與話劇屬于兩個不同的范疇,彼此間可以產生影響,但是不可以互相替代。這一點在當今社會也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沒有任何一種藝術形式有被時代淘汰的必要,在自身革新努力跟上時代變化的同時,民眾也要用一種包容的態度接納不同種類的藝術形式。
其次,田漢強調了劇本創作的重要性。在梅蘭芳時代,名角比劇情要重要得多,很多觀眾只是為了來看名角,劇本再粗糙也毫不在乎,但是這種片面的戲曲觀念是會被歷史摒棄的。劇本不應該只為角色服務,量身定做適合某位名角的劇本故事,這樣造成的明星化效應,并不利于戲曲文化的傳承,使得戲曲淪為博人一笑的工具。與此同時,田漢呼吁戲曲藝術要敞開懷抱,融合多種藝術形式,不同劇種之間也要取長補短,交流學習。
令人遺憾的是,田漢先生生前提出的改革思路,在當今時代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田漢先生的戲曲創作一直貫徹著他所堅持的戲曲理論觀點,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倡導民族精神,歌頌民族英雄,發動全體民眾,鼓舞抗戰情緒。田漢廣泛與戲曲藝人合作,使戲曲創作與舞臺實踐相結合,這在日后成為他獨特的創作方式。新中國成立后,田漢的歷史劇改編體現了他本人的戲曲觀,他注重舊戲中民族的、科學的、民主的成分,以提高民族的思想內容為戲曲改革的關鍵,不輕易否定舊戲中美麗動人的故事。這一時期,田漢的戲曲觀有所發展,戲曲作品不再只是被當作宣傳鼓動的工具,而更多地體現了對社會與人性的深層思考。這些創作是對傳統的繼承與革新,是對舊劇的深化與創造,他賦予了歷史故事嶄新的思想主題。
與其他戲曲理論家相比,田漢先生總顯得要官方一些,但是這種縱觀大局的審時度勢是十分必要的。戲曲改革并不局限于某個細節動作的糾正,或是某個劇本的構思是否巧妙,更多的是與社會、國家或是其他藝術形式產生的碰撞。田漢先生在多年之前就已經提出了對戲曲未來的擔憂以及戲曲創作將遇到的瓶頸,只有在解決這些前輩思考驗證過多次的難點問題之后,當今年輕的戲曲工作者們才有資格從前輩那里接過守護戲曲、發揚戲曲的接力棒,從多個角度完善戲曲,將之發展為既符合大眾審美又不至于失去初心和文化內核的通俗民間藝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