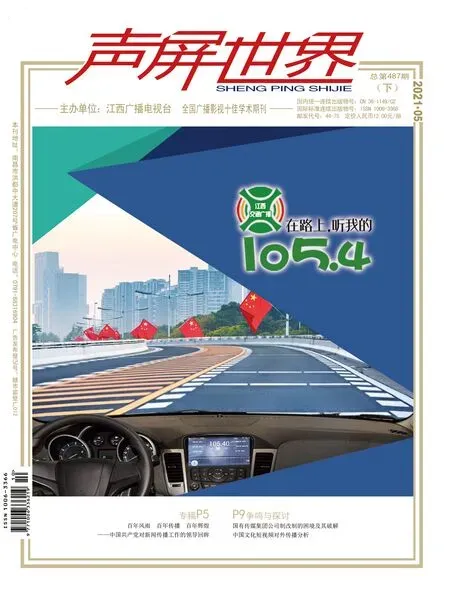中國紀(jì)錄片的詩意化現(xiàn)狀與趨勢探討
□ 劉小慧
紀(jì)錄片是紀(jì)實影像創(chuàng)作,真實是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的前提,同時,紀(jì)錄片也是創(chuàng)作者價值觀和審美的體現(xiàn),是詩意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近年來受到大眾廣泛關(guān)注的紀(jì)錄片無不是兼具客觀屬性和詩意特點的作品,無論是影像風(fēng)格、配樂特點還是解說與訪談的剪輯,乃至紀(jì)錄片深層的文化底蘊和審美追求,都體現(xiàn)出詩意的特點和風(fēng)格。
紀(jì)錄片詩意特點的元素與特征
紀(jì)錄片的詩意體現(xiàn)在畫面、配樂、解說、同期聲、結(jié)構(gòu)、文化底蘊等各個方面,全方位營造出詩意的文化氛圍。各個元素之間的關(guān)系是在統(tǒng)一的基調(diào)之下的有機配合,更是在統(tǒng)一的文化底蘊和審美追求之上的顯性因素。以引起廣泛關(guān)注和好評的紀(jì)錄片作品《掬水月在手》為例,這是陳傳興導(dǎo)演拍攝的記錄著名學(xué)者、詩人葉嘉瑩的紀(jì)錄片,它用唯美的鏡頭、細(xì)膩入微的訪談、余韻悠長的配樂、天馬行空卻又嚴(yán)謹(jǐn)獨特的結(jié)構(gòu)營造出詩一般的意象,帶領(lǐng)觀眾走近葉嘉瑩先生歷經(jīng)坎坷、閱盡滄桑、詩詞為伴、傳奇豐富的人生。兩個小時的作品讓人如醉如癡,這部紀(jì)錄片蘊含的詩意內(nèi)涵與元素恰恰可以作為了解紀(jì)錄片詩意形態(tài)的典范。
視覺上的詩意:鏡頭詩意化的蒙太奇處理。紀(jì)錄片通過影像呈現(xiàn)故事和詩意,通過光線、構(gòu)圖、色彩、動靜等鏡頭的運用來寫“詩”,在通過畫面的選擇、剪輯呈現(xiàn)詩意。《掬水月在手》一開始就運用了大量龍門石窟的石窟造像、壁畫、碑拓、地圖等畫面,光影與色彩很講究,看起來沒什么聯(lián)系卻展示了主人公出生成長的中國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時期,大量蒙太奇的運用營造出古今交融的歷史感和文化感。
在表現(xiàn)主人公在國破、喪母、喪女等人生悲劇時,大量運用枯枝、落葉、冰雪、荒原等畫面交錯剪輯,用環(huán)境的悲涼、蒼茫、寒冷、蕭瑟反映主人公內(nèi)心的痛苦、絕望和巨大的孤獨感。每一幅畫面都是一行詩句,每一組蒙太奇都是一首小詩,視覺上的詩意油然而生,帶領(lǐng)觀眾領(lǐng)略詩意的視覺美感。
聽覺上的詩意:精妙而豐富的配樂。作為紀(jì)錄片的重要元素,配樂的作用堪稱點睛之筆,對于立體詩意氛圍的營造非常重要。如果說語言傳達的是理性的、確定的信息,音樂則是傳達感性的、朦朧的信息,對于詩意氛圍的營造、觀眾想象力的打開至關(guān)重要。
《掬水月在手》的配樂是請日本作曲家佐藤聰明創(chuàng)作的雅樂《秋興八首》,雅樂是這部紀(jì)錄片期望重現(xiàn)唐時氣氛的重要因素。雅樂是當(dāng)年鑒真東渡日本保留下來的最接近唐代音樂的形式,包括樂曲形式、樂器演奏等。值得一提的是,片中用到的男女聲吟誦唱和,讓人繞梁三日,久久難忘,和影像、訪談等元素交相輝映,互相配合,呈現(xiàn)出如泣如訴、如歌如慕的詩意美感。
意象中的詩意:解說、訪談、詩詞交錯形成的情境。在紀(jì)錄片的表現(xiàn)形式中,同期聲、配音、解說等元素交錯剪輯,互相配合,形成全方位的綜合表達,而詩詞的運用更是詩意空間營造的靈魂。同期聲是質(zhì)樸的詩意表達,《掬水月在手》這部紀(jì)錄片全片沒有用解說,完全用主人公的同期,不同時期、不同場景的采訪、主人公學(xué)生、同事等人的采訪和各種詩詞來相互配合,尤其是《秋興八首》是葉女士的代表作,詩詞和畫面、配樂等元素融洽的結(jié)合,展現(xiàn)出全片的主題。主人公的訪談娓娓道來,將觀眾帶到特定的歷史時期和場景中,充滿了詩意的想象空間。
中國紀(jì)錄片詩意的內(nèi)涵
表現(xiàn)人與命運的關(guān)系。對人的關(guān)注是紀(jì)錄片永恒的主題。人的命運、人的情感、人的苦難、人的抗?fàn)帲谶@些終極命題中閃現(xiàn)出的人性光輝成就了紀(jì)錄片的詩意內(nèi)涵。
《掬水月在手》中,葉嘉瑩女士在人生的重重苦難和歷練中寄情于詩詞,穿越苦難,抵達永恒的詩詞之美。詩詞在苦難中度化了她,她穿越重重苦難成為了一代詩詞大家。電影里多次出現(xiàn)船和擺渡的象征意味著遇到生命中的困難時,詩總能把葉先生渡過去。這種隱喻讓觀眾領(lǐng)略到一種獨具的美感,命運多舛卻又山重水復(fù),幾度絕處逢生,始終如蓮綻放、不改初心,讓全片氤氳著詩意的人性之美。
展現(xiàn)性格和品德的力量。無論是哪種題材的紀(jì)錄片,終極的主角是人,表現(xiàn)人物的性格特點尤其是人性之美是紀(jì)錄片的深層內(nèi)涵。《掬水月在手》展示了主人公的“弱德之美”。“弱德之美”是葉嘉瑩先生對詞體的美感特質(zhì)提出的一種本質(zhì)性說法,在強大的外在壓力下,所不得不采取約束和收斂的屬于隱曲之姿態(tài)的一種美。而在葉嘉瑩身上同樣有著這種“弱德之美”,面對苦難和欺凌,隱忍不發(fā)卻又不屈不撓,默默地發(fā)展自己,柔韌地展示自己的生命和才華,讓人贊嘆。
中國紀(jì)錄片詩意的文化特質(zhì)
中國文化講究含蓄、意境,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以意境一詞來表現(xiàn)人與自然這一超越現(xiàn)實的審美關(guān)系。意境是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個性體驗。紀(jì)錄片要表現(xiàn)現(xiàn)實,而寫意性又是中國紀(jì)錄片深層的文化底蘊,在用視聽語言表現(xiàn)事實的同時,透著東方文化的審美意蘊。
寫意性的表現(xiàn)方式。如今隨著技術(shù)的發(fā)展,寫意性體現(xiàn)的更為精致,攝像器材設(shè)備以及技術(shù)的不斷發(fā)展,讓畫面更為精致和豐富,多種技術(shù)手段的運用讓紀(jì)錄片可以呈現(xiàn)一種陌生化的詩意。紀(jì)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主人公是草根詩人余秀華,這部表現(xiàn)詩人的紀(jì)錄片有著濃郁的詩意底蘊。農(nóng)村的風(fēng)物人情,大量的生活場景,自然的各種聲響,近乎白描的客觀記錄,對于人性的深刻刻畫,穿插主人公的詩歌獨白。這種種寫意性的表達帶領(lǐng)觀眾走近主人公內(nèi)心的孤獨和痛苦,身體的殘缺和令人驚艷的才華、現(xiàn)實世界和內(nèi)心世界的巨大反差形成一種張力,整個紀(jì)錄片仿若一首深情、雋永、綺麗又悲憫的詩,這種詩意令人動容、引人深思。
天人合一的生命意蘊。中國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文化底蘊是“天人合一”的東方文化,中國文化對于人和天地的融合、和諧有著很深的體悟和追求,在很多紀(jì)錄片中,人們都可以看到這種“天人合一”的文化內(nèi)涵。比如《舌尖上的中國》圍繞中國人對美食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展現(xiàn)了人在天地之間對于谷物、獵物、各種食材、各種烹飪方法的研究,數(shù)千年傳承下來的對于自然的敬畏,對于一日三餐的重視,透過看上去很普通的餐食來表現(xiàn)人的情感與追求,乃至天人合一的生命理念。
中國紀(jì)錄片詩意審美的發(fā)展回顧與展望
從中國紀(jì)錄片誕生開始,就有著詩意的基因,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紀(jì)錄片的詩意呈現(xiàn)出不同階段的特點和風(fēng)格。
單一到多元化的詩意表達。改革開放后,人們的自我意識增強,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有了更多的人文色彩和個人思考,中國的詩意化紀(jì)錄片由此而開始產(chǎn)生。早期紀(jì)錄片的詩意風(fēng)格較為單一,《話說長江》《話說運河》《絲綢之路》等早期的紀(jì)錄片以詩化的語言和鏡頭講述中國的人文地理,成為中國紀(jì)錄片“詩化模式”的開始。上世紀(jì)九十年代,中國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著重于人和人之間的關(guān)系,紀(jì)錄片的美學(xué)和哲學(xué)的意味逐漸增強,用詩意的鏡頭和語言來表現(xiàn)普通人的生活。
21世紀(jì)以來,中國紀(jì)錄片隨著技術(shù)發(fā)展,使用大量獨特的拍攝方式和后期特技,詩意的表現(xiàn)多為形式上的美感。近年來,智能手機的拍攝功能原來越專業(yè)化,一些導(dǎo)演甚至用手機來拍攝紀(jì)錄片和微電影。紀(jì)錄片門檻降低,紀(jì)錄片的詩意在商業(yè)和藝術(shù)之間平衡,風(fēng)格上趨于多元,出現(xiàn)了《舌尖上的中國》等一批藝術(shù)性、人文性和商業(yè)性結(jié)合得較好的紀(jì)錄片,成為現(xiàn)象級的作品。
宏大主題和個人敘事兼容并緒。宏大敘事反映時代、社會乃至人類層面的內(nèi)涵,強調(diào)整體性,善于表現(xiàn)宏大主題,對于社會有推動作用。比如《話說長江》《大國崛起》等紀(jì)錄片,表現(xiàn)宏大的歷史長卷和浩瀚的詩意風(fēng)情,而個人敘事則主要關(guān)注普通人的生活、命運,蘊含細(xì)膩、婉轉(zhuǎn)的詩意。近年來,不少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者嘗試將宏大主題敘事和個人日常生活敘事相結(jié)合,創(chuàng)作出《中國人的活法》等具有全球性話題,展現(xiàn)中國各地不同地域、不同職業(yè)的普通人生活的紀(jì)錄片。
微紀(jì)錄片的詩意化漸成趨勢。隨著技術(shù)的進步和人們欣賞習(xí)慣的改變,短小精悍的微紀(jì)錄片自2012年出現(xiàn)后吸引了眾多受眾。相對于傳統(tǒng)紀(jì)錄片,微紀(jì)錄片單集時長短,制作成本低廉,更為靈活,更有生活氣息。不僅是時長的縮短,更是具有了新的敘事結(jié)構(gòu),成為一種新的紀(jì)錄片形態(tài),而微紀(jì)錄片的詩意化趨勢也非常明顯,如《如果國寶會說話》《人生一串》《早餐中國》等微紀(jì)錄片,清新、婉約是詩意化的代表。
結(jié)語
不同題材和風(fēng)格的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如何打動人心,詩意是重要的標(biāo)準(zhǔn),優(yōu)秀的紀(jì)錄片作品往往具有詩意的特質(zhì),值得人們研究與探討。對于紀(jì)錄片來說,詩意的表現(xiàn)形式背后是詩意的內(nèi)涵和文化底蘊,探討紀(jì)錄片的詩意化元素、發(fā)展和趨勢,對于中國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有著現(xiàn)實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