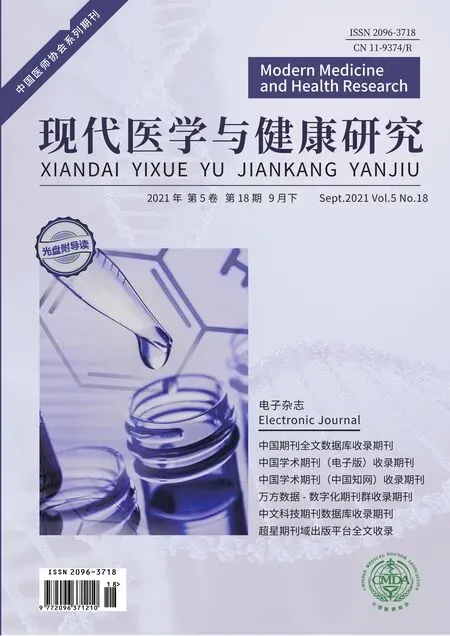經臍單孔腹腔鏡與開放式疝囊高位結扎術治療腹股溝斜疝患兒的臨床療效
涂學廣
(贛州東河醫院普外科,江西 贛州 341099)
小兒腹股溝斜疝屬于常見的外科疾病類型,臨床認為,小兒腹股溝斜疝的發病原因多與鞘狀突未閉有關,同時因各種因素導致的腹壓升高也會誘發小兒腹股溝斜疝的發生。傳統開放式疝囊高位結扎術操作復雜,耗時較長且創傷較大,具有較高的復發率,嚴重影響患兒預后[1]。隨著醫療技術的發展與進步,腹腔鏡技術已被運用到小兒腹股溝斜疝的臨床治療中,與傳統的開放手術治療相比獨具優勢。其中經臍單孔腹腔鏡手術對患兒的創傷小,且具有恢復快、復發率低的特點,腹腔鏡輔助下術野開闊,可完全顯露內環口、疝環,于環內扣進行疝囊結扎,減少手術對患兒神經組織的傷害,有利于改善患兒預后[2]。基于此,本研究主要針對經臍單孔腹腔鏡與開放式疝囊高位結扎術在小兒腹股溝斜疝中的臨床療效展開分析,現將研究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6年9月至2020年9月贛州東河醫院收治的86例腹股溝斜疝患兒作為研究對象,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對照組(43例)和觀察組(43例),對照組中男患兒33例,女患兒10例;年齡20個月 ~10歲,平均(5.90±2.57)歲;患病部位:左側疝18例,右側疝25例。觀察組中男患兒35例,女患兒8例;年齡19個月 ~10歲,平均(5.85±2.46)歲;患病部位:左側疝16例,右側疝27例。兩組患兒一般資料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組間具有可比性。診斷標準:參照《實用小兒外科學》[3]中關于腹股溝斜疝的診斷標準。納入標準:符合上述診斷標準者;術前經彩超檢查明確為單側原發性腹股溝斜疝并無嵌頓者;依從性良好,積極配合者;無手術相關禁忌證者等。排除標準:急性嵌頓疝者;復發疝者;腹部有手術史者;合并心、肝、腎、腦重要器官功能障礙者等。本研究經院內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且患兒法定監護人已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所有患兒均于術前6 h禁食、禁水,在術前0.5 h取開塞露實施肛門注射,并排空膀胱,患兒進入手術室后立即進行心電監測,觀察心電圖狀況,并建立靜脈通道。對照組患兒行開放式疝囊高位結扎術,實施靜脈全身麻醉,患兒取頭高腳底位,偏轉手術床至需要手術一側,在疝內環口對應的體表投影處作一2.0~2.5 cm的斜切口,依次對皮膚和皮下組織行鈍性分離,不切開腹外斜肌腱膜,對未閉合鞘狀突或疝囊位置實施準確定位,辨別疝囊與精索血管之間的解剖關系,在無血管區域將疝囊解剖開,根據疝囊的大小對疝囊實施完全剖離或者橫斷,將其游離至高位后,使腹膜外脂肪組織充分顯露出來,再對鞘狀突或和疝囊實施雙重縫合,皮下縫合處理后,結束手術。觀察組患兒行經臍單孔腹腔鏡手術,術前準備和麻醉方法同對照組,使患兒取平臥體位并將臀部墊高,在臍正中位置作一5 mm的豎向的切口,置入氣腹針(5.0 mm)和腹腔鏡,建立人工氣腹,壓力參數維持在8.0~12.0 mmHg(1 mmHg=0.133 kPa),流量參數為2.0~2.5 L/min,在腹腔鏡下探查疝內環的位置,經此切口處將疝環穿刺針放置腹股溝管內環處位置,并從腹膜外沿著內環扣外上方穿至內環扣內下方,穿出腹膜,將雙線置于腹腔,隨后將穿刺針撤出。經過相同的穿刺孔將穿刺針再次穿入腹腔,同時穿刺至內環前壁腹膜外,并與第一針交匯后穿出,將雙線拉出,經過穿刺針將單線放入腹腔,再將穿刺針撤出。以雙線自腹中將單線帶出,壓迫腹股溝和陰囊,將疝囊中的氣體排出,最后實施皮下打結剪線,提起腹股溝區域的皮膚組織和皮下組織,使得線結埋于皮膚的深層后,結束手術。兩組患兒均于術后觀察7 d。
1.3 觀察指標 ①比較兩組患兒手術相關指標。包括術中出血量、切口長度、手術時間、下地活動時間及住院時間。②比較兩組患兒術前與術后24 h炎性因子指標。采集兩組患兒空腹靜脈血3 mL,以3 000 r/min的轉速離心10 min,分離血清,使用酶聯免疫吸附實驗法檢測血清C- 反應蛋白(CRP)、腫瘤壞死因子 -α(TNF-α)及白細胞介素 -6(IL-6)水平;血液采集方法同上,采用血細胞計數儀檢測外周靜脈血白細胞計數(WBC)水平。③比較兩組患兒術后7 d內并發癥發生情況。包括切口線結反應、感染、陰囊血腫、腹脹、睪丸異位及繼發鞘膜積液。
1.4 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 22.0 統計軟件分析數據,計量資料(手術相關指標、炎性因子指標)采用(±s)表示,行t檢驗;計數資料(并發癥發生率)采用[ 例(%)]表示,行χ2檢驗。以P< 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手術相關指標 觀察組患兒術中出血量少于對照組,手術時間、切口長度、下地活動時間及住院時間均短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兒手術相關指標比較( ?±s)

表1 兩組患兒手術相關指標比較( ?±s)
組別 例數 術中出血量(mL) 手術時間(min) 切口長度(cm) 下地活動時間(h) 住院時間(d)對照組 43 10.55±3.42 22.22±3.44 2.29±0.16 22.65±2.64 5.13±1.63觀察組 43 5.22±2.13 12.31±2.26 0.45±0.05 13.12±1.78 3.02±1.01 t值 8.675 15.788 71.978 19.627 7.216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2.2 炎性因子水平 與術前比,術后24 h觀察組患兒外周靜脈血WBC及血清CRP、TNF-α、IL-6水平均升高,但觀察組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兒炎性因子指標比較( ?±s)

表2 兩組患兒炎性因子指標比較( ?±s)
注:與術前比,*P < 0.05。WBC:白細胞計數;CRP:C- 反應蛋白;TNF-α:腫瘤壞死因子 -α;IL-6:白細胞介素 -6。
組別 例數 WBC(×109/L) CRP(mg/L) TNF-α(μg/L) IL-6(pg/mL)術前 術后24 h 術前 術后24 h 術前 術后24 h 術前 術后24 h對照組 43 6.11±1.11 9.25±1.14* 2.61±0.13 5.66±1.21* 1.26±0.07 3.37±1.49* 3.40±0.64 5.21±1.81*觀察組 43 6.04±1.06 7.15±1.22* 2.62±0.09 3.43±1.44* 1.27±0.08 2.64±1.14* 3.41±0.83 4.27±1.22*t值 0.299 8.247 0.415 7.775 0.617 2.552 0.063 2.824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3 并發癥 術后7 d內觀察組患兒并發癥總發生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兒并發癥發生率比較[ 例(%)]
3 討論
臨床中小兒腹股溝斜疝自愈的可能性較低,主要采用開放式疝囊高位結扎術和經臍單孔腹腔鏡手術治療,前者主要是經過腹股溝解剖后尋找到疝囊進行處理,為此需要對腹壁組織實施逐層分離,但是對疝囊的游離操作,極易對精索、輸精管及神經等組織帶來不同程度的組織損傷,尤其在鞘狀突未閉合的隱匿性疝情況時,該手術方法存在明顯的局限性[4]。
經臍單孔腹腔鏡不需要破壞腹股溝解剖結構,也無需對提睪肌和精索實施游離操作,進而避免了對神經、血管的損傷,在腹腔鏡清晰的視野下實施內環口周圍縫合,做到了真正意義上的高位結扎,該手術方法創傷較小,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血腫、切口線結反應、術后感染等并發癥的發生率[5]。此外,腹腔鏡手術方法的應用,能夠在腹腔鏡直視下明確觀察疝內容物血運情況,明確隱匿性疝的探查和復位過程中是否有損傷,從而在術中實施同期處理,避免了開放性手術造成對腹股溝管解剖結構的破壞;在腹腔鏡下完成相關手術操作,更有利于了解精索血管的走向,提高手術操作準確度,減輕對腹股溝管及周圍組織的傷害,減少術后相關并發癥的發生[6]。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患兒術中出血量少于對照組,手術時間、切口長度、下地活動時間及住院時間均短于對照組;術后7 d內觀察組患兒并發癥總發生率低于對照組,提示經臍單孔腹腔鏡治療腹股溝斜疝患兒,可減少術中出血量,縮短手術時間,且減少并發癥的發生,安全性較高。
在對腹股溝斜疝患兒行手術治療時,手術和創傷均會刺激機體線粒體細胞和內皮細胞,使患兒機體產生應激反應。外周靜脈血WBC作為細菌感染與炎癥反應時的非特異性標志物,在人體組織損傷或發生感染時,水平升高,使得機體內產生大量嗜酸性粒細胞因子、肥大細胞等,從而導致血清IL-6、CRP、TNF-α等炎癥介質聚集,水平升高[7]。本研究結果顯示,與術前比,術后24 h觀察組患兒外周靜脈血WBC、血清CRP、TNF-α及IL-6水平均升高,但觀察組低于對照組,分析原因為,經臍單孔腹腔鏡手術對患兒的創傷較小,在較小的切口下,可保護疝囊內環口組織,減輕了手術對血管及其周圍組織的損傷,應激反應較小,避免了感染風險,有效地降低炎癥反應[8]。但在行經臍單孔腹腔鏡手術時需注意對腹腔鏡疝氣針的選取,若針尖太尖銳會對血管、輸精管等造成傷害;若針尖太鈍會導致腹膜外潛行的分離效果不理想,對患兒的治療產生不良影響,因此手術操作要求相對更為嚴格。
綜上,對小兒腹股溝斜疝治療中,應用經臍單孔腹腔鏡手術,具有創傷小、恢復快、效果顯著的優勢,可減輕機體炎癥反應,且安全性高,值得臨床進一步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