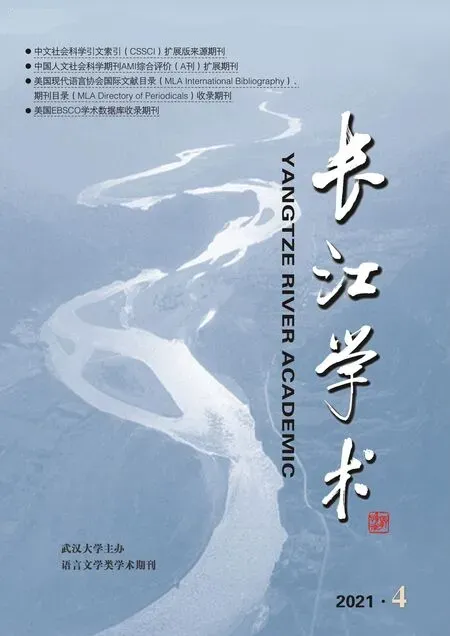西周冊命銘文的文體生成
李明陽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北京 100026)




一、冊命記載的文本認定





克罍蓋銘拓本

克盉蓋銘拓本


與此對應,書類文獻或出土竹簡中的冊命文本是以簡冊形式傳抄并流傳于世的冊書,其主要內容是王的詔令。然而,鑄刻銘文時的底稿由于未被傳抄,全部散佚了;考古發掘出的絕大多數竹簡寫定于戰國時代,經歷西周、春秋與戰國的不斷傳抄,導致今文《尚書》中出現各種訛誤,甚至偽托相關史事擬作的先王詔令層出不窮。我們還應考慮到,抄本時代的文獻具有“流動性”特點,這些文本有可能是直接抄錄,也可能經過了追憶、想象、演繹和改寫,還可能在傳抄中出現各種訛誤。如果說,簡冊與銘文均有被視為“冊命文本”的理由,那么維系前者的文體要素只有冊命儀式和內容的規定性,而后者則在整個敘事環節中體現出格式性的策略和安排,加之書類文獻和出土竹簡中出現的追憶、想象、演繹、改寫等現象,筆者認為,或許為數眾多的青銅器銘文才是更值得深入關注的文體學范本。
二、冊命銘文的文體演進
冊命儀式在西周中期漸趨成熟,冊命銘文也很快形成了穩定的書寫范式。顯然,一篇完整的冊命銘文包括四種基本要素:時間地點、儀式過程、作冊用途(如“用作某公寶尊彝”等)和禱祝語(如“對揚王休”等),書寫范式的定型體現了敘事的內在要求。下文即梳理西周冊命銘文的結構和話語方式變化,探尋西周時代的敘事要素和載錄方式的發展脈絡。




縱觀西周時代的銘文寫作,西周早期和中期,冊命銘文逐漸擺脫商代文化而建立宗周的時代風格,文辭漸趨明晰和典范,冊命儀式的時間、地點、過程、作器用途等要素得以清楚地記載和呈現。從而在西周中期,對冊命儀式的記載形成了高度穩定的書寫程式和語言規范。至于西周晚期,冊命銘文雖然總體保持了以往的風格,但筆墨稍顯簡省。
三、西周彝銘的撰鑄制度



除銘文的撰寫外,還要考慮到在鑄刻銘文時,工匠很可能根據器型等情況對史官提供的底稿加以潤色和修改,因此,不得不對銘文的鑄刻制度加以考察。




結語
簡冊和銘文是冊命文本的兩種介質形態,前者多為冊命儀式上宣讀、傳遞的文書,后者則是史官對冊命儀式的全面載錄,因此冊命文體研究應高度關注銘文文本。冊命銘文的基本要素包括時間地點、儀式過程、作冊用途和禱祝語。上文已對各要素的詳細變化作了梳理,揭示出這些要素在西周中期的銘文書寫中逐漸聚攏,形成冊命銘文清晰而典范的書寫風格,至西周晚期又再度歸于簡潔的總體趨勢。由于銘文的撰寫者供職于受冊命貴族,銘文側重體現受冊命者的意志,在凸顯冊命儀式榮耀的同時強化了周王室的權威。筆者猜想,銘文語詞的一致性可能與工匠對底稿的潤色有關,因此,冊命文體是國家意志與貴族愿望的綜合體現,也是史官與工匠共同參與禮樂文明建構的結果,并推動著周代意識形態的生成、凝聚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