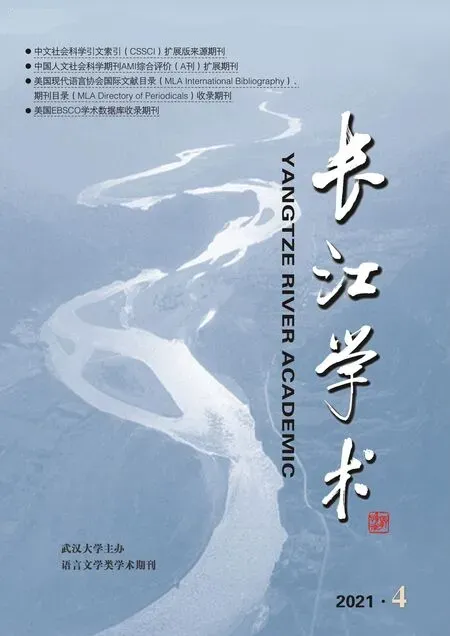回溯性建構與拉康精神分析的倫理指歸
葉娟娟 朱國華
(華東師范大學 中文系,上海 200241)
引言:蓋世太保-撫摸皮膚(Gestapo-geste à peau)





一、回到弗洛伊德





二、回望善的幻象



為從他者欲望的裹挾中析出主體的面貌,拉康分兩個途徑對他者欲望進行拆解:一是在精神分析大廈中架入語言學理論,指出無意識是像語言一樣建構的,以此闡釋他者欲望對主體的植入過程;二是通過“康德與薩德”裝置,展示了象征界如何以純粹實踐理性或意志的命令,即一種絕對強力的意志,以倒錯的形式對主體施以薩德式淫穢主體的無節制之惡,拉康還以這一裝置徹底瓦解了西方理性主體的自主自明神話。
拉康倒轉了索緒爾的所指/能指公式,將其轉換為S s
意謂能指在所指之上),以圖示的形式強調了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阻隔,表示能指與所指之間并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確立了能指的優先地位。按照拉康的觀點,由于能指是不斷滑動的,能指無法真正錨定所指,然而,正是在能指與所指之間產生的詞語裂縫中,實在界的真相往往得以突破符號秩序的邊界而閃現,這也是后來齊澤克所闡發的“實在界的鬼臉”。在本文開篇所講述的案例中,拉康正是利用能指的滑動這一特質,捕捉了掩藏在“實在界的鬼臉”之后的主體真實欲望,即,以“撫摸皮膚”為表象的指令,要求主體確認自身的存在。另一方面,拉康以“康德與薩德”裝置對西方傳統倫理所構想的自明主體進行了拆解。傳統倫理以及弗洛伊德之后的自我心理學,都允諾主體在獲致善與快樂之間是正相關的關系,但拉康表示這是一種幻象,是虛假的承諾,因為善與快樂都具有兩重性,二者有其自身無法解決的悖論。善與惡是一體兩面的,善的理念之倒轉就是惡的意志。快樂達到一定限度后就會轉變為痛苦,通過“欲望是法則的反面”,善以純粹實踐理性或意志的命令強加到主體身上,這與薩德式淫穢享樂主體互為鏡像,這就是拉康所說的“薩德從后門溜進了康德的臥房”。拉康以原樂(Jousissance)作為支點,撬開了西方啟蒙倫理至善的背面,揭示至善與極惡之間的同質性。由此,拉康要求人們警惕道德自身的悖論,因為其所暗含的善/惡之辯證,已經最有力和直觀地呈現在當代以允諾未來幸福的名義而施行的政治之暴中,即,以至善為道德意志凌駕于個體生命之上——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政治殺戮都借由此法則,昭示道德強大的同時也暴露了其致命性的殘酷,尤其以奧斯維辛集中營宣告了西方理性的全面潰敗。為此,拉康及其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主體與理性、理論與實踐的關系。


三、回溯主體的個人史
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傳統倫理學有其本體論意義上的基礎,即人對幸福和至善的追求有其自然的目的和傾向,就如先有桌子的理念,后有匠人根據這一理念打造出完美的桌子,它們指向的是本體性的完善,或最理想的自我實現。因此,在傳統倫理學觀念中,主體的完美和諧與主體對幸福和至善的追求是同質的,它們在本體論意義上有其自然的根基。在亞里士多德之后的基督教世界,“實在”與“虛構”還未出現對立,上帝與人及萬物處于一個等級森嚴、和諧一體的封閉世界中,一切事物按照上帝的至高理念被賦予了自然本性。但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封閉世界被瓦解為一個開放的無限宇宙,中心解體,至高之位不復存在,至善理念開始失效,現代性的倫理和價值體系必須為自身重新尋找新的根基。人類的生存環境從封閉世界置換為無限宇宙,意味著宇宙中心點與至善理念的徹底失落,宇宙不再以統一整體的形式運轉,宇宙中的匱乏部分成為支撐宇宙存在的本質所在。匱乏部分成為實體意義上的空位,以懸置的無有狀態賦予宇宙以無限性。



不論是哲學還是科學,都有自己關于世界統一圖景的想象,在拉康的精神分析領域里,母嬰同體就充當了這個統一圖景的原初神話。主體從完滿中永遠失落的原初場景,在其他人類文明圖景和闡釋體系中也有相似的文化符號,如圣經故事中亞當



命名之時,由于主體尚未與象征界主動契合,這種他者欲望對主體的嵌入其實并不深刻,主體對于命名的認同是被動發生的,主體在后來的個人成長中仍可以對該命名進行拒斥,甚至依據象征界的法則對其進行擦除。鏡像階段主體對鏡像的認同則較為復雜,主體在本質上也是被動的。通過他者和象征界對主體的詢喚,主體在經歷了原初的失落后,能夠表現出對鏡像進行主動認同的姿態,從而接受象征秩序即大他者對主體的統攝。
這里涉及拉康精神分析倫理的另一個重要維度——認同。主體在母嬰同體時期的自我認同是依托于母體的,不論尚在母親子宮里的胎兒或是剛出生的嬰兒,在還未意識到自己與母親身體的事實分離之前,嬰兒對自我的認同表現在對母親的持續依賴上,母親就是自身的一部分。當嬰兒開始觀察鏡中自己的反射形象時,父母或其他人會不斷重復將鏡像等同于嬰兒的指認行為,對嬰兒說:“看啊,這就是你!”在外界和他者的反復指示下,嬰兒將鏡像中的完整統一形象與自我進行對等聯系,并在日常生活中以各種形式不斷重復和強化。然而,實際上,不同于鏡中看起來和諧統一的整體形象,主體體驗到的是自身的分裂感及對肢體的支配無力感,二者之間形成了沖突。拉康指出,鏡像作為理想自我外在于主體的虛幻形象,與主體自身形成對立,對鏡像的認同包含著對主體自身的否定,并對主體自身展開了競爭,這無疑造成主體對自身的額外消耗。當主體沉睡于自我的幻想中時,就迷失了主體本來之處,也漸失自己的本然狀態。故而,主體應該穿越幻象,走出他者欲望的詢喚,立定自身,承擔主體的命運,這也是精神分析中主體的倫理責任所在。
四、他者的介入與主體的干預
在上述拉康所回溯的兩個重要時刻所發生的主體認同,無一例外都涉及主體對他者欲望的處理。主體一出生就降臨于象征秩序中,落入符號之網,以語言來言說使主體得以進入社會關系的構成,而主體的言說要求有聽者的在場,聽者充當了拉康意義上分析情境中的他者。他者的存在,使主體的言說具有了介入現實的可能,而介入現實,則是主體對自身存在進行的自我干預。


他者在拉康的理論中是一個重要的多面相概念,它包含了以下幾層涵義:大他者(Autre),可以理解為意識形態的存在,在象征界無處不在,統攝性地籠罩其中,以絕對強勢的權威和意志要求主體臣服,遵守大他者的法與禁忌;小他者(autre),既是相對于主體的其他主體存在,又同時作為概念而獨立于具體主體之外,亦如大他者是一種身份定義;更為重要的是拉康極為重視在精神分析關系中的他者,此時,他者可以是分析師,也可以是分析者,在更廣泛的范疇內,他者可以是外在于主體的其他物之在場。
他者是相對于主體而言的,二者是互證的概念,主體亦是他者的他者。拉康精神分析在恢復主體性的同時也重視他者的作用。主體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亦需要從兩個層面來看待:一是肅清他者欲望對于主體的異化,以使主體從他者欲望疊加的壓力下掙脫出來,不向他者的欲望屈服;二是這一事實背后顯示的是主體對于被認可的需求,主體通過滿足他者欲望以期獲得他者的認同,以此確證自身的存在和價值。因而,主體是始終與他者相纏繞的概念,此二者可以被視作一組“對子”概念,它們不能孤立存在。
我們始終要明確拉康的一個立場,其對符號化和大他者對主體作用的分析,并不是為了將符號置于主體存在的對立面。正如拉康高呼主體應直面自身的欲望,并不是號召主體要縱容自己的欲望。拉康反復要求主體警惕他者欲望對主體的異化,又極為重視主體通過與他者的關系建立來觀照自身。與拉康的回溯性建構始終指向主體的當下境況同質,拉康精神分析倫理所指向的也始終是主體的恢復。
拉康的精神分析要達到的臨床效果是使主體直面自己,站回主體之位,接納自身,而不是用如鏡像般的統一整體幻象來對自我進行異化,因為對幻象的沉浸只會使主體在喪失自我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拉康雖然剖析他者欲望對主體的強制置入,以使主體能夠拒絕他者欲望帶來的不良影響,但也始終表示主體的存在需要他者的介入。他者的介入當然不是符號化社會下為主體提供自我心理學派的“矯正”觀念,而是在認同主體的存在需要與他者形成互動的前提下,形成一種精神分析式的關系。以分析師為例,在一段精神分析經驗中,分析師的角色排除了生活經驗和大他者的暴力意志輸入,提供主體在言說過程中與實在界的真實相遇的渠道。拉康的精神分析比之弗洛伊德更向前邁進的一步是使精神分析脫離了生物主義的桎梏,在文化研究層面具有了建立一門新的宇宙論的宏大格局。因而,在精神分析關系中,分析師與他者,作為分析者與主體的對子角色,可以替換為在主體日常經驗中所相遇的其他介質,如文學與藝術。拉康表示,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原物(das Ding)的性質,可以物的形式使主體遠離他者欲望的裹挾,填補主體的匱乏;又因為擺脫了語言和符號的暴力與意志,為主體提供了無的空間,供主體在此與自我相遇,以空無的形式提供了主體復位的可靠途徑。這是拉康精神分析的倫理觀對我們理解自身以及與文學藝術建立緊密聯系的價值所在。
結語
回溯性建構最重要的特質在于它是根據現在來對過去作出新的理解,建構的立足點始終是主體的當下境況。拉康以回溯性建構的方法,回溯主體個人神話史的寓言式重要時刻,厘清了在拉康精神分析視域下主體困厄處境的來源以及突圍之法。拉康以同情的目光回溯主體的境遇,指出主體個人史籠罩在悲劇色彩之下,因而其精神分析的倫理永遠指向主體。
拉康的這種以回溯性建構為方法論,始終堅持訴諸恢復主體性的倫理關切,深深影響著同時代及之后的大量思想家,例如巴迪歐注意到拉康通過回溯而厘清的主體是分裂的、匱乏的主體,正是這種主體支撐著真理的存在。巴迪歐承襲了拉康的“反哲學”立場,堅持對標準化的排斥、對偽善的追求幸福的排斥,堅持思考真理和知識之間的關系。阿爾都塞和齊澤克對拉康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的連接,激發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文化研究和意識形態批判上新的活力與激進性。德勒茲和瓜塔里的“精神分裂分析”主張“反俄狄浦斯”,將欲望視為生產性力量,實際上也未能超出拉康精神分析所探討的命題范疇。
總體而言,通過定位回溯性建構作為方法論在拉康思想中的作用,我們能夠理解為何說在結構主義浪潮中,拉康是為數不多的致力于恢復主體性的人,也正是因此緣故,齊澤克堅決反對將拉康視作結構主義者。拉康精神分析的倫理不在于教人如何獲得幸福快樂的善,它要求人必須從生命的悲劇向度中直面主體的命運。將主體的生命經驗交付大他者、象征界的秩序與父法、想象界的幻象,都是對主體存在的盲目置換,只有主體確認自身的存在,直面主體的欲望,才能穿越我思與他者欲望編織的幻象,擺脫象征界與他者對其異化的根基。回溯性建構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思路,即從符號秩序的統治和掌控的企圖中審視主體的當下境況,通過回溯將被自足的我思主體(幻象)排擠出去的主體移歸回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