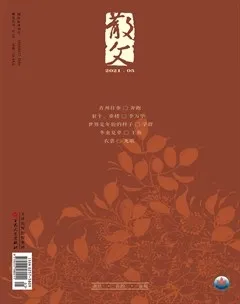青州往事
奔跑
一
十年,對一個人意味著什么?對一個時代又意味著什么?
我們在到達青州的當日下午,就尋訪了李清照故居。不巧的是,南陽河畔的“歸來堂”已被關閉,等待維修。來一趟不易,我們只好有樣學樣,翻了女詞人家的院墻。
夏日雨后的庭院,芳草萋萋,有一種潮濕的氣息在鼻尖游弋。院中林下一座涼亭,紅柱黛瓦,有一桌兩椅,似乎在等待醉酒的主人歸來。這時,你要吟誦“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的詩句嗎?
女詞人已遠足,家門緊鎖,墻皮剝落,墻根不知名的小株綠色植物在迎風搖曳。門外不遠處就是長長的游廊,與永濟橋隔湖相望。微風蕩漾,送來藕花淡淡的清香。“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那個憨態可掬的女子猶在眼前。抑或是那個相思的人在倚欄而立,默默感喟“為君欲去更憑欄,人意不如山色好”。
1107年,趙明誠李清照夫婦帶著家庭變故的創傷,回到乃父趙挺之的青州老家。他們在這所“私邸”共同生活到1121年。這一年,趙明誠再次被起用,出任山東萊州知府,李清照隨夫搬到萊州。四年后,1125年,趙明誠轉任淄州知府,李清照不再跟隨,而是返回青州歸來堂,獨自居住到1127年青州兵變前夕。
在名作《金石錄后序》中,她將自己的青州歲月稱為“十年屏居”,實際上是大約十七年。
“屏居”,就是“幽居”“隱居”之意吧。他們將空置的趙家老宅稍作打理,取陶淵明先生《歸去來辭》旨趣,“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命名為“歸來堂”,女主人則自號“易安居士”。兩口子過起了“幽居”的日子,繼續他們的金石文物收集研究和文學創作。
其間,作為京東重鎮的青州,知府像走馬燈似的換了十幾任,我們卻看不到半點記載能夠表明這位宰相公子兼前正六品官員與他們有過任何往來,哪怕是酒桌上的逢場作戲。
這十年仿佛天賜。才華橫溢的一對青年,在此迎來他們的新生活。他們成為完美接力歐陽修、范仲淹、蘇軾的時代“后浪”,就像明代詩人吳寬曾在《易安居士畫像題辭》中所稱道的那樣,“金石姻緣翰墨芬,文簫夫婦盡能文”,天然地以“學術夫妻”和“文藝伉儷”的姿態,成為那個治亂輪轉間真正的神仙眷侶。
簡樸的蟄居雖不富裕奢華,但也衣食無憂。他們全心投入的學術研究和文物收藏結出了碩果。一部《金石錄》初稿,高水平地弘揚了“金石證史”“碑刻互證”的治學傳統,同時保留了許多早已散佚的珍貴史料,成為中國古典文獻學繞不過去的一座高峰。2020年10月30日,這部流傳下來的巨著,入選中國第六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留下的,當然還有無盡的美好日常。
二人沐浴在金石研究的簡單快樂中。“每獲一書,即同共勘校,整集簽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為避免過于沉湎其中而影響休息,他們甚至不得不約定,“熬夜”當以一根蠟燭燃盡為限。
對于這樣的美好日常,易安還這樣寫道:
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后。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
(《金石錄后序》)
這種“賭書潑茶”的居家日子,甚至招來了幾百年后另一個詞作家的借用,寫下同樣撩撥無數心靈的詩句來懷念他的亡妻:
誰念西風獨自涼?蕭蕭黃葉閉疏窗。沉思往事立殘陽。
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
(納蘭性德《浣溪沙》)
為搜集金石碑刻,趙明誠不時要外出考察。從大觀到政和年間,他與妹夫李德升等曾兩游青州西南的仰天山,三游濟南靈巖寺。他們還曾登臨泰山,多次造訪京師汴梁。 “(郭巨)墓在今平陰縣東北官道旁小山頂上……余自青社(即青州)如京師,往還過之,屢登其上。”(《金石錄》卷二十二)這樣的記錄還可以找到若干條。
趙明誠的出游,三五天到一兩個月不等,制造了不少夫妻的“小離別”,惹來女詞人的諸多相思佳作,千年傳誦不衰。
莫許杯深琥珀濃,未成沉醉意先融。疏鐘已應晚來風。
瑞腦香消魂夢斷,辟寒金小髻鬟松。醒時空對燭花紅。
(《浣溪沙》)
不要說這酒杯太深,不要說琥珀色的酒太濃,而未醉即已意蝕魂銷。琥珀濃,瑞腦香,辟寒金,燭花紅,色調高華,渲染了濃郁的抒情氛圍。據說,這是作于大觀二年后某年之春。
寂寞深閨,柔腸一寸愁千縷。惜春春去,幾點催花雨。
倚遍闌干,只是無情緒。人何處,連天衰草,望斷歸來路。
(《點絳唇》)
在寂寞深閨中,能倚靠的欄桿都倚靠遍了,還是打不起精神啊,唯有“惜春”與“懷人”了。
蕭條庭院,又斜風細雨,重門須閉。寵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閑滋味。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
(《念奴嬌》)
這善變的早春時節,連天氣都是“惱人”的,而且是“種種惱人”!一列列鴻雁都飛過去了,這要寄給遠方的信卻還沒有寫完……
——這“書袋”掉得愉快啊!一支秀筆,寫盡天下小別離情。用現在小資語言說,這是怎樣一種幸福的“慢時光”呢。
對這樣的日子,易安后來總結得到位:“甘心老是鄉矣。”而少有詩詞留世的趙明誠呢?在易安三十一歲小像畫成時曾題詞云:“清麗其詞,端莊其品,歸去來兮,真堪偕隱。”有這樣可心的佳人一道歸隱,夫復何求?
沒有多余的社交,沒有世俗的喧囂,只有琴瑟和鳴、歲月靜好。在女詞人的一生當中,青州是留在她心里的,永遠的、唯一的家。
這就是他們“屏居十年”之三味吧。
二
而這樣和美的青州日子,卻濫觴于五百公里外汴京朝堂上的持續斗狠。
此時,王安石、司馬光早已作古,連蘇軾、章惇也新喪未久,新舊黨爭已然是“后變法時代”。君子之風的政見博弈,已蛻變為權謀“宮斗”乃至政治迫害。其間,易安夫婦的父輩李格非、趙挺之先后應聲折戟。
1100年,宋徽宗趙佶即位,任用“新黨”蔡京為相,再次全面推行新法。在其支持下,蔡京等以崇奉“熙寧新法”為名,羅列元祐舊黨名單,斥之為“奸黨”,御書刻石于端禮門及各地官府,并嚴厲要求:凡名在黨籍者,不能在京師任職與居住;宗室、官員不得與其聯姻,已定親但未交換聘禮聘帖者,必須退掉——是為惡名昭著的“元祐黨人案”。
是時,趙挺之任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屬新黨干將,力主打擊元祐黨人。李格非任禮部員外郎,因與蘇門關系密切,被列入元祐黨人“黑名單”,其最終結局史料竟語焉不詳:一說流放廣西象郡,再無記載;一說返回原籍山東章丘明水,并于幾年后終老是鄉。
翻手為云,覆手為雨,不斷拉抽屜,是北宋中晚期政壇的特點。1106年,宋徽宗毀元祐黨人碑,大赦天下。拜官尚書右仆射的趙挺之,卻在與蔡京的爭權中敗落,次年三月被罷,五天后郁悒而死,隨即被抄家,族人凡在京者一概被押,至七月方獲釋。趙家雖不至被逐出汴京,但已受重創。趙家三兄弟各有安排,趙明誠一出獄,便與李清照離京,前往青州。
黨爭掀起的政治狂瀾,逐步將王朝拖入時代旋渦,卻留給了這對小夫妻十年的時光,讓他們退避山壑,享受了片刻的寧靜。
柳詒徵先生說:“蓋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純出于士大夫之手,唯宋為然。” (《中國文化史》)相比較于東漢后期的外戚、宦官和士大夫之爭,唐后期“牛李黨爭”,明末東林黨和閹黨之爭,北宋新舊黨爭是中國古代史上唯一一次發生在士大夫內部的政見之爭。有研究者認為,其性質最為接近現代政黨政治。
在科舉制度的引導下,北宋士大夫集團崛起于唐與五代的庶族士人階層,具有強烈的參政意識和“共治天下”的政治激情,他們如期迎來以“文治”立國的趙宋,尤以真宗、仁宗和神宗朝為黃金時期。
至熙寧年間(1068—1077),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變法。因為政理念不同,形成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新黨”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反對變法的“舊黨”。兩黨不斷分化與組合,到哲宗、徽宗、欽宗朝,由“理念之爭”蛻變為“人事糾葛”,內政外交陷入紛亂,終于招致了外侮。
青州十年,一對士大夫的后代僥幸獲得一個以學術為寄托的療傷期,對這個王朝、這個時代又意味著什么?
士大夫們所津津樂道的“天下共治”政局,為何沒有能夠得到維持和發展?他們是否在廟堂上喪失了一次歷史性機遇?那么,他們為什么會喪失這個機遇,又是如何喪失的?
金國的鐵騎,給予了北宋士大夫政治一個血腥的了斷。
三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又何況是“山中”已十年!
在時代風云的襯托下,易安詞既是婉約巔峰,亦夾雜著一縷“亡音”。在趙明誠重出江湖擔任高官之后,人們從易安作品由清新慵懶而變得幽怨哀愁的格調中,發現了更多不祥的端倪。
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鳳凰臺上憶吹簫》)
這種不祥是女詞人的,也是那個時代的。
康震教授的研究很有洞見。他找到易安作品中先后使用過的三個典故,并從中發現:趙明誠復職之始,即是他們夫妻感情危機之時。結合北宋社會風氣,康震認為,趙明誠養了外妾,冷落了易安。
一是“武陵人遠”“煙鎖秦樓”。
“武陵人遠”,典出南朝劉義慶《幽明錄》。說漢朝時,劉晨、阮肇二人在天臺山采藥迷路,偶遇兩位仙女,樂而忘返,與她們共同生活了大半年。返家后,方知世間已過六世。“煙鎖秦樓”,典出《詞譜》卷二十五引《列仙傳拾遺》中的故事。說秦穆公時,蕭史善吹簫,穆公將女兒許配給他,結為愛侶。兩個典故都暗示丈夫有了“外遇”。
二是“分香賣履”。
在《金石錄后序》中,易安在記述趙明誠去世情景時曾寫道:“取筆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分香賣履”典出曹操的《遺令》,說:“余香可分與諸夫人,不命祭。諸舍中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也。”意思是將剩下的名貴香料等財物分給諸位夫人與侍妾,并要求她們學會自食其力,比如做鞋帶售賣。易安使用這個典故,正好說明趙明誠生前是有侍妾的。
蓄養侍妾歌妓是宋代士大夫階層的風尚。按康震教授的統計,宰相韓琦“家有女樂二十余輩”,宰相韓絳“家妓十余人”,歐陽修“有歌妓八九姝”,官員身份的蘇軾也“有歌舞妓數人”。
宋真宗多次鼓勵大臣們蓄養歌妓、享受生活。據說,他與大臣們曾經如此推心置腹:
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得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
(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五)
當時不僅私家、驛館、酒樓蓄養歌妓,官府有“官妓”,軍營有“營妓”。仁宗年間,家妓、官妓不僅成了官僚貴族、文人商賈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成了社交、商業場合的一種可以互贈的禮品。甚至連太學生也常召喚歌妓到太學中陪酒。
在如此奢靡享樂的社會風尚之下,趙明誠在官府為官,也不能免俗。這本來也不算什么,但對于年近中年且尚未生育的易安來說,那顆高傲的心,就面臨著巨大的落差。
這種社會風尚恐怕是趙宋對高官貴族階層的“糖衣炮彈”,讓他們在享樂中放棄對重權的覬覦。從杯酒釋兵權、崇尚文治到倡導奢靡生活享受,趙宋朝可謂用心良苦。
這與“宋詞”有關聯嗎?當然!
五代以來,詞作為一種宮廷靡靡之音逐步走向市井,與世俗化的社會生活快速接軌,蔚然成為一種時代文化潮流。
這里不能不說到為人們所熟知的詞人柳永(約984—約1053)。柳公子出身河南柳氏官宦士族世家,參加科舉屢試不中,于是流連江南,一心填詞,給歌妓樂坊傳唱,乃至“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柳永成為婉約派代表詞作家之一。到了蘇東坡,詞這種體裁方才突破“閨房”的促狹天地,成為抒寫人生際遇和社會萬象的文學樣式。
然而,歷代王朝唯獨趙宋消受不起這樣的“婉約”。石敬瑭將幽云十六州拱手割讓給遼國,使得此后的中原王朝失去了北部屏障。西北部黨項的崛起,也使得中原的軍馬、鹽鐵等戰略資源供應盡失。連位于黃河平原的國都汴京,也不免一覽無余地暴露在馬背民族的兵鋒之下。
難怪有人不無遺憾地發明了一個“斷語”:“帶血的宋詞”。
青州這樣的北宋重鎮,距離京城、金宋邊境也不算太遠,我們卻在易安夫婦兩人的作品中看不到半點時代風云,這的確是令人困惑難解。要知道,至少易安仍是一個關切時政的作家。
在1099年,她與張耒的唱和就曾震動一時。
張耒年長她三十歲,與李格非都算蘇門弟子,二人往來密切。在汴梁期間,張耒經常造訪李府,研討文學,談論國事,對多才的小女公子在文學上有著持續的指點,時間一長,就成為亦師亦友的關系。
1099年,張耒寫下七古《讀中興頌碑》,借安史之亂的史實抒發了百年興廢之慨,贊頌了郭子儀、李光弼等中興名臣的不朽功績。這首詩在當時影響很大,黃庭堅、潘大臨等知名詩人都有唱和之作。
時年李清照約十六歲,也創作了《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兩首長詩,分析了安史之亂的根源,表達了她對北宋朝政的擔憂。在詩中,她呼吁要吸取歷史教訓:
夏商有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俱在。
(《其一》)
進而她發出警告:
君不見驚人廢興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
不知負國有奸雄,但說成功尊國老。
(《其二》)
誰能相信出自一個少女的手筆呢?
那么,她在青州居住時期和趙明誠復職后的萊州時期,難道對日益困窘的北邊局勢沒有關注嗎?這是不合情理的,我們也無法面對這個尷尬。
連轟動當時文化界的易安《詞論》,也不得不導向另一種傾向的批判。就如研究者點評的那樣:
(《詞論》)既否定詞體的改革,又未找到新的出路,于是仍回到固守傳統“艷科”“小道”的舊軌道去。
(謝桃坊《中國詞學史》)
這樣的解讀,使得易安“詞別是一家”的驚世論斷和她在《詞論》中對各大詞作家的激烈針砭,瞬間變得黯然失色。
四
然而無論如何,顛沛流離的日子都要開始了!
在金國鐵騎的兵鋒所向,易安拖著十五車文物圖籍,為家族的名譽和多年珍藏的安全,以其超常的大智大勇,踏上了追隨宋高宗的南渡之旅。青州十年的全部快樂與幸福,轉變為逃亡路上千百倍的痛苦煎熬。一個弱女子的生命成色,就以這樣嚴酷的方式得到了“淬煉”。
在艱辛的旅途中,易安經歷了喪夫之痛,經歷了盜賊的算計,經歷了張汝舟的“騙婚”,經歷了“玉壺頒金”流言的中傷,女詞人的品性和格局也得到浴火重生。她內心的那個英雄再次滿血復活,在創作上別開生面,真正成就了她“詞別是一家”的理想。
于是,我們讀到了她對男性世界聲色俱厲的批判:
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
(《烏江》)
更有對北方青州老家的泣血懷念:
欲將血淚寄山河,去灑東山一抔土。
(《上樞密韓肖胄詩》)
而她的“后浪”們也逐步走上歷史的前臺,帶來陽剛充沛的南宋詩詞佳作。比如,易安的老鄉、抗金戰士辛棄疾:
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
(《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還有劍膽琴心的陸放翁:
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
就連《金石錄》這樣的作品,也要在若干年后由易安親自補上這樣的一筆:
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歟?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肯留在人間耶?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嗚呼!……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矣!
(《金石錄后序》)
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一個中年喪夫的女子身陷亂世,性命自保尚且不易,何況幾卷書呢?然而,青州十年的最好念物《金石錄》,在易安“以命護稿”的九死生涯中終究得以完整保全。對易安而言,在經歷了三十四年的家國巨變之后,有了這部《金石錄》,似乎一切不甘都變得稍稍圓滿,一切遺憾都得到些許補償。也唯有這樣,那些青州往事、那些似水年華,也才終究變得可堪追憶。
至此,或許你我可領悟:易安已成為一個載體、一個媒介,照見千年來漢語讀者自己的心路歷程。我們對易安的千年追尋,對紅顏的百般憐愛,對才華的萬般景仰,對人性高處的矢志不渝,原本就是一場一場的自我期許、自我發現和自我救贖。一部易安的傳播與接受史,也正是一部漢語民族跨度千年的心靈史詩。
——知否,知否!那些青州往事,它們并未如煙。
責任編輯:田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