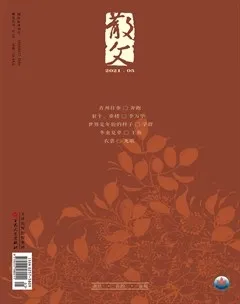讀周思聰
菡萏
一
周思聰是靈秀女子,才氣逼人。她晚年繪的《荷之系列》,極為動人。那種淡,是用水沖出來的,煙火全息,淡到不能再淡。
才情偕風骨并存,是件難事,也是件奢侈之事,亦是一個真正藝術家缺一不可的德行,周思聰做到了。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個蠢蠢欲動的時期,也是藝術的荒涼期。她的荷系列誕生于此,與下海經商的浪潮背道而馳,可用“坐靜”來形容。即便篩濾至今,也是無法逾越的高度。那樣的荷,沒時光性,不過時,也無法仿效。不像吳冠中老先生的畫,易臨摹,贗品也就多。周思聰的荷,除用紙做了特殊處理,墨色里還混入丙烯及廣告顏料,無論審美意象,還是創作技法,均獨特。這樣的獨一無二,造就了其特質,也見創新精神。她不盲從別人,也不蹈襲自己,對藝術的嗅覺異常靈敏,所煥發出的勃勃生機,淡遠悠長,愈靜愈美。盡管那時她的生命已趨萎縮,進入倒計時。
她是個天才,她的高度,至今無人跨越。活著在世,她沒能迎來藝術的繁榮期,但作品超前,且時間驗證了這點。
她的逝去是美術界的重大損失。五十七歲,一個畫家的黃金期,離臻入化境尚遠。她折翼在自己的高度里,藝術不老,肉體卻休止于中年。
灰,是種很難把握的色調,深淺的彈性游走在水墨兩極之間。周思聰的《荷之系列》,幾乎全部采用此色。灰,并不臟,吹化了的水,極致清潔。像雪落在薄薄的宣上,脫去戲服,便這般清儀。那樣的肅穆,是另種隆重與浩渺。
你會發現,最好的色澤是無色,榮辱過后,如此空淡。
任何顏色均嬌媚,透著自身個性與熱情,哪怕冷色,也有自己的表現欲。灰揉搓了所有色,又背離了所有色,那種抽身極令人心疼。就像周思聰的一生,健康時,四周圍堵,老人孩子親戚,家務工作,學習開會應酬,一樣都不能少。外加畫債纏身,擁擠在自己的日常。她也畫過一些時令畫,而真正平靜安詳下來時,已到了肉身潰敗期。
關上大門,世界才是自己的。
二
周思聰的創作分三個階段:早期政治,中期生活,最后自己。由大而小,步步退縮。代表作有《礦工圖》組畫、《高原風情畫》《荷之系列》等。反過來看,也是她心靈自由度逐漸打開的過程,大與小、內與外本辯證。她終于屬于了自己,屏蔽了外界雜音,這種單純性,鑄就了她最后的高度。
藝術,不能戴著人性鐐銬舞蹈,回歸自己,方能散發人性真味。周思聰的一生,也是同時代大部分畫家的寫照。起先畫大題材,為國家;中期畫生活,礦工、兒童、難民、少數民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凡人的負重,亦是自身映像、時代縮影;最后畫自己,不再寫實。那些荷,極為縹緲,是其精神世界純潔度的映射。
她曾在信中對馬文蔚說,喜歡拜讀孩子們的畫作,沒有想討人歡喜,或被人恥笑的種種顧慮,真摯,一心一意表達情感。而自己的畫雕琢太多,條條框框太多,不能自由抒發。每畫完一幅都像打了敗仗,沒有勝利的快樂,多么想體驗一次!
可見藝術多么艱難,又多么簡單。說一千道一萬,離不開“情感”二字。
她最后做到了,變得極度輕盈歡愉。
她的畫不襲古,不風雅,非沈復的《浮生六記》或張岱的《陶庵夢憶》推崇的東西。樸素自然,有對生命最原始的體察。她說,喜歡美,凡美的都想畫;喜歡大自然,喜歡平凡人,這是她鐘情的兩樣事物。
她不做作。
每當看到有些人搬出若干古典知識,炫耀自己多文人雅士、風流情調時,便想起周思聰。她是那么可敬,透著人性真實的光輝和對自然的摯愛。
深刻是件令人糾結之事,被諸多文藝家翻來覆去咀嚼過,顯得越發高深。人與時代的關系似函數,一個膚淺之人,非不關心時代,而是對外界無獨到認知。精確點說,還是價值觀問題。
時代是由人組成的,孤立的時代并不存在,人的感受本在時代大潮中。
最大的深刻便是對虛榮斷奶,虛榮是喂大的。走在自己的清水里,方為深刻里的深刻。
藝術很小,所謂大,只是光源輻射,而非假大空。世界的袍服再大,不能穿在自己的身上;量身定做的,永遠是自身情感的外衣。正如周思聰所言,“它不負責說教功能”。
所以在她這里,看不到所謂深刻,只有美、自然和真實。當然還有一些詼諧犀利之見,對事物的好惡評判,都是她的價值取向。
精神是無色的,有其純正、純粹性,宛若她繪的荷,除喚醒潛在審美外,還注入個體生命經驗與想象。“生活沒讓你失去童年對生活的樂趣,你便是詩人和作家。”于繪畫亦是。童心,是藝術的眼睛。藝術首先是自我的,然后才是社會的。正像《紅樓夢》,首先是曹雪芹的,其次才是歷史的。脫離了自我,哪還有情感可言。人本體的關懷,先要自我關懷,于社會和歷史才有不自覺作用。
歷史上沒有一位畫家和作家,創作初衷,是為時代作序的。無非想畫、寫出自己心中那點可憐的東西,而這點東西,恰恰是一個時代的珍貴部分。
生活是活出來的,作品是生活的骨頭。
三
周思聰是患類風濕去世的,很疼,是慢性的癌。骨頭里的病,在歲月里磨著你、啃噬著你、丑陋著你,也軟糯僵硬著你。聽不見骨頭咔咔變形聲,卻感知它日益腫脹的刺痛,七扭八歪的難堪,清醒的只能是內心。馬文蔚最后去醫院探望她時,她的臉也已變形。
自己也曾手指晨僵,見風疼,打字戴很厚的棉手套,睡覺也是。也曾反復驗血,到處看診。很灰暗的兩年,也疑心過類風濕,恐懼忐忑都有。所幸好了。周思聰的絕望與平靜,可想而知。
骨骼乃人體最美的部分。拍過手片,那種美是沒遮攔的,像藝術,比肉眼看到的實體更美。一個人的氣韻多半是骨骼給的,而周思聰病的恰恰是骨頭。
疾病是強盜,搶掠的不僅是健康,往往還有身體里的尊嚴。
史國良第一次見周思聰,覺其特別土,穿件丈夫盧沉穿舊的男士上衣,打了補丁,染了色,臉色也不好看。包括她婆婆在內,一家五口擠在一間九平方米的暗屋里。當時,周思聰已是知名畫家。于這樣的畫面中,不難看出她賢淑節儉、內心沒自我的品質。
史國良那時年輕,不諳世事,學畫心切,半夜也去叨擾。周思聰疲乏一天,瞌睡連連,盧沉也不耐煩。但她仍耐心講解,鼓勵史國良。史國良無以回報,就幫她做點家務。盧沉身體不好,患有肝病。周思聰坐月子,大冬天仍站在院內水池旁,雙手插入刺骨的水中揉搓衣服,便落下病根。
臧伯良曾幫周思聰賣畫,她和盧沉的工資加起來,也就一百多塊錢。他們的畫在榮寶齋八十元一幅,臧伯良多給點。她自己重病在身,孩子們需要開銷,而她的手基本不能再畫,屋里亂糟糟,也沒作畫條件。
臧伯良下過十份定金,一千塊錢。她沒畫給,讓臧伯良從參展畫中選十幅。臧伯良考慮是她各時期代表作,賣了可惜,便說還是隨手畫些老風格的。
她畫風正變,怕臧伯良嫌不好,眼中透著惶恐不安,急急地去拿錢。臧伯良說一生都不會忘記周大姐那期許的目光,自己心酸得想掉淚。
這便是畫家的窘境,真正的藝術是寂寞的,它并不能使一個人大富大貴。
照片里的周思聰是位外表沉靜、端莊可親的女子。溫柔的眼神閃著母性之光,像深潭里的水,能把人吸進去。
周思聰的兒子盧悅在接受電視采訪時,評價自己的媽媽用了“偉大”一詞,稱其為二十世紀中國偉大的女性畫家。其實,他并不了解母親,他母親喜歡平凡。一個真正繪畫之人,舍不得的是勞動,就像割舍不下親情。價值只是外界界定,多少戴著貪婪勢利的鏡片。
周思聰1962年畢業于中央美院,畢業畫繪的《蔣兆和先生肖像》,天賦那時便顯現。構思機巧,蔣先生臨桌揮毫,背景是其成名作《流民圖》。老師的人與作品有機結合在一起,桌上之畫,便是背景圖。既有內心活動,又有外部延伸;既有創作過程,又有大功告成,集分裂與統一為一體。
繪這種畫頗有難度,不僅設計出形神兼備的老師形象,尚要臨摹好老師的成名作,一百多人的浩瀚場景。臨死前,畫的最后一幅圖是恩師李可染。她的骨節已嚴重變形,不能握筆,只能忍痛用指頭夾著毛筆。寥寥幾下,一位拄著拐杖,胖墩墩溫雅前行的老者便躍然紙上。晚年的李可染,她記憶深刻,可親可敬的老師。
幾日后,她便死了。
這兩幅圖繪的是老師,也是她自己,生命從隆重至清淡的過程。
四
很多時候,一個畫家便是一名潛在的作家。周思聰的文字亦好,輕柔靈動,俏皮可愛。
“文蔚,收到你的信時,春樹剛剛透出輕柔誘人的淡綠。”1981年4月9日的春天,如在眼前。
“北京這滿載風沙的春天,又誘人,又惱人,但畢竟是春天來了。”活畫出北京的春天,使人想起老舍說的“墨盒子”。
隨便翻至一頁。“文蔚,現在是清晨,車窗外已是一派南國景色。夜里下過雨了,土地滋潤,紅綠分明。朝暉印在一簇簇農舍的白墻上,輕柔舒緩。路上背包挑擔的,農民們匆匆去趕早市。車廂里忙亂起來。對面坐著一位年輕母親在奶她的小兒。就是這個嬰兒昨夜不時啼哭,聲音甜甜的,令人神往。有人發出怨聲,示意那母親,妨礙了別人的睡眠,我倒是喜歡聽。這個小罪魁現在正美美地吸吮著乳汁,玩著自己的小腳丫。”
旅途中匆匆隨意幾筆,便情趣盎然,車窗內外描摹殆盡,有情有思也有愛。她滿眼慈愛,孤身乘坐的綠皮硬座車廂。
1986年,她住在醫院,寫道:“周圍靜極,三只肥滾滾的小麻雀正在涼臺上啄食,我盯著它們已有好幾分鐘,美麗的小頭,左顧右盼著……”
多么好的“肥滾滾”。小信輕快安適,透著天真,一點都不壓抑,盡管處于病中。
她說腿關節已有好轉,這讓她很得意。
心態,依舊似少女。
有封信這樣寫道:“文蔚!我寂寞極了。兩個藥瓶懸掛在頭上方,破碎的彩虹,微微晃蕩。那液體慢吞吞,不情愿地一滴一滴流進我的血管,它究竟是要解脫我多少苦難,還是故意消耗我的時光。”
這是她去敦煌途中,因病住進蘭州醫院,急不可待用手紙寫下的。疾病在其筆下充滿詩意,苦痛與所珍愛的時光也是輕淡的。然而半夜常嚶嚶疼哭,她不想麻煩別人,即便在臨死的前一夜。
臨死前,她有過一段靜謐時光,精神很好,和盧沉住在北京西郊的一處賓館。環境清幽,有人照顧,有作畫條件,時間空間都具備,也有喜愛的光線。除完成賓館任務外,還尚可畫自己的作品。
《墨荷》系列,便誕生于此。她的骨節已不能彎曲,只能用腫脹的食指和中指夾著毛筆,三個月畫了一百多幅。每天吃激素,直到腿部潰瘍,不得不離開畫案。1992年,她迎來了自己的巔峰,忘情游走在水墨的黑白世界,輕盈朦朧,也對死亡做出了另種詮釋并坦然接受。
《朝霧》《碧葉蒼煙》《雨溟溟》《絮語》《聽雷》,這些靜寂的荷,在其筆下風塵全無,清虛到仿佛從《詩經》里走下。洗褪了現實版的鮮明,也摒棄了傳統墨荷的圭臬,脫胎換骨的一瞬,極具殺傷力,可謂素到極致,素到驚艷。
一個人活至最后已變得極輕,卸下沉重肉身,細小的肋骨,似一莖蘆葦。暮秋江岸,一天雪白。悲愴而平淡。
真正的美,是抽象、提煉過的神經末梢語言,有極高辨識度。她的荷長成了她的本體,是人化了的物。藝術也是在不斷碎裂中發掘自身的過程,作品乃作者自身遺落的鏡像,有多少能量便分娩出多少個自己。邯鄲學步,拓片,只是幼兒階段的把戲,如果找不到或背離了自己,都終將是不誠實的。文學和繪畫最可貴的品質,是擁有自身真氣和根性。
肉體沒有永恒的榮耀,不死的唯有魂魄。人們視她為中國二十世紀美術史杰出的女畫家,繼任伯年、蔣兆和之后著名的人物大師。也有人說她是自李清照以來中國最偉大的女藝術家,還有人稱她為亞洲最優秀的女畫家。
而這些輕飄飛舞的花絮,她都沒聽到。她的一生只忠實于自己。離世后,馬文蔚曾和她哥哥去祭奠她,他們都沒一張她的畫。
責任編輯:沙爽